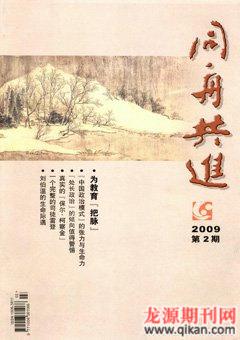编读往来
新年伊始出手不凡
广东广州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辞旧迎新之际,《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已送到我手上,正好利用元旦假期细细品读。刊物的封面、栏目与风格一如既往,雅致而亲切,好似与老朋友晤面。一读文章,却不能不惊异于新年第1期的出手不凡——不仅专题策划做得好,而且几乎每一个栏目都各有精彩,让人目不暇接。
“网络改变中国”专题文章深入浅出,击中要害,道出不少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真知灼见,不能不让人佩服作者的智慧与编辑的眼光。杜平《网上的中国令人兴奋》将网络与传统媒体对比阐述,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譬如:“中国网络的活力,在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通过传统媒体和正规渠道表达意见的民众,终于拥有了一部分话语权。”“网络在毅然决然地推动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出现的网络公共事件也正在有力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型。”王长江《执政党如何用好网络渠道》阐述了网络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不是手握权力单方面行使权威,恰恰相反,是首先获得民众的认同”,网络在这方面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民网的“什锦八宝Fans圈”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即使网络上出现“负面信息”,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负面信息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只有在碰撞之中,人的理念、观念才会越来越牢固。作为执政党,有引导全民价值体系全方位发展的责任,而不是以生硬的方式使群众的步伐整齐划一”。这样的论说充满了民主政治的智慧与改革创新的意识。笑蜀《两亿网民穿越言论长城》说得好:互联网的从天而降,有如时空隧道,让“两亿中国网民正在穿越千年万里长城,展开阳光下的思想竞渡”。王志安说:网络让“你是公民,也是记者”变成现实,“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时代发展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必将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王琳《虚拟世界的真实规则》认为,“网络始终是人创造出来的事物,仍然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陈季冰《“网络暴力”的特殊功能》提出了对“网络暴力”的新见:“虚拟世界里问题的根源出在现实世界,不化解巨大的社会不公,不消除‘社会暴力,‘网络暴力只会有增无减。”因此,所谓“网络暴力”,其实“是未来民主化进程必定要经历的暂时性的社会混乱在虚拟空间的提前预演”,应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
“议政论坛”栏目的文章很有力度。十年砍柴《县委书记的权力边际在哪里》振聋发聩,指出要解决县委书记在其辖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权力泛滥,“不能简单地进行荣辱观教育,必须在体制上作较大的改革,真正做到‘限其权,实其责”。于建嵘《农民:三十年的得与失》总结了30年改革带给农民的得与失,但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徐松林《官员豪华别墅群“三奇”揭秘》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征地时的一元垄断制和供地时的价格双轨制不改变,官员豪华别墅群越来越多、农民对政府征地的反抗越来越激烈等现象就不会有大的改变。”因此,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唯有寄希望于土地制度改革。不过,改革的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着矛盾。王志安《棘手的难题:土地的“原始取得”》对土地制度改革中的难题——“原始取得”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土地制度改革目前还不能操之过急。
“公众话题”栏目的两篇文章都不长,却触及当今中国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靠什么推进改革?秋风《改变中国:靠制度?靠道德?》指出,人的变革意识“源于人们的道德感:人们是因为觉得现实不‘好才形成变革意识的”,“人们总是呼吁制度变革,但可能恰恰忘记了:自己就是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应当说,善良、诚信等道德伦理的缺失是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是非常有见地的。郭宇宽《我们是否要回到“自力更生”的社会》叙说了孙大午、马文友两位德才兼备的企业家不得不“自力更生”办一大堆企业的经历,从而阐明: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诚信,必然大大提高交易成本,而“当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就无法运作”。因此,在推进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
古代中国向来注重道德伦理,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今中国最为缺失的恰恰是道德伦理与文化礼仪。“同舟视点”许纪霖的文章《中国文化在哪里?》指出,“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需要一套礼仪,如今中国文化的这套礼仪可以说已经崩溃了”。的确,如何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弘扬民俗文化,进而建设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同舟共进》不仅关注社会现实,而且对揭示历史真相并进行反思情有独钟。2009年第1期为我们奉献了不少这方面的好文章。譬如:“人物春秋”栏目的《罗翼群与叶恭绰》读来让人感动而又沉痛。又如“往事历历”栏目的《蒋氏父子研制原子弹秘辛》披露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美国暗中帮助下紧锣密鼓地展开原子弹研制而最终被美国叫停的过程;《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以翔实的数据讲述了从新中国建立到1970年代中期对外援助的情况。这两篇文章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认识价值。
一种“抛砖引玉”的兴奋
——捧读金春明先生、郭汾阳先生的文章
北京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编审):读到《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金春明先生的《一点补充和思考——读<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一篇是郭汾阳先生的《也谈“约法三章”及其他》,非常高兴。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我发表在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上那篇关于“约法三章”的文章引起的,我有一种“抛砖引玉”的兴奋——这不是客套话,确确实实是肺腑之言。
金春明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特别对“文革”研究有突出的成就和贡献。我读过他的著作和文章,受益匪浅,也见过面,他长我几岁,我对他是很尊敬的。郭汾阳先生没见过,可能比较年轻,既被称为“文史学者”,也肯定有相当的造诣。我是一个普通的理论工作者,不是搞历史的,1998年退休后写点关于回忆“文革”的文章,那是经过很多历史学界热心同志的劝说才做的。而我回忆“文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厘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江青结婚中央究竟有无“约法三章”?读到金春明先生和郭汾阳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眼界大开,既增加了知识,也加深了认识。金春明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革命老前辈杨尚昆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这对否定“约法三章”是很权威的材料,而我从来没看到过,没听说过。在金春明先生的这篇文章中读到了,心里的高兴是不可言表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郭汾阳先生在文章中提到1947年“毛泽东《五律・喜闻捷报》中的‘妻儿是谁”,也使我兴奋异常,这个问题根本没进入过我的视野,这说明我多么孤陋寡闻。在他们的文章中我还读到关于江青的许多新材料,这是我兴奋的原因之一,十分感谢两位先生!
我兴奋的原因之二,是金春明先生和郭汾阳先生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探索和研究。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尽管我坚信没有什么“约法三章”。更可贵的是,他们都提出了继续探索研究的思路和线索。据此,我可以完善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和论据。
我兴奋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金先生和郭先生的文章向世人表明,学术问题一定要互相切磋、“百家争鸣”。事实越辩越清,真理越辩越明,这是百验不爽的道理。中央近年来提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要进一步在学术问题上贯彻“双百方针”。如果我们三人的文章在这方面有所裨益,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恕我代表他们两人说话了。仿佛邵燕祥先生曾提议建立“江青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建议。江青,20世纪30年代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什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造成中国和中华民族“十年浩劫”的历史罪人?她的思想演变的轨迹是怎样的?内因是什么,外因又是什么?如此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不消说,“江青学”即“江青研究”是“文革学”、“文革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约法三章”问题只不过是其中的小问题,当然也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同时,还要指出,《同舟共进》的同志热心为学术讨论和争鸣提供平台,这是智者所为,很值得称赞,衷心祝愿这个平台越筑越牢,范围越扩越大。一花再艳不成景,万紫千红总是春,让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和氛围真正地成为历史吧!
金春明先生在文章中最后引了恩格斯的话,我再把这段话引全些。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和金春明先生一样,在这方面“愿与有志于研究党史的同志们共勉”。让我们一起为实事求是地开拓历史(包括党史)研究的新局面而努力!
广东广州 陈朝辉(广州地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同舟共进》是国内最讲真话、最实事求是的杂志。2008年一如2007年,是有很多好文章的一年,不少评论性文章切中时弊,提建议切实可行;许多回忆文章切实可信地还原历史,读后令人荡气回肠,豁然开朗。“同舟视点”和“焦点关注”能对现实的政策弊端提出看法和良好建议,有现实意义,令人倍感爽意,也坚定信心。(2008年12月18日)
浙江温州 许岳林(离休主治医师):我是贵刊多年的老订户、老读者,订阅了几年受益匪浅。我读过几个省政协的报刊,认为《同舟共进》是最有品位的,并向同学、朋友推荐。《同舟共进》关心民瘼,尊重历史,鼓吹民主,呼吁法治、宪政,总体来看是一个好刊物,我希望它继续更好地办下去。(2008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