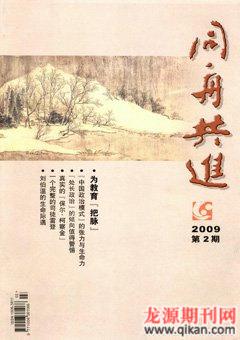教育改革至少滞后十年
顾明远 温元凯 杨东平 等

应试教育:教育领域的癌症
□ 敢峰(北京力迈学校名誉校长,曾任教育部干部,晚年致力于民办教育事业)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规模是空前的,但存在一个严重的危机:应试教育。
中国的教育改革至少滞后于其他改革10年。现在的教育状况可用一段话来描述——“‘三个面向艳阳高照;应试教育阴云密布;教改之路崎岖难行,而且路上‘行人稀少”。近年来,应试教育风助火威,愈演愈烈,整个教育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应试教育是教育领域的癌症,应试教育+(现代)社会=“机器人”制造车间。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铸造出来的学生都是同一张面孔的。
现在的情况很有意思:所有人包括领导都反对应试教育,但大家都戴着“紧箍”。谁是唐僧?就是评估、排名。因此,要坚决改变对学校评估的价值取向,淡化升学率标准,强化以学生的进步为标准的评估。
过去因材施教,是好的思想,应不拘一格“育”人才、“用”人才。

勇于改革的大学校长哪里去了
□ 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
中国崛起还缺少什么?人才。中国现在面临高端人才的危机。
根据上海交大发布的2007年世界500强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有8所在美国、两所在英国,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排第181位,北京大学排第257位。中国为何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50名,这很值得深思。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前两年说过一句很尖锐的话,“中国在国际上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5个人”。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很突出。我与很多老板交谈过,问他们是否满意应届生的表现和能力,90%以上都摇头。很多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夸夸其谈。在美国,进名校要考核四个方面——领导力、创造力、协同力和做义工,书呆子、高考状元不一定能进名校。而在中国,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实践能力。
中国缺少一批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大学校长,现在大部分大学校长只是教育官,不是教育家。想要变革的校长不是没有,但就像过去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样“全身被捆绑”,受到体制的约束,想做事也很难。张维迎在北大推进改革,结果把自己的“党委委员”“改”没了,可见教育改革的艰难。
上世纪80年代是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几所学校——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都由当时的校长推动迈出了改革步伐。但在90年代以后,哪一个大学校长、哪一所大学作出了真正的改革?这就是由于缺乏改革主体。改革首先要鼓励改革者,只有更多人参与做扎扎实实的事,改革才能被推动。

小孩怎么能从小分成三六九等
□ 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两主席之一)
人们谈教育存在的问题,谈教育改革,往往忽略一个重要的角度——文化背景。
“应试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大陆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存在。这跟东方的文化背景、长期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有关。另外,我们的社会是人情社会,家长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认为邻居的孩子上了大学而我的孩子没上就很没面子。
2007年我在成都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成都市政府提出减轻学生负担,可家长不答应。即使学校减负,家长也重新买参考书,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这里特别谈一下奥数的问题。其实我是奥数的始作俑者之一,1986年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参与组织了第一个奥数班。但现在我是坚决反对的,奥数对人才是一种摧残。我讲完以后,一个小孩举手发言:“顾爷爷,我们不上奥数班,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上不了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我将来怎么养家糊口啊?”一个10多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其实代表了他父母的心声,反映了社会现实。所以素质教育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一个制度设计就能解决的,根源在于教育理念要转变。
还有“三好学生”的问题,我很反对。小孩怎么能从小就分成三六九等?这样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吗?为什么一定要定格你是个好学生,他是个坏学生?这样的话,北京奥运会得了8块金牌的菲尔普斯就是坏学生,他小学时调皮得不得了,还有大器晚成的爱因斯坦也不是好学生。
现在评“三好”衍生出很多弊端。另外还有弄虚作假,孩子给老师送礼,孩子之间也讲关系,要选三好生了,请同学吃饭,给同学送礼。成人世界的腐败都渗透到小学里面,这样下去,民族的未来堪忧啊。
教育的方针是全面发展,是对每一个学生讲的,为什么只评出来10%、15%,那85%、90%都不是好学生?说明你贯彻了方针没有?说明你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废除不了?就是观念不愿变。不能用单一标准去评价孩子,这种评先进,特别是在学生里评先进,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现在素质教育主要是知识分子家庭、干部家庭的孩子能享受到。在农村,也许最基本的课都开不出来,还谈什么应试教育、素质教育。
(杨东平插话:非常赞成取消“三好学生”的评选,取消变相的重点学校。实际上,社会各界崭露头角的人很多都不是“三好学生”,我也从来没当过“三好”。我们的评价标准需要改变。)

大家都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
□ 陶西平(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协会全国联合会主席)
30年来,教育的功能从主要为政治服务向为经济建设服务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如果只停留在这样的阶段,认识容易产生局限。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是一个新的进步。
教育的本源就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陶行知先生讲过,“教育就是教人变,教人变好就是好教育,教人变坏就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这是教育最根本的东西。
美国教育部的大门上贴着一个标语“不让一个孩子落伍”。以人为本应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而我们有时停留在笼统的“人民”概念上。学校老师总是在研究怎样“赛课”、怎样出“名师”,可就是不研究学生。
200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离任时说了一句话:不要问我做了什么,要问我没做什么。他总结自己10年的校长生涯说,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争项目、争经费,争到后来忽然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他最欣慰的就是自己最后几年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环境。

农村教育谁来管
□ 胡平平(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心是教育公平。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孩子入学机会的公平基本达到,但是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公平还很不够。
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办学条件差距仍然较大。我刚到过河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民权县进行基础教育监测,那里农村的中小学几乎没有实验条件,甚至没有活动场所。现在实施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国家拨付了一些计算机和卫星接收设备,大都闲置了,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付不起电费、维修费;二是没有老师会教。可见我们的管理、经费、人才在农村是相当缺乏的。
制度性的缺失是诸多问题的源头,现在只是中央和省一级有刚性规范,到市、县就没有了,所以出现“跑部跑省,谁会哭就有钱,谁不会哭就没钱”的现象,这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管理缺乏有效监督机制,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50多个县,有超过80%即40多个县挪用国家教育经费。

农民工子女中可能诞生未来的伟人
□ 徐永光(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现在教育领域不光有高考指挥棒,还有权力指挥棒和金钱指挥棒。很多问题是深层的体制问题。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很多农村调查,农村教育的落后触目惊心。广西一个乡,五年级的失学率是90%。我问一个老师读过几年书?他说两年,他当时教三、四、五年级。那时,我就觉得要建立一个“希望工程”,动员社会的力量来支持教育。(编者注:徐永光1988年辞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以10万元注册资金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希望工程”)
汶川大地震中,重灾区的146所“希望小学”没有死一个人。《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问我,为什么“希望小学”不倒?其实很简单,第一有全程的监控,第二资金足额到位。因为有民间的监督,地方政府在合作中便不得不认真。实际上希望工程只有四五十亿的资金,这些钱在上海只能修5公里的地铁,但希望工程给社会带来的精神、道德和文化的价值是很难衡量的。
我觉得还是要走“草根”道路,要做一件事,就是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改革开放30年,有很多人受益,但得益最少甚至利益受损的是8000万农民工子女。湖南省和广西省的未成年人犯罪中,50%以上是“留守儿童”。现在这一代农民工的孩子,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越来越强,如果他们从小看到的是不公平,在他们身上埋下的不是政府的关怀、社会的关爱而是仇恨的话,是非常麻烦的。
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首先是政府财政加大投入,其次是发展民办教育。广州市70%的农民工子弟就读在民办学校,东莞大约有80%,北京、上海大概50%。民办学校的好处是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同时不给政府制造太多麻烦。民办学校的发展,一方面应得到政府的补贴,另一方面要持续得到社会的捐助。民办学校可以成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一个农民工的孩子与我联线。这个孩子现在读三年级,已换过4个学校,从家乡到广东,到上海。我问他,你是不是感觉周围的人都说你眼界非常开阔?他问我为什么呢?我说将来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可能就是农民工的子女。我看过一本书,介绍美国13位改变世界历史的伟人,他们都有童年迁徙的经历。如果给农民工孩子一个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社会接纳、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融入城市,那么里面的精英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伟大人物。我最后总是要说一句话:农民工的子女,改变中国历史的人就在你们中间。

杨东平: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尤其需要
□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我深感教育改革失去动力,而且方向不明。大家总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全能政府身上,但政府的行为是难以预料的。只有通过民间的教育讨论,通过集成的教育创新才能解放思想,引起共识,积累动力。
实际上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下,一场理性的、建设性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否可能?很多人觉得太难、太复杂了,没法改。实际上我们虽然寄希望于一场整体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改革需要前提,需要自下而上的基层的创新,需要通过企业参与,从各个不同方面营造改革的气氛,创造改革的实践,然后把它上升为整体性的改革。最近这些年,各地基层教育创新出现了很多成功案例,为整体性的改革提供了一些经验。

政府眼中的教育还很“软”
□ 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区域创新问题,杨东平谈到我们要帮政府总结一些创新的案例,这都是非常好的。人民满意的教育不应光由政府来评,更多应由民间来评。地方的创新,其实更多的是要遏制甚至削弱体制性的障碍。我曾在安徽和江西调研,发现从教育部一直到下面的学校,层级过多,一个好的政策经过层层机构、层层政府权力的影响,最后执行总有很大的偏差。另外在一些地方政府中,教育是排在财政、规划、基建等之后的,教育很“软”。这些体制性障碍不排除,不光改革难以推进,还会给教育带来很大损害。

教育部很难有所作为
□ 胡建波(西安欧亚学院院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认为,教育改革从国家教育部制度切入太复杂、太宏观,实际上教育部很难有所作为。美国联邦教育部只做两件事,一是教育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发布,另外就是联邦助学贷款。我们的教育部管的内容却非常具体,如果由教育部来改革,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样,是很难见效的。因此教育改革的权力应更多地下放,由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制订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