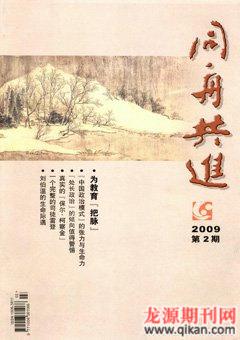权力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陈丹青

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版)又写成了,20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从清华大学辞职那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帐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做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账,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
好在教育界另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了评论:刘道玉、杨东平、顾海兵、张鸣,我一一读过,从中或可找点话来说——
譬如张鸣教授指出:“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点中要穴死穴,让对方反驳不得。”这末一句,其实不然。诸位可曾见全国上下层层叠叠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开场合、大小媒体、各种文本中对任何批评观点与批评者予以反驳么?没有。这教育界的庞大“对方”不是“反驳不得”,而是不屑于反驳。为什么?因为真的权力乃是怡然沉默。你有什么权力?“对方”又是什么权力?且看2006年张鸣闹事,言语不好听,2005年笔者辞职,态度很嚣张,除了若干媒体网络出现过零星同行的议论、问难甚或嘲笑,不见一位教育官员出面反驳。而权力之外更有势力,这势力不仅指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更兼广大无边的无权者:家长、孩子、职工、社区,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链吃饭的卑微者,他们也参与这大荒谬,构成这大势力,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讨生活。
所以,“逆种”如熊丙奇者尽管叫嚣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
资深教育研究者杨东平先生是温和的批评者,尤擅观察与评析:“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备受关注”,“充满着夺人眼球的新闻,具有了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这一层,怕是比“没有反驳”的处境还要美妙——“观赏”,即围一堆袖手的公众看你叫嚣,看你跳,他们可能喝彩,心里以为解恨,但现实肯定改变不了。媒体则作为围观的场所,每天需要“猛料”,隔三差五发出教育圈负面报道“娱乐”大众。是的,如今所有严肃的问题均被精心划分为两端:一端给闷在体制里,动弹不得说不得;一端,是经过筛选而扔给媒体去放大,供大众尽情观赏、消费,形同“娱乐”。中国教育没人反思批评吗?请看媒体多么热闹!舆论能监督体制、革除积弊吗?请看校园内何其平静。权力的齿轮运行无碍,根本不理会墙外的喧嚣。真的,权力不反驳,甚至比没有批评还要糟糕。
刘道玉先生的长篇评论,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他曾是教育界高层主事者之一,亲历其中30年,彻底看穿。看穿者不少见,而凛然说破者几稀,刘道玉先生正是有胆魄、更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他直斥当今主掌教育的高官“不懂教育”,戳穿教育部宣称“义务教育”的“巨大成功”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是“有意误导”,是“欺人之谈”,是对义务教育的“亵渎”,因为他很清楚——人民也很清楚——我国的“假义务教育”推行了20年。他提醒众人:早在23年前的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呢?“教育部集权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有谁会反驳这位教育界的老上级、老校长、老同志么?我相信教育部后任对这类党内异见的良策,还是世故而有效的沉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反问、追问、诘问道:“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但我忍不住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最后的那点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全归僧侣把持,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被就地亵渎;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遞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畸形、劣质、有名无实的大学,仍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劣质、敷衍、滥竽充数的教育,仍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被无耻利用,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这样的“大学”,则当前罄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