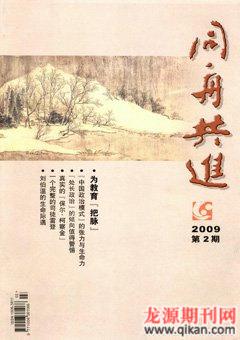告密者:一种历史幽灵的闪现
朱大可
告密者,一种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事件”,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该校两名女生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局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有如此“双管齐下”的周密手法,难怪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早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就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明朝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变本加厉。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乾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
即便在我个人的生命记忆里,告密也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依据。曾几何时,有多少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贱民,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
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例如,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就曾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打死。
“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1977年以后,教师重新找回了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今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教育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
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往往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