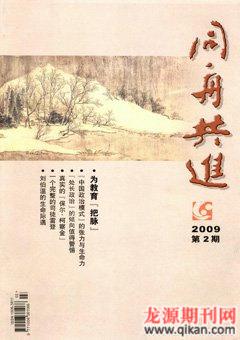“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
《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陈伯达之命运》一文,使我想起自己对于陈伯达的多次采访和相关著作(《陈伯达传》上、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文革”作为一场大灾难已经过去,然而“文革”留给人们的反思是无穷尽的。“陈伯达现象”便是值得探索的反思课题之一。
初抵延安,陈伯达“坐冷板凳”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比起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秀才”们,陈伯达的资历要深得多:他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30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在“文革”中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成为“舆论总管”。1945年的中共七大,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中列第47位;1956年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列第21位;1966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第五号人物”;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打倒后,他升为“第四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直到1970年夏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倒台……1980年,他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尽管康生也有着“理论家”之称,但此人奉行“述而不作”,一生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却是一位著作家。我曾查阅陈伯达数百篇文章及十几种单行本。陈伯达是诸多重要历史文献的执笔者之一(有的是他主稿),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等。
继完成王、张、江、姚四部长篇传记之后,我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陈伯达传》(作者注:初稿为40多万字)。通观陈伯达8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可以发现,理论一旦被奴性和媚骨所玷污,只能成为换取官阶的贡品,从此与真理无缘。“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北平陈伯达先生的《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和《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一卷第二期),“可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奠基石”。(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7年版)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一场自由与民主的运动,在当时颇有影响,陈伯达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把自己所写的一系列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文编成一本文集,取名《真理的追求》,由新知书店于1937年3月出版。陈伯达早年的这些论文写得洒脱,思想无拘无束,他的意识是独立的。他所发动的新启蒙运动(后来艾思奇等人也参加这一运动)于今日看来仍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1937年9月,陈伯达挈妇将雏,从北平经天津、青岛,与黄敬结伴而行,由西安进入延安。刚入延安,这位“理论家”只在马列学院当一名教员。他那糟糕的“闽南普通话”使他的讲课效果极差,不得已而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10年前他在武汉便已担任此职,而他在进入延安前已是中共北平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相当于北平市委书记)。此外,他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初抵延安的陈伯达还处于“坐冷板凳”的状态。
陈伯达后来成为“中共一支笔”的契机,是在讨论孙中山思想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谈了关于孙中山的“两个两重性”的见解,使毛泽东第一次注意他。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时,便请陈伯达作陪,与他作了第一次详谈。从此,毛泽东与陈伯达开始讨论理论问题,有了交往。
那时毛泽东异常勤奋,而且为人谦逊。延安时代是毛泽东著作的高峰时期、思想的黄金时代。为了弄清一点“疑点”,毛泽东会去信询问比他年轻得多的艾思奇“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伯达写了《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送毛泽东处请教,毛泽东不仅仔细看了,而且先后写了3封长信,谈了自己的见解,与“陈同志”“商量”(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时的陈伯达仍按自己的学术见解写文章,只是请毛泽东予以指教。毛泽东再三声称“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不过“望文生义地说出来”,仅供“考虑”、“斟酌”。
此后,毛泽东调陈伯达到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做他的秘书——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最初,陈伯达只是协助毛泽东收集材料,研究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这时,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向王实味开第一炮,大获全胜
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陈伯达领悟到“跟人”的重要性。向王实味开第一炮的是陈伯达。陈伯达在1939年2月16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王实味提出异议,于1940年冬写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批驳陈伯达。陈伯达于1941年1月7日急就章,写了洋洋万言的反驳文章《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反诬王实味有“托派思想”(其实陈伯达本人在留苏期间曾与托派过从甚密)。延安正在“肃托”,王实味一紧张,“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这下子,陈、王之争从理论之争进入整人与挨整。毛泽东支持了对王实味的批判,陈伯达顿时跃为“批王先锋”,在 1942年6月9日作了慷慨激昂的批王的长篇发言,斥责王实味是“蚂蟥”、“白蛉子”(在“文革”中,陈伯达把这种惯用语言演变为“小爬虫”、“变色龙”),大获全胜。由此,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声名鹊起”,再不坐“冷板凳”了。陈伯达总结“经验”,说了句“名言”:“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
1940年代的毛泽东确实不愧为党的英明领袖。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按照毛的思想脉搏写文章。那些文章是不错的。比如,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跟陈伯达闲聊时,说了句:“蒋介石出了个好题目呢!”陈伯达心领神会,连夜赶写《评〈中国之命运〉》,经毛泽东审阅,加上几段精彩之笔,于1943年7月21日发表。一时间被国内外看成“中共论战家”,名声大振。此后,陈伯达又写下《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政论著作。
建国后毛泽东威望倍增。陈伯达写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写了许多阐释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家。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基本上是对上级观点的转述、解释。
毛泽东也发觉“理论家”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从1957年开始,中国向“左”偏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一层层地“剥笋”。剖析这一时期陈伯达的文章及其写作经过,可以清楚看到典型的“陈伯达现象”:有野心而无主见,一切为了取悦上级,以求加官晋级。
“陈伯达现象”表现为: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有时,他不得不如同中医“悬线搭脉”一般,借助于“线”摸情况。陈伯达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这种“轧苗头”、摸行情的作风,宛如政治投机商。“理论家”的“理论”变成“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有时为了抢风头,连夜急就章,以求得“头功”,可谓“闻风而动”,可谓随机应变“胜如神”。
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摸新的“行情”。陈伯达拿到了毛泽东1959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录,反复研究其中一段话:“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到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陈伯达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论证”的“文章”,题目也是来自毛的讲话,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陈伯达急呈毛泽东。此文果然以中央名义加了按语,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此件很好,印发各级党委,供党员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参考,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不久,陈伯达加以修改、补充,在1959年第22期《红旗》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公开发表。由此,陈伯达不仅躲过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成了“反彭英雄”。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进入“文革”后,毛几乎不写文章,只是发布简短的“最高指示”,“秀才”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
例如,1967年第16期《红旗》所载“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是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此文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纳为六条。这六条,是陈伯达和姚文元反复揣摸,从一系列“最高指示”中总结出来的,写毕呈上,附一信:“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主席阅毕,在信封上大笔一挥:“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也是陈伯达主稿的。在陈伯达之前,已有人写过一稿,被毛泽东否定。陈伯达接手此事,格外小心。毛泽东说:“我要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陈伯达反复琢磨这句话,悟出前稿被否定,是因为立足于“庄则栋式”的“攻”,于是他起草时,改为“张燮林式”的“守”——正面阐述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他逐条整理毛的意见,加以系统化,写成《二十五条》。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这最常见。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但“跟准”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发挥”、“发展”的时候。例如,1967年“二月逆流”时,陈伯达把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赶紧加以“发挥”,写出《红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这时,毛泽东却已改变了观点,说:“究竟有没有反革命复辟逆流?”毛压下社论,不予发表,还把陈伯达批评了一顿。
“理论家”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一味“紧跟”,文章充满八股味,就连毛泽东也发觉了这一点。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毛泽东曾举陈伯达为例,说陈的文章现在不如过去生动活泼了。后来,陈伯达在为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作文字修润工作时,请求毛泽东删去这段话。(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一群“陈伯达”
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实际上并不真懂马列。他手中的马列主义,只是为了证明领导的某一观点时,选择马列的某些可供引用的片言只语,用于文章中做装饰品罢了。这位“理论家”在1966年达到巅峰,成为红得发紫的“一号大秀才”,成为极左派的一员主将。自1967年1月4日他联合江青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在1月10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此后他的地位开始变化,一次次遭到批评,在“揪军内一小撮”事件中差点垮台。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改换门庭,“跟准”林彪。在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上,他编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以配合林彪。毛泽东于庐山上写了700字的讨陈檄文《我的一点意见》,陈伯达彻底垮台。毛泽东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于是,全国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陈伯达在“文革”中犯下严重罪行,他自己也承认“犯了滔天罪行”。本文只是从他的“理论家”的道路加以剖析,指出他的奴性和媚骨,使他失去了理论家的脊梁骨。“陈伯达现象”曾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与他同时代的人之中:
姚文元因为在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批评《文汇报》用“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转载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的消息。(正是那次接见,毛泽东婉转地发出了准备反右派的信息)毛泽东见到此文,嘱令《人民日报》在6月14日头版转载,还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姚文元由此名噪一时。
王力因为在1957年8月2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论社会主义的内行》而被看中,调往陈伯达手下工作。由此王力得以发迹。
关锋因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文,受到赞赏,由此得以被重用。
张春桥则是揣摩了毛的几次内部讲话,在1958年第6期《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由此平步青云……
这真是一群“陈伯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姚文元,把看风向、摸行情作为“看家本领”,手中的笔成了随风而转的“风向标”。这群人号称“理论家”,而他们的“马列主义”实际上成了橡皮泥。王力在“文革”中按指示“研究”“文化大革命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些年则在“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真不知他的“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
辩证法的本质是批评的。马列主义之所以具有攻无不克的力量,就因为它是科学,而不是“标签”。
在对“文革”进行冷静剖析之际,应当对“陈伯达现象”予以曝光,并彻底铲除。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