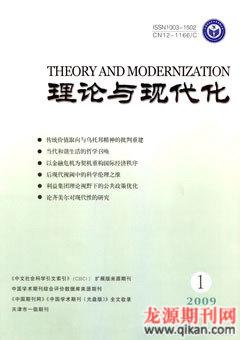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
熊 辉 杨金平
摘要:身份和户籍政策造成农民工社会资本先天不足和积累困难,从而使进城农民工在城市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取消户籍区分、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农民顺利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民工;发展困境;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1-0092-04
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大批农民必然从农业产业转向非农产业、从农村迁往城市。但是,由于我国僵化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存在,进城农民并不能自然地成为城市居民,从而使得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被人们称作“农民工”。这种特殊身份,使得进城农民处于尴尬的境地,使得他们难以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经常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作用
社会资本概念由来已久,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马克思都提到过社会资本,但他们的社会资本概念与后来的社会学家所理解的社会资本有很大差别。美国经济学家洛瑞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他所理解的社会资本是各种社会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组织之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提出并初步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他看来,资本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科尔曼则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个人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其一是人际关系结构,其二是社会组织结构,正是对这些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才使得社会结构资源成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社会资本的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这样,行动者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可以从社会团体或组织的稳定关系结构中去获取资源,也可以通过个人的人际社会网络去获取。虽然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的甚至是国家的财产而不是个人财产,但他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仍然给了我们研究个人的社会资本以有益的启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虽然这种定义模糊了作为心理现象的信任与作为行为关系的组织或网络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组织的特征、人际交往的信任心理甚至是包括国家政策、法律在内的总体社会环境都直接影响着个体获取资源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其一,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大环境之中,这种资本是国家或社会提供的,平等的信念、人际信任、社会道德、合作精神以及国家的政策、法律等制度都影响着个体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不同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使得人们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存在着差别;其二,社会资本存在于群体、团体或组织之中,由于个体的成员资格,可以获取相应的工具性资源乃至情感性资源,这种资源的获得对非成员具有排他性;其三,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人的关系网络之中,个人可以利用其关系中的个体所占有的信息或其他工具性资源,还可以获得情感性资源。
社会资本不是一种直接的资本,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虽然经济资本是资本最纯粹的形式,但是,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当国家给予个人某种资格,他便具有了获取国家公共资源的资格;当个人具备某种团体或组织成员的资格,他便具有了获取存在于团体或组织内的资源的可能性。当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去争取自身利益时,社会关系网络就具有了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格兰诺维特、林南、边燕杰等分别发现和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求职和职业流动的不同影响。同时,社会资本还具有提供社会支持的作用,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可以获得有形的物质支持,也可以获得无形的精神支持。
二、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和积累的困难
波特斯首先注意到社会资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后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等等)都与移民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密不可分。农民工虽然不是真正的移民,但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过程以及在城市中经济地位的获得,同样受着其在城市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深刻影响。
与城市居民和一般的城市移民不同,农民工不具备市民身份,因此不具备国家提供的城市居民应有的社会资本。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当国家赋予一定成员以一定社会身份的时候,也就给予了其相应的社会资本,规定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和范围并使之合法化。对于进城农民工而言,由于其身份限制,尽管他们与城市居民有着大致相同的义务,却无法平等地获得城市为其市民提供的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福利保险等在内的各类优惠性的或稀缺的社会资源。正是在制度化的城乡区隔的身份制度的制约下,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先天不足。没有人能够否认,在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在获取城市公共资源上具有合法化的绝对优势,而农民工要享受城市公共物品,则需要花费比城市居民更大的代价,这无疑增加了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在城市中,虽然市民身份可以看作是一种能够享受城市特权的正向社会资本,而对农民工而言,农民身份则成为一种负向的社会资本,不仅不具有增值作用,相反却具有减值作用,直接影响着农民工职业的获得以及收入水平(如很多城市对行业用工进行了分类,对外地工的工种进行限制)。
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还存在于家庭和亲属关系、邻里、社区、单位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之中,基于他们的成员资格,可以从这些组织和团体获得相应的资源。而对于农民工而言,远离家乡,也就意味着削弱了或者失去了其所属的乡村群体的社会支持。科尔曼曾列出了六种社会关系可以构成个人有用的社会资本,其中多功能的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组织的创立可以提高个人行动的一致性,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从而使行动更为有效,由此成为组织成员重要的社会资本。无论是自愿形成的多功能组织还是有意创建的组织,虽然是出于一定的目的,但也可以为成员的其他目的服务。如果这种组织被保留下来,就可能成为其成员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由于身份限制,农民工并不能自动成为城市中已经存在的组织(如工会)中的成员。虽然农民工中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临时性组织,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及其自身思想意识的影响,其组织化程度很低,多为处理某一具体事务
而形成的松散的临时性团体,农民工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组织的解体。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要求一定的投资,用以形成义务和期望、责任与权威以及规范与惩罚等各种结构。而由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人们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尤其是农民工具有流动性,为创立、加入或者维持某种组织而进行投资被看作是一种负担。组织资源的缺乏,使得进城农民工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不仅缺少组织及其成员的支持,也难以集聚与外部世界抗争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利用关系获得信息、资源以及进行社会流动是人们节约成本的一种选择。格兰诺维特利用对美国白领的求职调查证明了其关于利用弱关系往往能够提高向上流动的机会的假设。而西德社会学家伯恩德·韦格纳对西德职业流动的研究发现,在流动前地位较低的蓝领工人可以通过强关系找到较好的工作,而流动前地位较高的白领职业、经理阶层则通过弱关系找到较好的工作。边燕杰则通过他在天津市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其强关系在求职中的巨大作用。当某人的社会网络被用于求职时,他所获得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教育水平和嵌入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而他所拥有的网络主要取决于他的先赋地位(家庭背景)。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找关系”、“拉关系”、“托关系”成为他们求职和获得职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有意识地建造个人的关系网是农民工在不具备城市先赋人际关系网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现实选择。然而,农民工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关系建立中处于弱势地位。除了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的缺陷、城市居民对农民固有的偏见和歧视外,我们可以从理性角度出发,假设人们建立关系是出于一种交换的目的,由于农民工所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占有资源较多的阶层在交换关系中处于“给予”多于“获取”的状况,在一般城市居民看来,与农民工交朋友太麻烦,代价太大。这种心理表现的一种现实情况是,普通城市女青年通常不愿意与来自农村一般男性甚至是大学生建立恋爱关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关系链中双方资源的不对等,她们以及她们的家庭认为与农村人结婚麻烦事多。尤其是,信任是人际交往和关系建立的前提,对农民工缺乏信任,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的建立和扩大。由于城市生活引起的大量接触,城市中的社会关系趋向于匿名、表面化和短暂化。农民工的流动性质以及对在各类媒体污名化叙事下所塑造出的农民工负面形象的社会记忆,使得城市居民出于一种本体性安全的考虑,对农民工避而远之。这样,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形成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形成孤岛经济效应,陷入一种严重的发展困境。而且,在农民工群体内部,也由于其职业不稳定、流动频繁和在城市住所居留的短暂,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缩小,绝大多数限于以农村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乡群体。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在很多时候,关系的力量超过制度的力量。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其难以建立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会关系网络范围狭小、同质性强,以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限,使得他们在求职、获取帮助以及情感支持、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等方面都比一般城市居民困难,从而使得他们经常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游离于城乡之间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三、增加农民工社会资本,加速农民工市民化
在向城市移民的过程中,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积累的关键因素在于其社会身份。农民身份不仅造成农民工先天的社会资本不足,而且在其影响下,也使得他们难以被城市组织吸纳,更难以建立自己的组织。同时,由于身份信任的限制,个人关系网络难以扩大。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社会资本严重不足。
社会资本虽然不是一种直接可以使用的资本,但由于其具有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特点,因而在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对城市的适应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使农民顺利转变为城市居民、适应城市生活,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1.取消户籍区分,让进城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资本。社会身份作为一种资本,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群各自所拥有的特殊权利和社会资本范围。在户籍区分制度下,农民工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都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况是与农民工的农民身份相联系的,作为农民工,其社会资本先天不足,这是农民工在城市经常陷入生存与发展困境的根源。应该打破户籍限制,平等对待农民工,在农民进城工作后给予其临时市民资格,临时享受一般市民应该享受的待遇。并且,要在农民进城工作一段时间后(如一年或者两年,但时间不能太长),根据农民工的意愿和申请,及时且不附加任何条件地给予其获得正式城市市民资格和享受市民待遇的权利。
2.加强进城农民的组织建设,增加其社会资本。进城农民的组织建设是一个难题,其关键障碍:一是农民工的农民身份,二是农民工的流动性,三是农民工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素养。因此,一方面要打破身份隔离,将农民工当作普通市民,将其吸纳进已经存在的各种工会团体和组织;另一方面,要及时给予其市民资格及相应的福利待遇,减少其流动性;第三,政府和社会要积极努力,在组织专门的社会团体对他们进行帮助的同时,积极宣传和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引导他们提高对存在于组织中的社会资本的认识,从而自觉自愿地对这种社会资本进行投资。
3.通过政府干预和社会动员,鼓励构建各种层次的对话网络和沟通场所,扩大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农民工的个人关系网络与农民工个人交际能力直接相关,但是,对农民的偏见和长期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所造成的农民工形象污名化,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通过构建各种层次的对话网络和沟通场所,可以打破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由于不信任而产生的隔离,引导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正常的交往,从而扩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也可以提高农民工城市居民化的速度。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