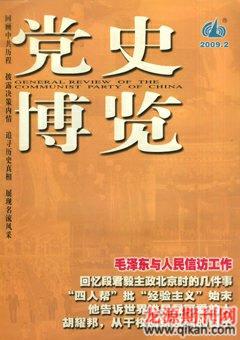我在“中央读书班”的见闻(下)
刘 岩

遵化参观引发了两种思潮的碰撞
1975年6月4日,第四期读书班学员和教职员工组成2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路经天津蓟县到达河北省遵化县。由于路途较远一天打不了来回,故决定用两天时间,除参观原计划的西铺生产大队外,另外增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沙石峪生产大队。
西铺生产大队的前身是王国藩领导的“穷棒子社”。1952年,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共产党员、村干部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仅有的一头毛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面对冷嘲热讽,王国藩不予理睬,带领23户农民发奋努力,依靠“三条驴腿”,从上山砍柴换农具做起,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第二年,合作社社员就发展到83户。没几年,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穷棒子社”的创业之举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他写按语说:“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王国藩历任西铺乡高级社主任,遵化县建明公社社长,遵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遵化县委第一书记,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书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王国藩。王国藩的事迹被选入当年的小学课本。他的名字在国内家喻户晓,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作为时代风云人物,王国藩的生活却非常俭朴,始终没有改变农民形象,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到中央读书班学习,穿的仍然是那身农民的装束:黑色对襟上衣,黑色土布裤子,老伴做的黑布鞋。从1967年开始,及至担任了一系列高层领导职务后,他仍然不脱离农村,不脱离生产,不拿工资而记工分。
王国藩在读书班的学习讨论中少言寡语,但在介绍自己的生产大队时却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讲得有声有色。学员听后,大多数觉得“受教育很深,上了一堂最生动最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课”,但也有少数人提出不同意见,引发了两种思潮的碰撞。
一是如何看待生产队之间收入差别的矛盾。据王国藩介绍,20年来,西铺生产大队通过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进技术管理、开展多种经营等措施,增产效果显著,当年的工分值达到2元,比其他生产大队高出1元左右。对于这种差别,多数学员认为是正常的,属于生产力发展范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搞好“传学赶帮带”,使后来者居上。但也有部分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艰难的任务”。这种观点的根源来自张春桥的歪论。学员参观遵化前两个月,《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发表了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给“左”倾思想较重的一些人提供了理论武器。他们拿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帽子到处扣,把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差别、生产队之间自然条件的差别、生产经营收入的差别,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数学员特别是绝大多数部队学员,不赞成他们的说法。
二是如何看待王国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经历。6月4日下午,王国藩带领学员参观一片被改造的农田时,在一棵大树下即席介绍了西铺生产大队的发展历史。其中提到,“文革”初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帮造反派跑到西铺村,扬言王国藩领导的生产合作社是“假典型”,王国藩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煽动社员搞所谓“揭发”。经过一番折腾,实在无法找到“假典型”和“走资派”的事实根据,就说王国藩是“慈禧太后亲戚的后代”,胡搅蛮缠,连续围攻王国藩好多天,搞得无法生产和工作。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67年2月5日利用陪阿尔巴尼亚贵宾视察沙石峪生产大队的机会,去西铺才给王国藩解了围。对王国藩的这段经历,在学员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大部分人认为,王国藩“顶住一小撮极左分子妄图把‘穷棒子社砍倒,把西铺大队打成‘假典型的罪恶企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表示钦佩。但少数人却认为,这是王国藩“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的表现,表示反对。
“王洪文办的读书班”引发调查取证风潮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解放军除铁道兵以外的所有单位和部分地方单位,纷纷派人到总政治部调查取证,刮起一阵调查“中央读书班”学员的风潮。仅我接待过的就有上百批,被查证者达146人。为什么凡是到“中央读书班”学习过的干部几乎都要被查证呢?原来,军队某领导机关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以及会议总结、简报等文件中,将“中央读书班”改称为“王洪文办的读书班”。读书班的名称问题为什么会引来全军性的查证风潮呢?我们看了下面这个故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1985年,军队整党接近尾声。福州军区某集团军王军长在1973年当师长的时候曾入“中央读书班”第二期学习,回部队后一直风平浪静,顺利发展。没有想到,在1985年底写整党材料时遇到了麻烦。在集团军党委会上有人提出,王军长曾经读过“王洪文办的读书班,但在整党材料中没有交代这段历史”,因此不投通过票。当时,我的胞兄刘政(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原参谋长,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被全军整党办公室派往南京、福州军区“整党调研组”任组长,参加了王军长的这次整党“过关”会。眼看会议陷入僵局,他忽然想到我曾在“中央读书班”工作过,就打电话问我:“你参加过的那个读书班,性质到底是怎么确定的?”
我告诉他:“请你们查看《邓小平文选》第12页《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一文的题解,题解对读书班的性质有明确的说法。”于是,党委会上很快有人找来《邓小平文选》,打开一看,题解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这下子参加会议的人们才统一了认识,通过了王军长的整党材料。
说起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调查取证,真是五花八门,一言难尽。找我们查证者,持什么样调查动机的都有。概括起来看,可分为三类:一是持客观态度。因为领导机关宣布了,读书班是“王洪文办的”,所以应当到总政治部问问情况。持这种态度的是,你怎么说他怎么听,不带任何框框,这是多数。二是想让你多说“好话”。比如某野战军有位副政委,有人说他在读书班期间与王洪文、七林旺丹单独合过影。我写证明材料说:“我没有看见过和听说过××与王洪文一起照过相。七林旺丹与××不是同期学员,不可能在读书班合影。”取证者不太满意,恳求我写得“肯定一点,就说没有照过”,我表示我不能保证在我的视野和听觉以外发生的事情。第三种情况是带着倾向性搜集材料。不按他的意图说事,就反复提问,甚至纠缠,表示不满。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有一位研究所的政委参加过第二期读书班的学习,粉碎“四人帮”后成了被审查对象。1977年11月19日和12月17日,研究所两次派人到总政治部调查这个政委在读书班学习时的情况。其中,除了几件“大事”,比如关于去公安部工作的问题、王洪文是否听取过有人对他学习情况的汇报、他在学习中是否联系过本系统的实际、江青是否接见过他所在的工作小组等等,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进行查证是形势所需,非查不可。但是,调查人员反复查问的另外一件事情,就使人有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感觉了。他们问,1973年10月6日读书班开学那天晚上,叶副主席点到这个政委的名字时,“问过他什么问题没有”?对他和他所在的研究所“作没作过什么指示”?其目的很明显,如果叶剑英问过什么问题、作过什么指示,他回去没有传达,那就会给他扣上“目中没有叶副主席”、“封锁叶副主席的指示”的大帽子。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是全党和全国的第二号人物,军内很多单位把对待叶剑英的态度作为区分大是大非的标准之一。这个研究所的调查人员,无疑是想在叶剑英对学员“点名”的这个“鸡蛋”里,挑到一点“骨头”来。
读书班第二期学员中有一位海军航空兵师的师长,性格开朗,谈吐幽默,善于同人交往。1977年12月24日,海军政治部派人到总政治部集体了解海军曾进入读书班学习过的12个人的情况。我和一起到读书班办公室工作的王复初干事经领导审核同意,向海军介绍了包括这位师长在内的12个人的学习情况,并提供了12人所写的“学习小结”打印件。但是,这个航空兵师的调查人员并不满足。1978年1月7日,来人进一步查证,列了10多个问题的调查提纲。我和王复初对其中6个我们知道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写了书面证明材料。1月14日,该师的调查人员又来到总政找到王复初干事,查问他们师长“跟庄则栋是否一起照过相”。来查证者是这个师的一名副师职干部,我们从他1月7日的查问中就感觉到这个人有急于将师长整下去并取而代之的图谋。我们回答说:“庄则栋当时是世界乒乓球冠军,国家体委主任。周总理还曾到读书班找他谈过工作。且不说我们不知道他俩是否一起照过相,就是慕名与庄则栋照了张相又算得了什么问题?”最后,这位查证者悻悻地走了,以后也没有再来。
到公安部参加整顿和破案工作
由于公安部是专政机关,加上时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李震意外死亡,所以公安部的事情让大家感到十分神秘。在读书班学员参加该部工作的问题上,三年之内两次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第一次是1973年10月读书班组建赴公安部工作组时,受到读书班办公室和学员党支部的高度重视,对去公安部工作的学员和工作人员是经过严格筛选才确定下来的。第二次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读书班学员去公安部的事情又成了一些单位清查工作的重点。部队去公安部的9名学员都不止一次地被查证过。地方学员中几名去公安部工作的学员,如广东的梁锦棠、辽宁的王景升、北京的张世忠等,也有人找我调查过他们的情况。我作为行政工作人员,奉命跟随学员工作小组去过公安部十几次,听过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整顿工作和破案工作的介绍,也听过学员工作组向党的核心小组的两次汇报,对面上的大体情况了解一些。这里把当时大家都感觉十分神秘而又非常重要、必须调查清楚的若干情况略述一二。
“学员去公安部是谁交代的任务?”这是每个查证单位共同提出的首要问题。学员去公安部事先并无计划安排,是李震死亡以后临时增加的任务。这项任务,从当时的表象看是王洪文直接交代的,但是若干年后李震之死的结论定案后,人们才知道它是周恩来最后拍板的。过程是这样:1973年10月29日吃完晚饭,学员在上晚自习前,很多人逛商场去了。这时王洪文突然跑到读书班,要值班的同志立即通知各小组24个召集人到小礼堂集合。我走进小礼堂时,看见王洪文已坐在一张桌子前等待。人到齐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李震被干掉了!”大家听了都很震惊,一个个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他继续讲。他说:“这个事要保密,你们不要记录,不要外传。李震百分之九十九是他杀。中央对李震很信任,重大案件都交给他办,这是政治上的最大愉快,所以他不会自杀。”他还说,李震“死前情绪没有异常,死后现场被破坏了”,等等。他说这些话的倾向性很明显,就是一口咬定李震是他杀的。最后,他要求从读书班学员中“划一部分人到公安部去”,参加公安部的整顿和破案工作。
王洪文说完就从礼堂出去坐车走了。王洪文走后,办公室的两个负责人和两个党支部的领导成员立即开会,研究选择赴公安部工作组的名单。名单确定后,从第二天开始这部分学员就不再去原来的工作单位了,而是在家里待命准备随时出发。然而一直等了半个多月,直到11月16日才有了消息,开始进入公安部。
当时大家都很纳闷,原先王洪文急急忙忙亲自跑到读书班下达任务,可是前往公安部的第十四组组建起来后却半个多月没有动静,谁也猜不透是什么原因。若干年以后,被周恩来点名调往公安部参与主持破案工作后留在公安部工作的杨贵发表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才让大家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杨贵说:“在11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汇报了派往公安部工作的人员名单。周总理看过名单后说:‘都是工人和部队的同志,我看还是让熟悉地方工作的杨贵同志去吧!”原来,这半个多月是等王洪文向政治局和周恩来汇报呢。得到政治局和周恩来认可后,学员便于当天进入公安部。这就是说,第十四组去公安部过程的正确表述应当是:“派学员去公安部,开始是王洪文到读书班布置的,最后是政治局和周总理通过批准的。”过去,曾经把第十四组学员说成是“被王洪文派去公安部”的。这样就把他们与王洪文挂上了钩,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牵连,在运动中被反复查证,在精神上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应当向他们道歉。
提到上述问题,不能不说说王洪文在处理学员问题上的另一件事情。第三期读书班开学不久,学员中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上将身体不适,我带医生去宿舍看望,一量血压,高压200多,低压100多。医生说:“王司令的血压太高了,危险性很大!”我与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商量,建议赶快将其送医院检查治疗。但是王建安不愿住院,提出退学回福州或到总参招待所休息。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便给王洪文的廖秘书打电话,让他请示王洪文怎么处理。过了一天,廖秘书回电话说,王洪文报告了周总理,总理指示:“王建安不要回福州,也不要去招待所,有病可住301医院治疗。”这件事同样说明,读书班涉及学员的较大问题时,王洪文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的,他得向总理请示报告。在清查“四人帮”时,有的单位对王洪文的权力估计过高,把“中央读书班”改称“王洪文办的读书班”,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
“去公安部学员的名单是怎么确定的?”这是各单位查证工作中的又一个重点问题。查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搞清楚他们单位被查证的对象与“四人帮”一伙人有没有瓜葛。
从军队学员中抽调组建第十四组的工作,是读书班总负责人、中央组织部的牛树声会同总政治部在读书班办公室工作的四位同志一起研究的。当时研究时,在桌子上摆了三种学员名册:一是简历名册,二是学习编组名册,三是原来参加工作的分组名册。几个人在这三种名册之间翻来覆去查看,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四个学习小组之间抽调要均匀,三个小组各抽2人,一个小组抽调3人;二是在13个工作小组中,从部队学员人数相对较多的9个小组中各抽1人;三是所抽对象尽量是政工干部,并且头脑比较灵活、反应比较敏锐。别看区区9人,挑选、搭配起来还真费了一番周折。
“学员去公安部后干了些什么事情?”10月29日深夜,两个党支部讨论通过所抽调的18位学员名单后,前往公安部的第十四组宣告成立,确定了两名牵头人: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军副军长张英才,中央候补委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张世忠。下面分编为9个小组,每组由军队和地方各一名学员组成,规定进入公安部后以小组为单位活动,个人不得单独行动,不得随便表态,不得暴露公安部的秘密。待命半个多月后,11月16日牛树声亲自将第十四组送到公安部,首先在会议室互相介绍了双方的有关人员,然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向学员介绍了李震之死的有关情况,并带领大家察看了李震的办公室和死亡现场。
读书班学员进入公安部之前,李震案件的侦破工作已经开始。参加侦破工作的,除公安部本单位的人员外,还有从广州、天津、上海、北京借调来的侦破专家。由于王洪文竭力坚持“李震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所以对一些与李震有关系的人员都进行排查,要求每个人说清楚李震死亡前后几天自己在做什么、都和哪些人有过接触、发现过什么可疑现象,等等。公安部机关上上下下都非常紧张。学员在调查研究中开始听到的基本上是“他杀”的声调,后来张英才参加了华国锋主持的一个会议后,回来给大家打招呼说:“对于李震的死,以后不要说死了,他杀、自杀两种可能性都有。”这以后,学员们听到的就是两种声音了。
12月30日,读书班学员撤出公安部时,李震死因尚未能作出结论。以后从杨贵发表的文章看到,他和技侦专家经过艰苦细致的反复论证,李震自杀的结论无可置疑。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正式批准了公安部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案件的报告。
上海组学员到总政治部“放火烧荒”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一书提到:“江青‘放火烧荒,在总政治部的火很快点起来了。王洪文专门派了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上海金祖敏、周丽琴、万桂红、单文忠等人进驻总政治部,直接参与批林批孔运动。”“中央读书班”上海组个别学员进驻总政治部搞“批林批孔”,从事先的阴谋策划到进入后的不正常活动,鬼鬼祟祟搞了好多见不得人的名堂。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多次予以揭露,但由于受种种复杂因素的干扰,没有能够充分曝光。他们在总政的“放火烧荒”中暗中搞了些什么活动一直是个谜,我当时所揭露的只是从外表上看出来的四个问题。
一是上海组进驻总政,是王洪文在背后阴谋策划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开学不久,中央组织部按照有关方面的决定,开列出本期学员参加工作的10个单位,让办公室提出各小组分配所去单位的意见。3月18日晚办公室研究时,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依照学习小组和所去单位排列的对应顺序确定。与上海组相对应的单位是总参谋部,与总政治部相对应的是沈阳组,这样上海组就分到了总参谋部。19日上午,办公室总负责人王桂冀找到我说:“老金(金祖敏)提出,他们小组参加工作的单位变一下,改去总政。”我说:“这个组去总政不合适吧。他们组有十二军副军长任保俗,现在总政正在揭批李德生和他老婆曹云莲,最近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宝琦(总政原组织部长)也被揪回总政参加运动去了。他们都是十二军的熟人。过去搞土改,工作队有熟人都要回避,上海组也应当回避吧?”王桂冀听后说:“是吗?那给老金说说吧。”不一会儿,王桂冀从金祖敏住的学员楼回来了,对我说:“老金说了,任保俗只是个组员,不负责全组的工作,去总政没关系,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吧。”当天下午,学员支部召开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金祖敏宣布各小组参加工作的单位时,把10个组工作单位的分配都说成是“办公室建议”,明目张胆说假话。
二是排斥异己,将陈再道、任保俗赶出第四小组。任保俗回避总政运动本来是我首先提出的,目的是将我不同意上海组去总政作为一种方法,来表明我对上海这帮人的政治态度,根本就没有打算能够阻止他们的图谋。果不其然,3月28日晚上,金祖敏在几个小组召集人“碰情况”的会上突然提出,他们组的陈再道、任保俗总政熟人多,工作不方便,建议调整。我心想:“不是说不妨碍吗?”王桂冀也只好无奈地打电话请示中组部郭玉峰,郭表示同意。经办公室研究确定,任保俗调到天津蔡树梅小组,陈再道改去总参政治部参加那里的“批林批孔”运动,归孙玉国小组领导。
三是违犯保密规定,拒绝上缴去总政工作的笔记本。各小组学员参加工作的笔记本都是专门编号发放的,事先明确规定,工作完毕要统一收回缴保密室登记处理。但是,上海组去总政参加运动的笔记本一直不上缴,保密员王长顺向我反映,我让他催缴。催了几次还是拖着不缴,我便将情况反映给王桂冀。不知道王桂冀是怎么给上海组说的,不久王长顺告诉我说,“四组的笔记本他们自己销毁了”。这里面如果是光明正大、没有鬼的话,怎么能违犯保密规定“自己销毁”呢?
四是参加总政运动的工作报告,违犯规定径送王洪文。各学习小组参加运动的工作报告,规定所写内容办公室没有过问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向中央呈送时,应一律通过办公室的机要室登记,然后通过机要交通上送。其他各组都是这样执行的,唯独上海组对参加总政运动的几次报告都搞得十分诡秘,既不在机要室登记,也不通过机要交通上送,都是他们自己秘密地单线直接送给王洪文,很不正常。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安徽省军区等单位派人到总政治部调查周丽琴、万桂红、单文忠、王乐亭等人到总政治部“放火烧荒”的问题。总政“清查办公室”每次都不例外地批上“请刘岩同志接待”。我每次都只能重复我从外表上看出来的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在总政“放火烧荒”的主要目标是整李德生、田维新等人,我是跟李德生从军委办事组到总政工作的,人家把我划在“李德生线上”是尽人皆知的事。担任上海组教学工作的中央党校教员周养儒、王儒化就曾听金祖敏说过,“刘岩根本没有资格来中央读书班工作”。事实上正是这样:他们每次到总政机关,所依靠的都是少数“左派骨干”,根本不与广大机关干部接触;我是人家的对立面,他们与我格格不入,处处设防,背后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怎么可能知道呢,只有“左派骨干”知晓。然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左派骨干”,一部分人在揭批“四人帮”时仍然还是骨干分子,如果彻底清查上海组到总政“放火烧荒”的问题,势必“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是上海组到总政治部“放火烧荒”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查的根本原因。
我干了两件涉及江青的“玄乎”事
我参加“中央读书班”办公室工作期间,江青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按政治局的分工,她不管读书班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到过读书班。但我却干了两件涉及江青的“玄乎”事。
第一件,向组织提出吹捧巴结江青的××学员不宜提拔。1974年1月25日,第二期读书班学员行将结业时,江青在中央直属机关两万人(包括读书班学员)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叫:“孔孟之道有三纲五常,其中一纲就是对着我们妇女的!”1月27日,在政治局接见读书班学员的会议上,她把两天前叫嚷“孔孟之道……是对着我们妇女的”的起因抖搂了出来。她在会上宣布,河南省唐河县有个女初中生(张玉勤),因为外语考试不及格,遭到批评,想不通投河自杀了。她说女孩子是被“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逼死的”,高声呼喊“我要向全国控诉”!
1974年3月,第三期读书班开学后,“张玉勤事件”的余波尚未过去。部队学员中有一个特种兵师的政委,从第二期学员那里得知江青的上述表演后便投其所好,注意搜集积累《内部参考》上登载的关于全国妇女“受迫害”的资料,准备在妇女问题上做文章。为了讨好江青,他对读书班中的妇女学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统计,在“学习小结”中写道:“这期中央读书班17名女同志中,有11名中委和候补中委,其他有省、市团委书记和各级负责同志。”同时在小结中不惜篇幅、不厌其烦地引用全国各地所谓“迫害妇女”的事例,比如:“有个生产队,妇女因婚姻不自由,一条绳子吊死三个”;“湖南省汉寿县一个‘铁姑娘小组,因得不到同工同酬受歧视,九人集体自杀”;“吉林省发生一起严重的拐骗贩卖妇女的案件”,等等。他别有用心地写道:“如果这种陈旧的东西发生在上层,它对革命的危害就更大。”影射之意,昭然若揭。更为离谱的是,他超出了当时“四人帮”的舆论调子,吹捧江青说,“批林批孔”运动这个革命烈火“是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点燃的”!
我看了他的这篇小结后感到很不正常。作为一个部队的师政委,党和军队的很多事情不去写,偏偏在妇女问题上做文章,明显是为了讨好江青,图谋得到江青的青睐。所以,读书班结束后,我便将这篇“奇文”交给总政干部部的领导同志过目,目的是引起部领导对这个人的注意。1975年8月,全军调整领导班子,这个师政委不知是什么人提名,被破格提升为某兵种副政委。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命令尚未公布之前,带着他的“学习小结”找到新上任的总政干部部部长梁济民,说:“请你看看这篇东西。这个人品质不好,企图通过写学习小结吹捧和巴结上面的什么人(当时不敢直呼江青的名字),这样的干部不宜重用!”梁部长接过“学习小结”,答应看看。第二天,他将材料退给我说:“军委和党中央已经批准这批干部的任免,不好改变了。”
第二件,主张退回江青在天津的讲话材料。1974年6月底,读书班机要室莫明其妙地收到天津市委寄来的150份江青在天津的讲话材料,经过查问,原来是读书班办公室值班员擅自向天津市在读书班学习的学员要的。天津的这位学员虽然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天津市委和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但她是名纺织女工,是以劳动模范的条件进入领导层的,缺乏机关工作经验,糊里糊涂地转述了索要江青讲话材料的电话。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她和邢燕子等天津的学员收到市委寄给她们有关江青在天津讲话的材料后,到读书班值班室给天津市委打电话(整个读书班只有这一部能打长途的电话),告知江青在天津讲话的材料收到了。值班员在一旁插话说:“也给读书班其他学员每人要一份吧。”天津的这位学员不假思索地把值班员的话顺口传了过去,并说是“读书班办公室要的”。
7月2日,事情的原委搞清楚以后,我向办公室总负责人提出:“年初‘一•二五大会上批林批孔动员的讲话录音和材料,毛主席不准下发(其中有江青的插话)。江青在天津的讲话我们要来发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就等于是通过我们这个渠道把江青的讲话材料发到全国了。所以我觉得读书班绝对不可以干这种事情。”总负责人问:“那怎么办呀?”我向他建议,将办公室有关人员召集起来开个会,指出值班员擅自向天津学员要材料是错误的,要他作出检讨,并向天津的学员说明情况,收回索要材料的意见,把材料退还天津市委。但是,总负责人顾虑重重,说:“这可是件大事,得请示王副主席确定。”于是,他向王洪文办公室作了报告。
7月3日,读书班办公室总负责人告诉我,王洪文办公室回话了,答复是:“请读书班办公室定。”王洪文在这里耍了滑头:毛主席5个月前的批示在案,他不敢公然违背“最高指示”,同意给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学员散发江青的讲话,但骨子里又希望扩散“四人帮”的东西,如果读书班办公室决定发了,以后万一出了问题,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
如何执行王洪文的上述答复,读书班办公室当即进行了研究。我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其他几位同志也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样就让机要员王长顺将江青在天津讲话材料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天津市委。(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