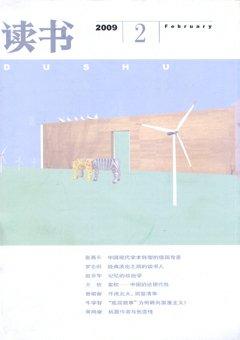对席的诚恳与周君的鼻子
张承志
至今我都觉得难以想象:太宰治,居然曾经用一本小说写过鲁迅!
它篇幅不长,印成袖珍本后约有一百六十页。它以中国人熟知的鲁迅留学仙台故事为题材,写成了一本以留学生周君为主角的小说。连题目也用“惜别”,藤野先生给鲁迅的题词。出乎意料的情节是没有的,小说只把散文《藤野先生》透露的旧事略加敷衍,加之浓稠的、叙述的淹灌。
但太宰治和鲁迅都是本国名家,事情便有趣了。某些日本人会以为,如此大家用墨于中国人,太过罕见甚至屈尊;中国人则会警觉傲慢的屈尊,更对小说读得仔细。
一九四三年自汪伪大使升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重光葵,鉴于逼近的日本败局,主张给与亚洲诸国“独立”、标榜“解放亚细亚”乃是战争之目的。同年一月,日本向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宣布放弃治外法权、交还外国租界。接着,由伪满、汪伪以及菲、泰、缅、印诸“国”参加的大东亚会议召开,发布五大宣言,呼吁东亚亲善、打倒英美殖民主义。
会议号召主旋律文艺。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向作家要求,歌颂和表达时代的最强音,写五大宣言,并承诺提供金钱、纸张、采访便利。一句话:当好作家的好后勤,为主旋律创作提供一切支援。于是众作家应募、报国会审选,还发出正式委托书——其中就有太宰治的《惜别》计划。这一篇承担的任务是,以小说表现五大宣言之第二项:“独立亲和。”
那时在日本,鲁迅的作品已被大规模介绍。太宰动笔前接到了竹内好寄赠的新著《鲁迅》,专家竹内好披露的某些鲁迅真实以及竹内笔尖横溢的一些自负和粗暴——大约使他不快。太宰治把竹内主动赠书一事写入后记,表白了对竹内好的敬远与拒否。
他未改初衷,“如少年之势开始了这一工作”。太宰治的自信,是比“五个二”更重要的缘起。他提交的《〈惜别〉之意图》,写的是严肃的:
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轻薄煽动,只以所谓洁白的独立亲和态度,正确且慈爱地描写年轻的周树人,让现代中国年轻知识人读,使之抱有日本存在我辈理解者的感情,而效力日支全面和平,其功远胜百发弹丸——此乃吾之意图。
太宰治话里的一丝较真,不易察觉。这里藏有一九四四年底大东亚上空败色已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自省和感悟。其时鲁迅正在日本声名鹊起,他初读小田岳夫《鲁迅传》,曾有相投的直觉,感到鲁迅“和自己一样”。他想尝试别样的“洁白”口吻,纠正姿势,诚邀对座,与中国对话的构思,正酝酿形成。
这一篇尚能分类小说,是因为它虚构了一个两人世界。在活脱一本对话录的作品里,日本式的优越被摒弃了,宛若身在乌托邦,一对朋友相濡相知。
败战就要降临,不妨留下预言式的篇什。我猜,此即太宰治接受官方征稿的动机。
此外,他坚信若想写好对方,不是靠竹内好式的理论甚至不靠背景资料,写好对方的唯一条件,是揣度的直觉和作家的感悟。心有灵犀高于一切,而“灵犀”,并非竹内好而唯太宰治才拥有!
这样太宰怀着方法的自负信笔写来。词语中屡屡可见他的思路。在小说的前台,“我”和“周”是一对挚友;而周与“我”背后的模特又并非等闲之辈——于是刻意的平等,就印在了纸背。
——学生会干事津田粗暴干涉“我”与周的交往,并对藤野先生信口雌黄。“我”不能忍受,跑去找藤野先生对质,于是引出了先生对友邦邻人做好事要“只做不说”(不言行)的一番抒发。
“……支那保全,从来乃是我国的对支国策。……正是支那,才有伟人辈出。我们想到的事,支那的先觉者们早就认真思考过了。……家风或国风,它的传统绝不是能中断的。东洋本来之道义——得这么称呼它——的底流,不管何时不拘哪里,总会存在活着。在这根本之道上,我们东洋人全都连在一起。也可以说,是背负着共同的命运。……相信这个,尽兴活泼地和周君交往吧!没有什么事值得想得太多。”
……我身上袭过冲过去与先生握手的冲动。但我忍住了,礼仪端庄地道了别。忽然:“你的脸,我好像没怎么见过?上过我的课吗?”
“哎,”我破涕为笑地,“那个,从今以后。”
“是新生呀。行啊,大家都互相激励!津田君那里我去说。我也是,在班会上说了多余的话。好罢,以后就只做不说吧!”(《惜别》,299页,新潮社)
当周君的“朋友”们,哪怕已经从卢沟桥和太平洋撤退,但是尚退守在“大东亚防卫”、“解放亚细亚”的一线时,无论谁,下笔就会画歪周君的鼻子。但要紧的是,一个“我”已然诞生,他是和周君抵足而眠的同窗,是亲密交谈的伙伴。就像他送给周的刊物名字“新生”,他是日本的一代新人,甚至是新生的日本。一部《惜别》中,最有趣的人物不是“周”,而是“我”。
很难说太宰治写下那个名字时影射了日本。至少从文字中读不出来。但细究太宰治接受国家任务的始末,能触碰到作者的一种虚无、古怪、安详,尤其过分明亮的文笔。满纸的无邪,更酷似缄默。
太宰治无意言及日本的危机。他把自己藏得很深,在亮色的、快速的、宛似不假思索的句子中,他主观地且理想化地涂鸦人物,像自欺又像描画乌托邦。流动的明亮句子,给了他麻醉,掩饰了虚无。新生的“我”和新生的周君,正隔着火海远望未来。尽管未来混沌黑暗,但他们感觉甜美。
——这些都使此一部小说更有滋味。
须知:太宰治为《惜别》去仙台取材,已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执笔已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待到出版,日本已换了人间。这部军国特邀嘉宾式的作品,是在占领军的统治下,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
像一个谜团,作家在灭顶之灾中,只字不提家国的危机,也不暗示自己个人的危机。他就像“我”:周君走了,自己也失去了目标。周君的塑造并不要紧,关键是周君一度诱发了他的热情。如今我明白了: 确实那是一次“洁白的”热情。然后跌跌撞撞地,他笔直地滑向战后的颓废。
后来看了《火宅之人》,那部电影写了太宰治的情死。二○○六年在日本,我很想去多摩川的上水,凭吊他在《惜别》问世不满三年之际、携情人弃命的地方,但是没能如愿。我不熟悉他其他的作品,但是我直觉,恰是这部受限最多的《惜别》,也许给了他一种鼓舞。因为对席的周君,给他制造了一种单纯语境,如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如洁白的乌托邦。
讨论周君的鼻子是否被画歪,多半会引起争论。
对太宰治而言,他根本没有捉摸过对方的心理。关于中国人对歧视的愤怒,他无心深入追究。他热衷的只是新生的“我”,这个“我”态度真挚、丢掉了百发炮弹,与中国人推心置腹。
画歪的几笔主要涂抹在:其一,让笔下的周君开口,支持日俄战争中“为中国浴血奋战的日本男儿”。
那个学年末的某天,也是微细菌学的课上,照例二○三高地的激战或三笠舰什么的画面打出来,我们大闹着鼓掌。其间画面咔嚓一变,出现了一个支那人因为给露西亚当军事间谍的罪,正被处死的光景。听着讲师的说明,我们又送去热烈拍手。那时,昏暗教室侧面的门悄悄地开了,我认出一个悄悄出去到了走廊的学生的身影。我一惊,是周。我觉得自己好像明白周的心情。觉得放不下,我也悄悄跟着出了教室。周的影子,已经不在走廊里了。授课时的学校,一派寂静。我从廊下的窗户往外望去,发现了周君。他在校园的山樱树下,仰面躺着。我也走到校园里,走近周的身边一看,周闭着眼睛,却意外在幽幽地笑着。
“周,”我小声一叫,周慢慢抬起半身。
“知道你一定会跟着来。别担心。靠了那个幻灯,终于我下了决心。……我立刻就回国。看见那个,不能再坐下去了。我的国家的民众,还是那么一副邋遢相呐。哪怕友邦日本举国勇敢地战斗,不知道那当了敌国军事侦探的家伙怎么想,唉,无非是被钱收买罢!但是,比对那叛徒,对聚在一圈呆头呆脑看热闹的、民众愚昧的脸,我更觉得受不了。那就是现在支那民众的表情。还是精神的问题,对现在的支那,要紧的不是什么身体强健,那些看热闹的不是个个都挺结实么?……”
“完全是为了支那的独立保全,才让日本来进行战争的……日本的青年在支那的国土上勇敢战斗,流淌着贵重的血。而同胞们却宛似隔岸观火,那漠然旁观的心理,我实在难以理解!而且同年支那青年何止不求奋起,看着他们还是一样地在清国留学生会馆耽于学舞,我终于立定决意,一段时间里,要稍稍离开留学生群,自去生活。”(《惜别》,270页、372—373页)
恰恰看是描黑的败笔里,藏着日本几代人的坚持。
这里藏着哪怕没有“课题费”,太宰治和日本知识分子也渴望一写的主题。他们需要把对日俄战争的同盟感、把对明治以来富国强兵国策的认同感,强加给中国人特别是精英。否则,崩溃于他们是可怕的。
所以其二,周树人弃医从文的选择,也就与幻灯屈辱无关。周君离开仙台不是为了抗议歧视,不是疗众救国的立志,而是为在“对席”共同实现“新生”。
所谓亚非各国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的观点是一种欺骗,不管日俄战争“对白人的胜利”怎样被渲染。“周君”生逢甲午惨败之后,身负国耻渡海,不得已以敌为师,偏偏又躲不过日俄之战,撕夺的是祖国的领土。竹内好批评太宰治“对鲁迅所受的屈辱共感太薄”,当然没有说错。
还是藤野先生把握准确。藤野先生追忆说:
周君来时虽说日清战争已然过了相当年月,可悲的是,日本还处在风行叫骂支那人“清清”小崽(チャンチャン)、说支那坏话的时代。所以同学中似乎也有这种人,有动辄对周君瞥以白眼、将他排斥的情况。(《谨忆周树人君》,载《文学案内》一九三七年三月号)
有论者强调,青年周树人弃医乃是city boy(都市青年)的“文学梦”,不能服人。除了藤野先生的证言,鲁迅的自白仍最可信赖。他在仙台教室遭遇的幻灯,使混杂的屈辱、歧视、挫折,骤然聚变,成了一种青年的发愤。
——当年日本孩童追着中国人叫骂的词儿“チャンチャン”,不知是否有对应的汉字。邹容《革命军》音译作“跄跄”,藤野先生《谨忆周树人君》的一个汉译本作“猪头三”。总之它令人费解。有日本朋友提示:抑或是歧视语“清国人、清国奴”(チャンコロ)的转音也未可知。对某民族的蔑称,大多与其族的称谓谐音,如把“俄国人”(Русский)一词谐音为蔑称“露助”(ru-suke)。抑或可作“清奴、清清”?尚不敢说。
众多的评论,都溯及了此文的缘起。太宰治强迫青年周树人对日俄战争礼赞,是否是一种奉命文学必有的缺陷呢?但是众多的日本评论,都对这里的道德问题发言谨慎。哪怕如竹内好对太宰驳难严厉,显然人们不怀疑《惜别》的文学性质及作者的节操。
这更使它令人吟味。中国,新生,这里发生了一次巧合。题材与构思的潜力,使作家能在刺刀之下,导演一个微型的魔术。太宰治的自信使人再三猜测他的意图。那里藏着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一片焦土上的思索。他表示:哪怕不入主旋律,他也会在某时一试。
再说一遍:他的方法,是以私人的作家体验,去判断直觉与自己同类的作家鲁迅。他已将周君置于平等的对席,因而他异常自信。将心比心,确是最好的方法论。
只是即便太宰治也很难做到——若想贴近一颗青年鲁迅的心,先要纠正一颗帝国文人的心;若想贴近破碎中国的心,先要纠正一颗明治以来的、胜利者的心。
竹内好云,“鲁迅死后,《藤野先生》在日本有名得能让媒体把活的藤野先生从北陆农村寻出来”。太宰治的《惜别》,也正是把一个记者钻进乡间诊所找到“我”作为叙述的开头,并以乡间诊所老医生的笔记,结构了这篇小说的。
漶漫往昔的、自己课堂上的一个留学生如今成了文豪;而且这文豪把自己视做唯一恩师、至死一直在书房里挂着自己的照片——得知了这一切后,藤野先生的回忆,写得很有意思。
他似乎有一点回避,对往事几近一问三不知。自己亲手赠送的照片、自己亲笔题写的惜别,都不记得了。他也没打算去想,为什么那学生这般记着他。但莫非老先生与鲁迅心有灵犀?否则他怎么总结得那么精彩——他说,所有一切,枝蔓衍生,只是因为一个孤独的留学生:
把那么少的亲切,当成了这么大的恩谊。
这是点睛之笔。细细咀嚼,这句话的每个字,都分寸贴切。不用说,藤野先生未曾刻意抱着“洁白的独立亲和态度”。他不过是听由习性,随心为之。但鲁迅也并未矫情,他确实也一直记着,因为弱者就是想涌泉相报。这简单平白的一句话,概括了所有昔日与今天的、留日中国学生心底秘藏的私人体验,当然也包括鲁迅。
——鲁迅就是这样追认了恩师。“那么少的亲切”,正是留日学生牢记的另一半。“藤野先生族”的存在,平衡了军国主义给日本民族抹的黑,并使每个留学生长久回味,自戒对一个民族的轻慢。
一个教骨骼学的学究,在无意识或下意识中,改笔记、话离别,实践了对“劣等民族”的平等和亲切。他全然不知一颗心为此感激战栗,不知有人因此永志不忘。鲁迅受伤的心头有一股温暖,成了文豪但不敢忘却,于是有散文《藤野先生》的诞生。岩波书店要出他的选集,译者问及篇目时,他说,选择篇目是译者的自由,只是务请选入《藤野先生》。
鲁迅的华章,是一次漂亮的中国式的回报。只可惜——愈是那些善良的日本人愈是感觉麻木,于是导致了竹内好所说,“对无数鲁迅的无数的离开仙台,无数的藤野先生并不理解”!
二○○八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