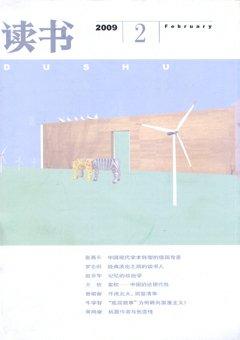被承认的问题
昝 涛
当我开始思考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土耳其军方正忙着在伊拉克北部山区进行针对库尔德工人党(PKK)的跨境反恐行动。自二○○七年底,土耳其部队多次侵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打击在那里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军方的这一行动为后伊拉克战争时代的中东地区增加了新的变数。
中东地区今天的种种问题,多数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库尔德问题也不例外。随着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本处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中东地区开始走向分崩离析,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以“托管”为名在中东地区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英国曾许诺给予库尔德人独立地位。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使库尔德人的梦想破灭了。一九二三年,土耳其与协约国在瑞士洛桑签订了著名的《洛桑条约》,这是土耳其民族运动的胜利果实,但却是当代库尔德问题的源起。根据条约,土耳其将约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划归伊朗,约八万平方公里划归伊拉克,由此确定了延续至今的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边界。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和地区大国的利益面前,库尔德人的民族利益成了牺牲品。
但库尔德人谋求独立地位的诉求从未减弱。在现代历史上,库尔德人不仅在伊拉克,而且在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都成了重要的离心力量。二○○三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在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北部,出现了一个高度自治的、准独立的库尔德地区,这刺激和鼓励了邻国境内库尔德人激进分子的分裂与独立倾向。
这其中受影响最大是土耳其。土耳其有两个主要族群——突厥族和库尔德族。库尔德族人在土耳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人口上说,除了在伊拉克,只有在土耳其,库尔德族人的人口占据相当比重,库尔德人占土耳其七千二百万人口的约20%;历史地看,自一九八四年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武装部队交战以来,双方一直打到一九九九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长达十五年的武装冲突,不仅造成了大约有三点七万人死亡,而且极大地消耗了土耳其的国力。
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者,从一开始,少数族群问题就自然地进入我的研究视野。通过作者本人在土耳其与库尔德人的接触经历,以及对土耳其近年来官方民族政策的近距离观察,这篇小文力图简要介绍和分析一下当代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我与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最亲密的接触是在二○○五至二○○六年期间,那是我第一次到土耳其。当时,我获得了荷兰方面的博士研究资助,到土耳其从事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安卡拉的中东技术大学(METU)。
我第一次遇到库尔德学生就是在中东技术大学的宿舍里。住在我隔壁的是个库尔德人,他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名叫穆斯塔法,人很热情。次日,穆斯塔法介绍了他的几个朋友给我,都是库尔德人,讲库尔德语。其中和我交往比较多的是齐亚与武夫克,但与穆斯塔法不同,齐亚与武夫克都不是土耳其公民,而是来自叙利亚的留学生。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总是作为一个小团体在活动。在我的眼中,他们的团体是很排外的,因为,别的人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只是对我有点例外,可能因为我不是中东人吧。在向我介绍他们的家乡和文化的时候,他们总显得充满激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上网,齐亚来了。他开始抱怨说今天他的英语预科考试又失败了。他说自己宁可讲土耳其语也不要讲英语。然后他又问我是否喜欢网络聊天。我说“一般吧”。齐亚又让我告诉他怎样才能在网上找中国人聊天。仅仅几分钟,他就全部学会了。就在我去了趟洗手间的功夫,齐亚就告诉我说他正在聊天室里和一个上海的女孩用英语聊天,他还让我看他们聊天的内容。那个中国女孩问齐亚是哪里人。齐亚没说自己来自叙利亚或者土耳其,而是说:“我来自库尔德斯坦。”那个上海女孩非常迷惑地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国家吗?在什么地方?”齐亚的回答是:“这个很难解释,但我坚信,在将来会有‘库尔德斯坦这个国家的。”
齐亚结束了他的网聊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纸和笔让他给我描述一下他刚提到的“库尔德斯坦”。等他画出这个“国家”的大致轮廓后,我委实吃了一惊,因为它包括近半个安纳托利亚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各一大部分。齐亚告诉我说,将来,库尔德斯坦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国家。
八月的一天,我正在宿舍的小客厅里读一本土耳其文的书,书名是《那些能够自称土耳其人者是多么幸福啊!》(Ne Mutlu Türküm Diyebilene!),这是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的一部新作,影响很大。不一会儿,穆斯塔法进来了。他抓起我正在看的书,冲着我大喊道:“不!不!不!这本书的名字就不好,它太民族主义了!”我被他的强烈反应吓了一跳,感觉他好像生气了。我问他说:“难道你不是个土耳其人吗?!”穆斯塔法没有直接回答我,他说:“我生活在土耳其,但我是库尔德人!”
土耳其的突厥族朋友们总是试图让我相信,大多数库尔德族人和突厥族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他们都以自身的经历和见闻给我举例说明。比如,他们会跟我说,他们都有很好的库尔德朋友,除此之外,有些库尔德人和突厥族人可以相互通婚。突厥族的朋友会跟我说,恐怖分子是一小撮人,而且他们确实存在;而普通人,不管是突厥族人还是库尔德人,都不太关心政治。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感觉,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很敏感和微妙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尽力避免讨论民族认同的问题。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库尔德问题与我所研究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九二三年建国以来,土耳其官方并不承认库尔德人是一个不同于突厥族的族群,禁止在学校和公开场合使用库尔德语,企图以强制同化的政策使库尔德人丧失其民族认同,建立一个族群同质化的现代国家。但土政府的政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起了库尔德人的反抗。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九七九年的评估,库尔德人的语言和文学一直在蓬勃发展,而且各种以独立为目的的组织也日益增多和活跃。
我是通过阅读伊斯玛仪·白石克齐(smail Beiki)的作品来加深对库尔德问题的理解的。我的库尔德朋友告诉我说,白石克齐是个勇敢的知识分子,他坚定和公开地捍卫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而也正是因此,他被土耳其当局数次投入监狱。白石克齐的著作也曾在很长时期内被列为禁书。最终,我在土耳其历史协会(Türk Tarih Kurumu)的图书馆里找到了白石克齐的书。
根据白石克齐的研究,土耳其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柱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假设:土耳其境内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土耳其人。白石克齐认为,自凯末尔以来,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官方政策就是同化,并且否认库尔德人作为一个特定的和不同的族群的存在。白石克齐指出,正是那些为土耳其的民族历史理论辩护的凯末尔主义者(Kemalists)编造了一些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证据,说库尔德人在起源上是纯种的突厥族;在土耳其,库尔德人一度被叫做“山地突厥人”,说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忘记了自己的种族起源。根据我在土耳其的观察,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禁忌。即使是在今天,土耳其强硬的凯末尔民族主义者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库尔德人是一个不同的民族。
一九九九年奥贾兰被捕后,库尔德工人党已经无力与土耳其军方进行正面的交锋。不过,依托伊拉克北部,近年来,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和反围剿经验,并在行动上日益恐怖主义化,越来越频繁地发动恐怖袭击,给土耳其政府造成了极其头疼的安全问题。
二○○二年上台后,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组建的埃尔多安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库尔德问题的严重性,并力图寻求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正发党虽然是一个具有伊斯兰复兴主义背景的政党,但在改革方面一点儿都不显保守。由于在二○○五年十月中旬欧盟将最终决定是否开启土耳其入盟的谈判,在这之前,正发党推动实施了与欧盟标准有关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这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库尔德人作为少数族群的权利问题。首先,正发党主导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允许在教育、文化、新闻出版领域使用库尔德语言。其次,正发党允诺加大对东南部地区的财政投入,努力提高当地就业比例和教育水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五年八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向库尔德人释放了一个新的信号。八月十二日,在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城市迪亚巴克尔,埃尔多安发表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指出,为了解决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土耳其需要“更多的民主”。在这个演讲中,埃尔多安暗示,他的政府将区分大认同和亚身份。所谓的大认同指的就是土耳其的公民身份;而所谓的亚身份,指的是种族的多样性。根据埃尔多安的说法,正发党一直以来都反对三种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本土—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埃尔多安还指出,他的政府承认在土耳其存在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应该获得平等对待。种族身份是一种亚身份,位于土耳其公民身份之下。
二○○五年十一月,在塞姆丁立的另一次演讲中,埃尔多安重复了上述看法。他明确指出,在土耳其共和国,公民身份是基本的和上位的认同。同时,埃尔多安向库尔德人承诺说,在土耳其公民身份之下,库尔德人民可以拥有将自身界定为一个不同族群的自由。埃尔多安解释说,除了是公民之外,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亚身份,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亚身份而受到攻击。他说:“一个库尔德人可以说‘我是库尔德人。”
埃尔多安的演讲在土耳其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所谓“身份之战”。埃尔多安受到激烈批评,说他违背了国家的“一个民族”政策。作为中国人,我当时很难理解为什么土耳其人关于不同身份层次的划分会有如此之大的争论。因为,对中国而言,自建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承认国内存在五十六个民族,甚至还为较大的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区。而且,在很多方面,作为少数族群,还享有政府所给予的特殊照顾。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埃尔多安于二○○五年八月去迪亚巴克尔之前,他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召见过十五个公共知识分子。据土耳其媒体说,这是土耳其领导人“第一次愿意倾听知识分子对国家事务的意见”。但是,也有人批判这些知识分子,说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领域里的专家,在决策方面,他们不够格。其实,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别挑选出来的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的名字是“少数民族和文化权利工作组”,它直接归总理办公室领导。在二○○四年十月十七日,该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列举了土耳其对少数民族问题误解的原因。最后一条是这么说的:“在提到Türk的时候,土耳其人没有意识到的是,Türk同时被理解为一个种族的或者实际上是宗教的团体。”该报告力图帮助在土耳其发展出一个“公民—民族认同”,它建议使用“Türkiyeli”(土耳其人民)而不用“Türk”这个词,用“Türkiyeli”来指土耳其公民更好,也更合适(参见“Aznlk Haklar ve Kültürel Haklar alsma Grubu” Raporu,October, 2004)。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就像在中国,尽管主体民族是汉族,但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中国”,中国公民叫“中国人”。这么做,各种不同族群的存在和权利将可以更轻松地被认可,文化的多样性也可以更容易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得以延续。
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不只认可了“库尔德人的存在”,而且,他也承认“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的存在。根据一些土耳其观察家的看法,这是一个更为大胆的步骤。这一步的重要性在于,总理已经开始将库尔德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这是一个创新。据土耳其前总统德米雷尔的看法:
在一九九○年以前,我们并没有在土耳其人民中认可种族差异性的存在。每个人在种族上都是土耳其人,这是一九九○年之前土耳其的官方话语。而我改变了它。作为总统,我曾说过,我们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那也就意味着说,在土耳其民族中,还有其他种族的存在。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是有必要的。那是我曾经说过的话。话语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但是,我并没有把那看做是一个民族问题。我只是说过,存在着不同的种族。(“Kürt realitesini tan1yoruz,”Milliyet, 17 August, 2005)
埃尔多安所采取的步骤显示了其政府在解决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恐怖主义方面的决心。在迪亚巴克尔的演讲中,埃尔多安还说:“迪亚巴克尔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安卡拉、艾尔祖鲁姆、科尼亚和伊斯坦布尔。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每个国家都会犯一些错误。作为一个大国,土耳其正在不断纠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前进。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该忽视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应该以更坚强的意志直面自己的错误。这正是我们的政府所坚信的。”其实,作为一个总理来讨论国家犯下的错误,就是宣称,过去针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是错误的。埃尔多安继续说道:“当我过去曾经因为引用了一首诗而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我就坚信,我已经向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那时曾说:‘我并没有对我的国家感到不安或者气愤。这个国家和这面旗帜都是我们自己的。而纠正诸如此类错误的一天终将到来。”埃尔多安最后说:“那些不懂得尊重思想的人,是不配讨论言论自由的。那些不能容忍自由的人也毫无资格谈论自由。这一类人和团体注定要消亡。”
在正发党的第一个任期内(二○○二至二○○七),它不仅在政策上开始向库尔德人大力倾斜,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寻求突破,力图挑战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所固守的官方民族主义的底线,从而赢得了广大库尔德民众的支持。
二○○七年夏,正发党再次以绝对优势赢得土耳其议会选举,埃尔多安得以蝉联总理宝座。正发党第二次获胜标志着土耳其已经形成了温和伊斯兰政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正发党的胜利得益于其温和且具包容性的意识形态、良好的经济表现、积极发展与欧盟的关系等等(可参见拙文:《变动不居的道路?》,《读书》二○○七年十一月)。进一步分析正发党的选情,不难发现,支持该党的选民主要来自两个群体,一是安纳托利亚的平民,他们有较强的宗教诉求;二是土耳其东南地区的库尔德人——据估计,土耳其东部有54%的选民投票给了正发党。唯一进入议会的库尔德人政党民主社会党得票率仅10%多一点,主要是因为该党只知诉诸族群政治,没有提出明确的政策路线,也不愿意与库尔德工人党划清界限,难以获得库尔德人的全面支持。当然,并不排除双方存在交集。
然而,在第二个任期刚开始不久,正发党政权就差一点夭折。二○○七年下半年,出于讨好其保守的穆斯林选民的需要,正发党企图推动修改宪法,修宪的主要内容是要使土耳其大学里的穆斯林女生获得戴伊斯兰头巾的自由。长期以来,严格执行政教分离主义(laicism,土语laiklik)原则的土耳其严禁穆斯林女大学生在校园内佩戴宗教饰物,宗教保守主义势力对此一直颇多诟病。正发党为此修宪案辩护的理由也是非常之冠冕堂皇:维护和捍卫宗教信仰之自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责任。其实,土耳其政治和社会层面长期存在着所谓的“教俗之争”,而女大学生的身体(主要是头部)成了双方争执最持久也最激烈的一块阵地,极其敏感。
正发党在议会中得到了民族行动党(MHP)的支持,顺利地使修宪案获得通过。按照土耳其法律,修宪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后,需提交总统批准。几乎与此同时,出离愤怒的世俗主义者也发起了绝地反攻。土耳其上诉法院共和国首席检察官亚尔琴卡亚在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向土耳其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以破坏世俗主义为由取缔正义与发展党,剥夺埃尔多安等五十一名政客五年内的参政权。检察官列举了一些事实后指出,“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成为违反世俗原则的焦点”,它正在危害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国之基——世俗主义(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恪守凯末尔·阿塔图克之民族主义原则的世俗国家;第四条规定,宪法的前三条“均不得修改且不得提议修改”)。
宪法法院受理此案后,引起土耳其政坛的剧烈震荡,广大民众人心惶惶,土耳其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最终,在二○○八年七月三十日,土耳其最高法院宣读审判结果:不取缔正发党,只对其进行部分惩罚。根据土耳其法律,要取缔一个政党,需经宪法法院十一名法官中的七人同意方可。这次针对正发党的诉讼案中,有六人同意取缔正发党,四人只同意对其进行经济处罚,只有一人对诉讼案说“不”。这一细节显示,正发党可谓命悬一线。对正发党而言,这个结果是“严重警告”,足以令其有所收敛,触犯世俗主义原则的修宪案也只好不了了之。
通过诉讼案,世俗主义派显示了其力量。尽管正发党的支持者疾呼这是“司法干政”,称诉讼案是凯末尔主义者的报复行动,但在土耳其现行的宪政体制下,他们也只能发发牢骚而已。双方之间的较量还将持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库尔德人也起来对诉讼案说“不”。库尔德人起来支持正发党,这向凯末尔主义者和广大土耳其人民传达了一个很微妙的信息:埃尔多安政府的库尔德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库尔德族群的民心。
然而,库尔德人没有意识到的是,正发党在挑战世俗主义方面的失利,同时也将限制其在民族问题上深化改革的动力。因为,民族主义同样也是“国家精英”们所坚持维护的一个重要原则。正发党在受到象征性惩罚和严重警告之后,在挑战凯末尔主义传统原则方面将显得畏首畏尾。在土耳其,凯末尔主义是官方的主导意识形态,这里所谓的官方是以欧化知识分子、法官、行政官僚和军队等为代表的“国家精英”(区别于选举上台的“政党精英”)。他们人数虽不占优势,但影响力非常大。他们是凯末尔主义的信奉者和拥护者。凯末尔主义的两个重要支柱就是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正发党在政治上的胜利首先就是伊斯兰复兴对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挑战,其在意识形态上对库尔德问题的重新界定,则是对凯末尔民族主义的挑战。这两个挑战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精英”的抵制。
埃尔多安政府现在能做的就是兑现其向库尔德人聚居区加大财政投入的承诺,首先帮助那里把经济搞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大开发”(GAP)。二○○八年五月末,埃尔多安透露,正发党政府计划到二○一二年在东南部的九个库尔德人聚居省投资二百亿美元,用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当地的中小企业,并加大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投入,以推动当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繁荣。
另一方面,埃尔多安政府全力支持军方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主义。它还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并正在加紧争取获得伊拉克库尔德政治势力的谅解与配合。这些趋势显然对库尔德工人党日益不利,因此,它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加紧了恐怖袭击的频度和力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显示其力量存在,并阻碍土耳其与伊拉克的接近。
总之,在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上,正发党目前有三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手段:发展、民主和反恐。发展意味着对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进行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投资与开发;反恐则体现在政府坚决支持军方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行动;民主意味着落实库尔德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的各方面权利。在发展和反恐方面,正发党已经有所作为,并仍将大有可为;在民主方面,由于传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现行体制的阻力,则相对比较滞后。但从长期来看,发展问题解决后,政治方面的民主改革将不得不再度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随着库尔德人教育水平和文化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库尔德政党的日益成熟与发展,以人权、文化权、政治权与认同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权利问题迟早都需要有一个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解决方案。库尔德民族问题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认同问题正取代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