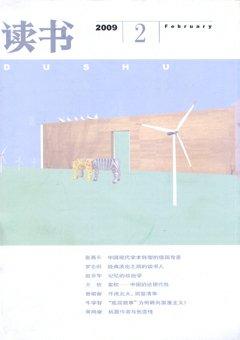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德国背景
张西平
从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和思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经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明末清初之际,西学还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在中文的话语环境中扩展影响,文人举子们也是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西学。虽然期间文化的冲突也时时迭起,但耶稣会“合儒”的传教路线,使士人在读这些“西儒”的书时尚有自己本土文化的底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李约瑟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许理和将其称为这“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
晚清时局巨变,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中国学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说:“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十二年后,到了一九一○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就是“援西入中”,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被解体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
如果我们想解释清楚今天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思想的根源,那我们必须回到晚清的“西学东渐”时代,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为此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进步,使我们开始逐步摸清我们今天所表达的学术思想、语言以及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来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著作(《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人群》)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学术路向展开的,如果将其放在近年来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想以下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在学术界首次如此清晰地勾画出了德国思想对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晚清传来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具体、深入的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讲“西学东渐”的“西学”时不太细分的,当时传来的思想是美国的思想还是法国的思想,这种学科体制是德国还是英国的,研究者关注不多,大都一概说成“西学”。其实,西方是分为不同的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区别。只有具体地研究当时“西学”的来源国,这种研究才会具体化,也才有深度。二是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时,研究者的重点大都放在中国本身。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样的重点没有一个前期对西方思潮和体制的了解,不了解当时西人所介绍的西学来源和所在国的关系,对“西学”本身的特点和“西学”本身的形成和变化注意不够,我们就很难从中国文献本身揭示中国近代制度变迁的特点。作者在书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将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放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变迁之中加以考察,使我们对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地认识。
这本书的看点之一在于此。正如作者所说:“理解德国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现代世界形成的整体框架中,才更易看得清楚。在我看来,虽然可将现代性的开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真正之潮流涌动、山雨欲来,仍当属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其标志有三:一曰传统秩序的终结,以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标志;二曰科学话语的确立,以柏林大学的建立与费希特的《知识学》为标志;三曰思考方式的呈现,以歌德的《麦斯特》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标志。”这样十八至十九世纪初西方思想的中心是德国,像哈耶克所说的一八七○年之后“六十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二十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作者甚至认为,“应该说,自十九世纪以来,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现代世界几乎可以说就是在德国思想的笼罩之下”。
我想这样的结论,这样一种对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的解释是过去许多做晚清史的学者很难听到的。德国在十九世纪对西方如此重要,德国拿什么东西献给西方现代社会呢?这就是建立在德国哲学思想之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学术体制。这样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时,就必须重视德国,就必须了解德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和历史。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到一九○○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一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这就是说,美国当时在思想和学术上是跟着德国跑的。
正是如此清晰、明确地指出德国在西方现代思想和学术体制上的地位与作用,我们才能更为深入具体地理解晚清以来我们所接受的西学的特点,特别是在学术体制确立上的西学来源,没有这样对“西学”的具体研究,对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
第二,这本书对在中国传播德国思想的主体的转换做了深入的研究。以往在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对其在中国的活动比较关注,对他们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与其本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们在华活动的影响研究不够。作者在书中再次展现了他熟悉德国近代文化和制度的特点,在谈到德国来华传教士的这种主体作用变化时他讲了三条原因:“其一,传教士思路从‘功利利益到‘文化立场的变迁,反映出帝国消解是大势所趋。这不仅表现在传教士作为政治力量的‘逐渐黯淡,同样也表现在帝国政治精英层面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其二,某种意义上具有传统延续性的‘现代性命题正为新一代传教士自觉所认知,现代的兴起乃是不可抵挡的大势所趋。”“其三,由‘帝国话语到‘现代转型的转折,为日后的‘双边学术场域互动铺垫下很好的基础。”德国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在向中国介绍西学时是直接和德国思想,和德国本身在欧洲地位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看到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是如何和德国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相通、互动,并深刻地受到本国思想的影响。德国在欧洲地位的下降和变化直接影响到在华的德国传教士的传教路线的变化。这点在英美来华传教士中也有同样的特点,他们在华的传教特点和路线直接源于其教派在国内的地位和宗教理解,不同的教派,宗教思想的不同,他们在华的传教路线就不同。以往的来华传教士研究中,这点是个薄弱环节,学者们往往只根据传教士在中国的材料来讨论他们的思想。殊不知,西方才是其思想的大本营,所在国才是其传教动力之源。传教士是跨越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我们必须对这座桥梁的两端的文化都十分熟悉,才能做好来华传教士的研究。
在书中,作者对卫礼贤从传教士转换为汉学家的分析十分精彩,对西方汉学的发展来说,卫礼贤的转型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但像卫礼贤这样将两种身份聚于一身,并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变,具有很大的戏剧性,个人命运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离,在这里显示出历史的吊诡。同时,在卫礼贤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近代中国学术的转型,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的形成与来华的汉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的建立,许多学科的形成不少都和来华的汉学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四部”到“七科”,从经学到现代人文学科,近代来华的汉学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卫礼贤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作者通过对卫礼贤和蔡元培、杨丙辰的合作完成了在中国介绍德国西学思想主体的转移的研究,说明了中国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是如何从传教士、讲学者、汉学家转换到中国本土学者手中的。同时,他以中研院和德语专业的建立与发展,说明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学科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这本书的研究中我体会到,我们在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的形成和现代学科的建立时必须考察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新文化运动,近代学术和文化的产生都是在中外文化的激荡中形成的,而以往的形成研究要么只从中国文化本身考虑,要么只从外部力量考虑,都有道理,但显然不全面。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指出中国近代学术和学科体制是在中外文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一种“学术互动”。而且更深入地分析作为西学内容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传入的具体内在过程,是如何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德语的产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对西学的介绍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主体的转变。这样作者就真实而细致地通过德国传教士和德国留学生这样两个群体展现了德国思想和文化、德国的现代学术体制和制度在中国近代学术形成的实际过程。
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是一个多重、多方面、多种力量的复杂过程,实际上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和学科的形成是多种力量集合的结果,是西学在中国长期传播的结果。从卫礼贤到蔡元培,在传播德国西学思想上主体发生了变化,但并不能说传教士从此退出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建立的历史舞台,或者不再发生作用。从同文馆的建立开始,现代学科体制就开始启动,但就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以后,民国初年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即便从德国来说,民国期间的辅仁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建立,在中国大学历史上和学术体制与学科制度的建立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说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传教士—汉学家—留学生”这种主体的转换并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立体的过程,是一个混合而不断渐进的过程。这点作者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建立的丰富历史画面。
近代以来,在“‘援西入中的大潮中,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样式”(《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复旦大学历史系编,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七年版)。从历史说,“如果把一九一○年和一九八九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自近代以来,在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学术体制之间有了巨大的间隙,随着中国自己的学问“国学”转换为各门具体学科,学科化的中国学问开始一一纳入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尽管民初关于“国学”的理解曾引起重大的争论,但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已成历史大潮,无法阻挡。
百年西潮最终导致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并由此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当下,被压抑的现代性在这个千年文化古国中以人类史前所未有的形式喷爆出来,一发而不可收,其现代化进程之猛烈,社会变迁之巨大,在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史上都未曾见。
当中华民族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环境时,文化自觉之心、之求,油然而生,此刻,中国学术界开始反思百年西潮在推动中国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同时,由此所造成的对中国思想资源的冷漠、忽略,开始反思百年西学思潮所引起的学术制度化、学科规范化在推动近代中国学科发展的同时,这种规制对中国精神把握的隔离与漏缺。争论由此而产生。
问题的实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关注国别中心的创造性发展的同时,也应思考具有‘普遍主义的问题。作为人类整体的世界,是否具有普遍主义的真理可能?或者这只是一种虚构的大同理想?如果每个民族(这里主要指以国家为载体的国家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历史和传统,并且仍将在很长时期内按这样的基本轨迹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建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与共识?它与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尝试去回答的问题。”民族文化理解和世界认知,西学学科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这些百年前曾经困惑我们前辈的问题,今天又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困惑我们。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像陈子昂在诗中所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过去已经失去,未来尚在探索。 学术从未像今天这样活跃、混乱,思想从未像今天这样分歧、多元,书写从未像今天这样繁荣而无力,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纷杂而各奔东西。但这正是伟大时代的特征, 这正是一个新思想、新学术诞生的前夜,探索中预示着光明,争论中渴望着新生。
(《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叶隽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二○○八年八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