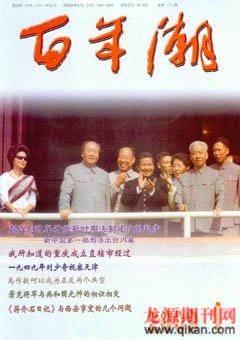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出国演出记
严廷昌
1974年11月1日是阿尔及利亚武装革命20周年纪念日。以布迈丁主席为首的阿政府决定大大庆祝一番,为此向各友好国家发出邀请。阿政府除了邀请中国政府和军事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同时邀请了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剧组,另外还邀请了朝鲜歌剧团的《卖花姑娘》剧组,以壮声势。
事情的缘起在一年前,布迈丁在访华期间的一次文艺晚会上,观看了由北京京剧团演出的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出人意料的是,在演出过程中,江青全场亲自陪同观看,还不时对剧情作些介绍。可能《杜鹃山》内容和阿武装斗争有相似之处,加之演出效果较好,布迈丁看了非常满意,当场向江青表示邀请《杜鹃山》剧组参加阿武装革命20周年纪念活动。此事正合江青心意,她立即表示同意,当场达成了口头协议。革命样板戏能出国演出,为江青企图在国际上树立自己革命旗手和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提供了极好机会。经过周密策划、精心组织,这出“样板戏出国”的活剧终于上演了。当时我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负责文化处工作,全程参与了《杜鹃山》剧组在阿的演出活动。

下机伊始遭遇尴尬
1974年10月26日,两架中国民航大型客机,一架波音707,一架伊尔62,先后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机场。波音707是宽体客机,为了装载舞台道具、服装等物品,不得不把全部座椅拆除,腾出宽大的机舱装满了大型布景和各种演出器材。代表团官员、演员、乐队和舞美等工作人员乘坐另一架伊尔62。全团共183人,这样庞大的艺术代表团是中国驻阿大使馆建馆以来所接待人数最多的团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江青为了以她的意图来控制京剧团,选择了一个能忠实贯彻她意图的人充任剧团团长,此人就是她手下的一员干将于会泳,而原来剧团的负责人担任了副团长。这位于团长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眼里只有一个江青,对外交事务极端无知,出足了洋相。当飞机在停机坪戛然停止后,他走出舱门一看,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冷冷清清的机场上,只有阿文化部对外联络处的几位官员和我大使馆以林中大使为首的几位外交官。当我们把于会泳引向机场贵宾厅时,面对阿方官员的热情欢迎,他态度冷漠,一脸不高兴。稍坐片刻,大队人马登上事先准备好的四辆大客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出发了。我“荣幸”地陪同这位文化大员乘一辆奔驰轿车,沿着海滨公路驶往阿尔及尔以西70公里处的旅游胜地提帕萨。当于会泳得知住宿地在海滨旅游别墅时,不知底细,欣然接受。提帕萨历史上曾一度是腓尼基人的商业城市,公元一至二世纪为罗马人占领,城中完好地保存着腓尼基和罗马时期的许多遗迹。我使馆同志假日常来此旅游和休闲。70公里并不算长,但在市区行驶车速不能太快,到海滨公路时已届黄昏,地中海朦胧一片,也看不到什么景色。为了解除一点车内的沉闷气氛,我不时向于会泳介绍一些沿途风光,他似听非听,情绪不高。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车队才到达海滨别墅。
这座属于阿旅游部门的海滨别墅,主要供欧洲旅游者夏天来此泡泡海水、冬天晒晒太阳度假用的,除了接待处和餐厅以外,客房像一顶顶蘑菇,星罗棋布地散落在高高低低的海边山坡上。每个“蘑菇”里有两张单人床,还有卫生间、小厨房,一应俱全,这非常适合一对夫妻或情侣使用。可是对一个团体,尤其是非常讲究集体生活的中国艺术团来说,面对如此分散的住宿条件,的确是个难题。加之初冬气候,海风吹来已带有寒意,也难怪于会泳和团部几位领导不高兴。
关于京剧团的住房问题,事前我们与阿方交涉时得知住海滨别墅,已估计到会带来诸多不便。但阿方再三解释,市内少数几家饭店仅能供各国政府代表团使用,而中国京剧团人数众多,并且在阿尔及尔只停留两天即赴外地演出,为此,阿方再三请我方谅解。此外阿方还告知,朝鲜《卖花姑娘》剧组住的是学校宿舍,连别墅还住不上呢。
为了分配住房,联络人员在昏暗的山坡上跑来跑去安排房号,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就绪。餐厅服务人员几次催促代表团到餐厅就餐。餐厅里饭菜早已准备好了,长方形餐桌上摆满了大盘的“古斯古斯”、烤鸡、牛肉、生菜等食物,这是普通晚餐。“古斯古斯”类似我国北方小米做的饭,初吃可能不习惯,加之饭菜已凉,人们胃口大减,吃了几口就不吃了,一大半食物杯盘狼藉地留在餐桌上,弄得主人很不好意思。第一天的接待离剧团大多数人的期望太远了,看来我们剧团多数同志对到第三世界国家可能遇上艰苦条件,事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位主要男演员对我说:“在国内,我们把外国客人当成贵宾,热情友好地接待。这次出国本想尝一尝做贵宾的滋味,没想到是上山下乡来了。”

江青送书
京剧团到阿第二天,大使馆按照国内代表团访阿惯例,邀请剧团主要负责人到大使馆会见并研究工作。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见。当双方人员坐定后,于会泳从文件包内取出两本装帧非常精致的线装书《古诗源》和《词综》,站起来,摆出一副庄重的神态,双手捧着书说:“这是江青同志送给林中同志的。两本书毛主席都看过,上面有主席的亲笔眉批。”林大使也站起来,微笑着双手接过两本“宝书”,说了声:“非常感谢。”这时于会泳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林大使,他以为林大使会发表一通感谢江青的激动人心的讲话。而林大使却从从容容坐下,翻开笔记本,示意大家开会。于会泳显得很不自在,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无奈地坐下,将目光从前方移开,示意副团长张科明汇报工作。
这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当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林中大使那种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的举止,令人钦佩。但于会泳不甘示弱,接着做了如下传达,说剧团离京前三天,除周恩来总理因病请假外,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了全团同志。江青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样板戏出国的重大意义,还说过去政治局中就是柯老(柯庆施)大力支持她搞革命样板戏。此外,为了显示对演员的关心,江青当场表示送给每位女同志一件“国服”(据说此服装为江青设计,俗称江青服)、一双白塑料凉鞋。江青还单独召见于会泳面授机宜,授权于会泳代表她向布迈丁主席送礼并转达问候。
散会以后,林大使独自一人背着手,在会议室内踱来踱去思考。前一天下午在贵宾室,由外交部派出担任剧团秘书的李培宜把林大使拉到一旁,悄悄地传达了时任外交部主管亚非事务的副部长何英的口信:“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要给周总理找麻烦。”林大使默默地掂量着口信的每一个字和江青送的两本书的含义,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这件工作实在太难了,但再难也要做好啊!
这天晚上,林大使叫我到他那里去一次。前些日子,对如何接待京剧团大使馆已讨论过一个方案:本来接待文艺团体属于文化处工作范围,具体工作由文化处负责,这次为了提高规格,决定派政务参赞侯德章全程陪同,我留在使馆内随时和阿有关部门保持联系。但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让我协助侯参赞,随团活动,并嘱咐在非原则问题上注意忍让一点,不要把事情弄僵。
视外交工作为儿戏
京剧团于10月26日下午到达阿尔及尔。28日上午,阿新闻文化部长艾哈迈德·塔列布即安排接见团长于会泳。这在阿礼宾安排上是十分友好的举动,而通常是代表团离阿前才安排会见。在京剧团来阿之前,为提请阿方在礼宾安排上重视,关于于会泳身份职务的介绍颇费一番周折。国内通知于的职务是“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组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职位,阿礼宾司怎能弄得清楚“组”是什么意思,外文又不能翻成“Group”,于是我们不得不反复说明这“组长”相当于政府“部长”。尽管阿方在礼宾安排上已非常照顾,但于会泳仍旧不领情,一下飞机就提出要见布迈丁主席,说要“转达江青同志的问候,转送江青的礼品”,还嫌人家部长身份低,对这次会见压根儿就不重视。
阿新闻部长接见安排在上午9时,阿方派了专车,但为保险起见,使馆又派车去接。谁知于会泳不在使馆,他带着几个演员到海边照相去了。当于会泳到大使馆时,离接见时间只剩20分钟。于会泳提出要吃早饭,林大使亲自布置厨房准备。当林大使问他礼品准备好了没有,于会泳突然想起礼品画轴还没有题词签名,并强调题词须用毛笔。于是大家忙着准备笔墨。题完词后,于会泳见旁边有乒乓球台,竟然招呼一名演员打起球来。使馆同志见此情形都很生气。于会泳在阿尔及利亚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竟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这在外交上是一次非常失礼的举动。
阿部长接见后,于会泳一再要求见布迈丁主席。林大使说,按阿方通常惯例,像京剧团这样规格的代表团,部长接见就行了。于会泳急得如丧考妣,说:“见不到布迈丁,江青同志交给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在于会泳的一再要求下,使馆几次商请阿外交部转达中方的意愿。阿方拖延了20多天,为了中阿友谊大局,在京剧团离阿前两天破格地作了安排。
11月25日下午,布迈丁在主席府接见了于会泳等人。可能布迈丁已经得到中国京剧代表团对阿尔及利亚在住房、餐饮等方面安排不满的汇报,在接见一开始,他就说:“阿尔及利亚是个新兴国家,各方面缺少经验,希望中国同志谅解。”然后接着说:“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时请我吃饭,饭桌上有松花蛋,开始我不敢吃,经周总理介绍,我吃得很香。”布迈丁讲完后看了看于会泳,而于会泳竟笨拙得连口也开不了。这时林大使赶忙出来打圆场,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当于会泳向布迈丁转达“江青同志的问候”,转送了江青的礼物之后,布迈丁略加思索后说:“请转达我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和良好祝愿。”布迈丁在提到江青时,还特别强调向邓颖超同志问候。消息传来,大使馆工作人员个个喜形于色,一致称赞布迈丁讲得好,有水平。布迈丁是国家元首、政府总理,而江青在政府中没有任何职务,凭什么以个人名义向布迈丁问候、送礼!于会泳在阿尔及利亚开口江青,闭口江青,甚至在接受阿记者采访时大肆宣扬:“我们国家有个领导人叫江青。”使馆同志对此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首场演出的风波
1974年11月1日是阿尔及利亚武装革命纪念日,也是阿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日子。阿政府规定,10月31日全国举行各种演出活动。阿方安排我京剧团在东部地区第四大城市安纳巴演出。28日上午,京剧团到达安纳巴。省长当天就接见剧团团长,并派出各种技术人员协助我舞台工作人员一起加班加点,于30日上午将舞台装好。通宵未眠的剧场经理阿古米高兴地对于会泳说,明天晚上演出不成问题了。谁知于会泳把手一扬,冷言冷语地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明天不行。阿古米大吃一惊,连忙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说:“31日晚上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安排的,如果安纳巴大剧院不演出,上级要怪罪我的。现在剧院的票也卖出去了,报纸也发了消息,无论如何请中方克服困难,按计划演出。”阿古米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央求道:“如果明晚不演出,不但要撤我的职,甚至要坐牢。”说着说着,他几乎要哭出声来。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回去和侯参赞商量,我们一致认为,31日不演出是不对的,一定要说服于会泳按计划演出。下面是侯参赞和我同于会泳交涉的对话:

侯:我们是为庆祝活动而来的,阿尔及利亚统一安排的庆祝活动,我们不演出说不过去。
于:请你们转告对方,由于安纳巴机场海关拖延了半天,耽误了我们开箱、装台和彩排,明晚无法演出,勉强演出,不能保证质量。
严:剧场的票都已经卖出,电台、报纸也发表了消息,全国各大剧院都在演出,如果唯独安纳巴大剧院不演出不好交代。
于:可以把剧场让给他们,由他们另行安排。
侯:31日演出是全国统一安排的,这里是我们的演出地点,他们临时找不到剧团。
于:演出质量问题我要对江青同志负责,这两天连续排戏,没有休息,不能保证质量。“两场一休”是政治局定的。
严:人家朝鲜《卖花姑娘》剧组一天演出三场。
于:他们怎么能和我们相比。
侯:这些话内部好说,阿方不好理解!
于:那就说服阿方。
侯:那你去说服,你是团长,你定好了!
侯参赞和我反复陈述理由,但于会泳的态度非常僵硬,无法说通。剧场经理又来催问,如果再不解决,他就去阿尔及尔请求处分了。我们觉得不演出是错误的,如果事情闹大了,我们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将处于被动地位。双方越争越激动,几乎要吵起来。侯参赞说完气冲冲回到自己房间。在侯参赞离开后,于会泳向我咕哝了一句:“代表团归使馆领导,你们定吧。”
这句话倒启发了我,外交部有规定,凡出访的代表团不论是什么级别,均须接受大使馆的领导。既然于会泳自己说出“代表团归使馆领导”,我立即趁机提出此事何不请示林中大使。此时于会泳也自觉无趣,便同意请示林大使。在电话中,林大使首先询问了演员身体状况、准备工作进展如何,然后婉转地表示,还是争取在31日演出为好。于会泳在电话中也不得不表示一定克服困难,争取31日晚演出。挂上了电话,于会泳沉思了一下说:“演出《杜鹃山》实有困难,可推到11月2日。31日晚可以演出几出折子戏,如《沙家浜》‘智斗、《林海雪原》‘打虎上山、《杜鹃山》的武打节目等。”
当剧院经理阿古米得知31日能够照常演出,也不管什么是折子戏,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跳了起来,紧紧抱住我说:“你们救了我,要不然别说刚上任半年的官要丢,甚至还会把我抓起来坐牢。”一场首场演出之争,到此告一段落。
31日晚,安纳巴剧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剧场座无虚席,省长格扎利等13名政要全部出席,气氛热烈友好。而11月2日《杜鹃山》首场演出时,当地政要只有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人出席,保留的50个座位非常显眼地空着。于会泳囿于保证演出质量,而丧失了《杜鹃山》首演的成功。
《杜鹃山》的演出效果
我京剧团访阿共33天,先后在安纳巴、奥兰、阿尔及尔三个城市共演出九场。观众对每场演出都报以热烈掌声,演出收到了预期效果。在这30多天里,我全程陪同,九场演出几乎每场都看,从前台看到后台。从观众的掌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热情发自内心,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因为观众都是自己买票入场,没有必要为不熟悉的中国京剧团捧场。在演出前,我曾担心阿尔及利亚观众对中国京剧能否看得懂。京剧团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事先在国内就作了充分准备,如舞台两边打出阿、法文字幕,每张观众椅子上安装了阿、法文“译意风”,传译阿、法文台词,另外还发给每位观众介绍剧情的图文并茂的说明书,可谓不惜工本。加之《杜鹃山》剧情紧张热烈,一环扣一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的艰苦曲折和胜利的喜悦,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演员唱腔优美,武打干净利索,观众叹为观止。最为精彩的一幕是,当党代表柯湘(杨春霞饰)在群众会上大声询问:“凡是给地主老财干过活的把手举起来!”随着台上扮演贫苦农民的演员一个接一个举起手来高声回答:“我干过!”“我也干过!”这时在台下观众席里,突然有一位平民打扮的阿尔及利亚观众站起身来大声说:“我也干过!”全场开始为之愕然,随即鼓掌叫好。这位观众真的是贫苦农民吗?如果真是,那太感人了。即使不是,带一点调侃,那也说明这出戏完全为观众所理解,观众的思想感情已融入戏中。主要演员杨春霞扮演的主角柯湘,唱功武打,文武双全,在聚光灯下一个亮相,全场为之倾倒。在与京剧团相处的日子里,我感到对京剧艺术的改革确有必要,如舞台布景的现代化和伴奏音乐的改进。除了传统的京胡、二胡、板鼓三大件之外,中西结合,大提琴、小提琴、圆号、小号等用于交响乐的乐器和京胡、二胡配合,音域辽阔,气势恢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