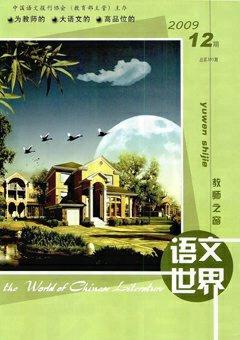品咂传统教育的甜味
马智强
在语文教育身陷泥沼、举步维艰的今天,被弃置一个世纪的传统教育,似乎很有值得回顾的必要。传统不等于保守、落后,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总是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去分析传统,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吸收和改造两千余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后产生出来的。我国《教育法》也写着“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这些论述为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传统教材的稳定性
凡对中国教育史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从春秋末期起,儒家思想的教材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等书,自汉代起构成一套完整的教材,一直沿用至清末。如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过去人们把原因简单地归之“崇古”或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但为什么要“崇古”,为什么要“提倡”,无人深究。中国的儒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是教人积极入世的学问。历朝开国之君,大都怀揣治国宏图。由于儒家所倡导的做人之道、人伦之序,有利社会安定,有利于封建统治;儒家描绘的“大同”,与其治国理想相符,所以他们大多尊奉儒学,都借重于这套教材办教育。自后的君主由于惯性的选择,或利用儒学思想来装点门面,也继续倚重这套教材。由于它蕴含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本源要素,它的超长稳定,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传统,因而值得代代传承。试想,如果没有它,没有借以施教的传统教育,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积极入世的精神、浓厚的道德色彩、崇尚气节操守、主张自强不息、强调适中和谐等等,能够传递到今天吗?迄今为止,其内容对治理社会、涵养民族性仍还有重大借鉴意义。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部分,这无需说。“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缺少辩证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轻易更换了教材,这就堵塞了传统文化传递的通道。而更换后的教材,常常是“女大十八变”,有时突出文学,有时又“政治挂帅”,强调思想教育;有时固守经典名篇,有时又要“紧跟时代”,呼吁“时代感”;有时恪守教材“严肃性”,有时又大讲“阅读兴趣”;有时注重文化性,忽而又讲实用性。有人赞叹教材六十年来的“巨变”,殊不知“巨变”也者,正是语文教育失败最明显的“标记”。变来变去,中华民族的文化命根——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却始终被弃一边,这诚然是怪事!
二、传统教材内容的多元性
传统教育的教材,是融文史哲诸多学科内容为一体的,即使同一本教材,往往也呈现出内容的多元性。如《论语》,内容就涉及伦理哲学、道德修养、国家治理、社会民生、礼仪习俗等等;而且文字简练,对后世的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仅直接出自该书及由其中语句凝缩演化而来的成语、格言、熟语就有八十余条。再如《春秋左氏传》,是史书,但其中又包括治国、军事、外交、地理、天文等等内容。就它的文学性来说,也影响深远,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评论《左传》:“其文缓,其旨远”,朱自清赞其:“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这种教材能使学生受到多重文化因素的熏陶和影响。在同样的教学时间里,这种教材的文化传授就显出了集约性、高密度、大容量的特点。这不但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优秀人才乃至大师级人才的出现提供了知识广博的肥沃土壤。现在的教材,内容偏窄,笼统来说是局限于文学一隅,不利于人才培养。相对而言,培养的学生知识面狭窄,道德观念薄弱,人文素质缺乏,与旧时毕业学生相比,思想成熟度显得相当逊色,已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诟病。
三、传统教材代表主流和本源文化
中国历史上传统思想学说的主流是儒学,而传统教材是儒学教材。因此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教材所代表的正是主流文化;而就儒家文化来说,教材代表的又是本源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和本源文化,都具有观念形态上的扩散、渗透作用。如儒家素来讲“仁”,扩展开去,治国理念就讲“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打仗就讲“不擒二毛”“不重伤”;保护生态就讲“斧斤以时入山林”“乐盘游三驱以为度”;行医就崇为“仁人之术”,倡导“贵义贱利”“普济大众”。经过这样的教育,学生既熟悉了主流文化思想,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它贯穿于所从事的领域,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举凡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军事、医学等领域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举出一长串历史名人的例子,证明这类文化在他们各自成功、成名的领域所起的作用。反观今天的教材,它有一个选材标准,即“文质兼美”。这固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这种理性选择并没有上升到文化的主流和本源高度,有的甚至没有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其所谓“文”,并非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而多指文采、技巧;其所谓“质”,又多偏重于功利性的思想教育意义,难以构成人文精神的体系。总之,传统教材对学生人文知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四、传统教法重诵读
语文教学,古代重读,把学习称为“读书”;现在重讲解、重分析。到底是“重读”还是“重讲”,有利于语文学习呢?吕叔湘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所以吕先生一贯提倡多读少讲。叶圣陶先生也讲“至于文字语言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千百年来的教学实践也证明诵读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通过熟读背诵,能让书面语的一切言语要素在学生大脑皮层留下系统的印象。诵读多了,印象就越积越深刻,最终,这些言语要素,如丰富的词语,多变的句式,言语的通畅协调、分寸情味,直至形象气势等等,就会在头脑中形成牢固的网络系统。当学生一遇到内在(自己表达)或外在的语言刺激时,就能凭借这个系统不假思索地分辨出词语的好坏、句子的正误、文气的滞畅、表达的优劣。很多老师也是主张多读的,只是受制于客观而无法去实践。从古到今,通过诵读学好语文的例子多不胜举,巴金曾这样介绍他的切身体会:“我背诵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里面有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我仍然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这段话给人深刻启发。
当我们面对“大多数人不过关”的状况感到迷茫沮丧的时候,是否该反躬自问,学生肚子里到底装了几本书?是一本还是多本?到底装了多少篇文章?有两百篇吗?是一百篇、五十篇,还是更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熟读背诵就是语文学习的本和源,就是学生要日日操练的基本功。古人深知此理,并据以指导少儿学习。当古代蒙童大量诵读“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事先败而后成,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事将成而终止,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等等语句的时候,当他们孜孜不倦背诵《论语》《孟子》等书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他们正沉浸在小蝌蚪、老山羊之类的童话世界里,正在为某个语素作何解释而大翻词典,正在为一个字能组成几个什么词而大伤脑筋,正在为词性分辨不清而大为苦恼。如此劳神费力,我们还能指望他们有多少文化知识、语言材料及语感的积累呢?这种状况能不令人忧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