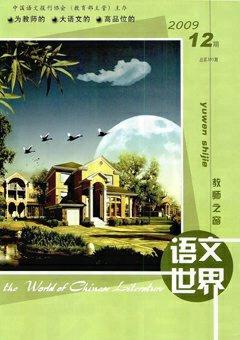“六字真诀”与不言之教
每一个语文教师都是“这一个”,但是并非每一个语文教师都能写出“这一个”。我们见过太多千人一面的教师形象刻画,读过太多对逝者的浮泛溢美的回忆文章。而张玉新老师为我们描述的两位已逝的师长,却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呼之欲出,如泥土般亲切真实。字里行间,戏谑中见至诚,深情中见肺腑。足见作者是性情中人说性情话,有个性的人写人的个性。文如其人,看张玉新老师的文章,便能想见他在语文课上不循旧规灵活多变纵横捭阖的风格。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每个语文教师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课堂风格。亲爱的读者,你能从张玉新老师的文字中体悟到他的风格吗?
(编 者)
成长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职业发展更离不开高人、贵人的指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能不提我的两位尊敬的师长,也借此表达对他们深切的怀念。
“六字真诀”练技艺
1985年9月10日是第一个教师节,我的学校——东北师大附中首次组织青年教师拜师活动。大家都不好意思主动选师傅,同年级谁年长就拜谁。我很快就弄明白学校教师的情况,私下里把人分成四类:甲类有能耐没脾气,乙类有能耐有脾气,丙类没能耐没脾气,丁类没能耐有脾气。甲类可遇不可求,碰上乙类就算幸运了。
恰好有一位属乙类的老师,同我年龄差距在全组最小——比我大16岁。他对我说:“兄弟,多大了?”我说:“22。”他说:“我回附中教书时已经38岁,这小青年儿,38岁还不得成精了!”借他吉言,我恰好38岁那年评的特级,虽然我并不认为评上特级就是成精了。
这一番话让我好奇,而他身上的一股“匪气”让我想起京剧《连环套》里的窦尔墩,就觉得过瘾。看他的模样仿佛是生产队长,衣着不讲究,矮胖的身材走起路来有些跩,稀疏而软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圆而扁的脸。虽然一副深度近视镜架在鼻子上,但总难和斯文联系起来,因为他的话语里国骂不绝,而且声音洪亮,有时骂着骂着还莫名其妙地汗流满面。但是从言谈可知此人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进而知道他也是师大附中学生,1965年也就是“史无前例”之前,他看到王光美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的照片说王光美是“娘们儿”,被他的班主任老师抓住把柄,受到“处理”,考上大学没有录取,便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了河北农村务农。一晃就到了1979年,落实政策承认他1965年的学历,插入78级读书,毕业回母校任教。
《长春日报》曾发表他的班主任老师写的题为《我是怎样帮助李光琦转变的》的文章,我眼前的此人就是当年被他的班主任“帮助”过的李光琦。
我说通了校长,强调如果拜师徒有虚名还不如不拜,并趁机举例我要拜就拜李光琦。校长同意了,李光琦成了我的师傅,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徒弟。
我最为受用的是他送我的“六字真诀”,他说:“兄弟,在这里混,首先要长能耐,能耐长在自己身上谁也抢不去;其次立规矩,立下啥规矩是啥规矩。”
除了“长能耐、立规矩”这“六字真诀”让我明确了当时的奋斗目标外,另一个受益是他为我提供许多上公开课的机会。我在同龄青年教师中上公开课次数最多,这一方面是客观因素——我是语文组最年轻的,比我大的都40岁以上,没心情参加赛课;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极力推荐,因为我是他的徒弟,他“护犊子”。而我的每一次公开课都得到他悉心指导,真像当年京剧科班里师傅为徒弟说戏那样言传身教。但他指导我时往往都是他相对空闲,比如外面的课不多,酒席不忙的时候。可是到了这时也就是赛课的前夕了,给我留下消化理解的时间所剩无几。我就必须在短时间吃透他的设计方案,同时必须暗暗地加上我个人的“绝活”,还要不露痕迹。京剧表演把演砸了叫“砸锅”,我不想“砸锅”;把名角因故不能出演而临时抓人顶替叫“钻锅”,我平时刻苦磨炼自己就是为了随时的“钻锅”。我能够较好地理解他为我设计的方案,并能落实到课堂。他的设计体现的是他的教学风格,依据是他自己的专长;我就不自觉地熟悉了他的风格,并颇以为是“李光琦第二”而自豪。我几乎不听他的课,一方面是排课冲突,另一方面是我最讨厌听课。所以我在他的宏观指导下自悟的多,建构的也就渐渐多了。
我知道了每节课(尤其是公开课)不能有多个中心,必须有一个高潮,要在设计时预先考虑到;上课像写文章一样,不同人有不同风格,因此要知道自己适合哪种风格。
我的师傅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扬言用在语文教学上的工夫不到三成,他是“用玩剩下的”来教语文,教师职业仅是他的谋生手段之一种。他文章写得好,有学问,又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优游在学校和社会之间。我出身社会底层,有“市井”气,也有“匪”气,一下子就同他那燕赵任侠之气与东北的“匪气”合流,且颇为自豪。后来我注重课堂大容量、快节奏、灵活多变的教学风格,纵横捭阖的论辩气势,大多受到他的影响。
我也是个性极强的人,我没有社会经历,不复杂,也就不能全学他那一套。尽管在教学技巧上获益匪浅,但最受用的还是“长能耐、立规矩”这“六字真诀”。在不断地“长能耐”的过程中,也开始旗帜鲜明地“立规矩”,立属于自己特色的规矩。
不言之教悟师道
我经常在知识和教学认识上与别人“交恶”,“战斗”精神生猛。我率真、执著的个性也不断走向极致。
我的教学水平也同样在茁壮成长,成为语文教学的多面手。学校每学期举行一次教学百花奖活动,青年教师上课,全省同行听课。我的课就是在师傅李光琦的指导下不断推陈出新,创出许多新课型,一时在省里声名鹊起。有一位闻名全国的语文教育专家每次我上公开课他都来听,而且听完我的课就走,却一次也没有评过我的课,遇到熟人还说:“我来听张玉新的课。”
他,就是张翼健先生。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大学毕业回到他的母校东北师大附中任教,1985年4月,在教了23个年头的时候离开母校,调到吉林省教育学院工作,离开时他是语文组长。而我,1985年7月分配到师大附中任教,同先生只差三个月没能在学校相遇。后来,2004年11月,我在这里教了20个年头的时候,也调到吉林省教育学院,离开时我也是语文组长。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我师傅可以跟你称兄道弟,但骨子里把徒弟视为“附属品”;你可以和他以朋友相处,但骨子里他是爹。翼健先生则是那种你可以和他成为忘年交,可以产生兄弟般的情谊,父子般的情分,师生般的友谊;他绝不计较名分,也不计较实质,管他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认可,他不会干涉你。他绝不主动把你揽在他的羽翼之下,你硬要偎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也不会把你推出去。
与我师傅的耳提面命不同,翼健先生几乎没有对我进行过“面授机宜”的指点,也没有当我的面夸赞过我,我们都认为没有必要。我的那点水儿他都了然,却在为我编著的《文言文学习手册》所作的序中给了我鼓励: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有这样几点很值得广大青年教师学习:一是不懈地广博地学习以使功底深厚,这是努力提高自己以成为一个好教师的根本;二是认真动脑深入钻研以提高能力做到教学游刃有余,这是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的前提;三是不断探索独立思考以形成自己的见解与风格,这是使教学真正成为艺术的关键。
1996年我有争议地被任命为语文组二副,翼健先生告诉我不能搞一言堂,要百家争鸣,还给我讲语文组当年的争鸣盛况。我开始尽量不上大型公开课,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多的机会。我是翼健先生关注的典型之一,他还关注许多可造就的中小学教师。
从此,我作为语文教师和教研组二副,我的“独善其身”的追求开始转为“兼济天下”。
在每周一次的语文组会上,我只要请他,他必到,而且我称呼他“语文组前组长”他十分受用,给我们办的《教学札记》写的序落款是“附中语文组前成员”。他关注着我的发展,通过关注我关注着语文组的发展。然而他对我的爱重,包含深深的母校情结,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无疑是被先生认作他在附中的继承者。他曾经狠狠地表扬我一回,这就是我的学生们出版的“中学生作文阳光书系——新人文作文”的序言(此文见“师说”部分)。这是先生留给我的珍贵评价,今后,就是想听他批评都没有机会了。
如翼健先生所言,我总主动找他交谈,用这种方式请教。他不是好为人师的人,从不主动告诉你应该怎样,你如果想知道自己的想法、做法正确与否,你就要陈述且看他的表情。如果你做得对,他可能没有什么表情,但一定专注地看着你;如果你做得不对,他可能很平淡地说:“你要这样这样做,是不是更好。”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了解了语文组辉煌的过去,了解了前辈的功底学识。这也成了给自己学问技艺定位的标尺,让我时刻感到自身的缺失,因而能不断进取。然而,除了翼健先生谈到的我因为参加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而不能为我的教改验收这一客观条件之外,我的主观因素更为关键,我的性格导致了“散装”特点,不能变成“瓶装”,那样太难受。我不愿意成为所谓的典型。这也因为我的发展一路平顺,没有什么坎坷,也没有过于感到生存资源的匮乏,也就不愿意因为被需要而上台说些肉麻的话。我教我的语文课,顶多当个弼马温。我有顽强的生存能力,不怕被捧杀,当然也不甘被捧杀。
我曾经用这样的话鞭策自己和全组的教师:我们站在山峰上,并不说明自己是巨人;我们考量个人的分量,必须减掉学校品牌赋予的附加值。就教师个人功底学识而言,横向看,我们或许是高峰,但纵向看,我们或许是低谷。我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我把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组建成了“吉林省语文教育的一面旗帜”,这是先生的评价。
他之相人,唯视其长,不计其短。有人说,好人自然说自己好,坏人也说自己好。我问了他这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先生从听课本上翻出了一页,上面记着一个故事,大意是说在天堂的门口排着很多人,突然天堂的门关上了,因为名额已满,其他排着的人就只好下地狱。先生平静地说:“你怎样区分好人和坏人?”去年9月,翼健先生去世了。现在,我只能说,以不言之教使我受益终生、使我成为语文教育的乐之者的翼健先生,在天堂安息吧,我坚信他不必排队。
两位师长一位传授我教学的技艺,一位点拨我教育的真髓,这对我的成长都不可或缺。两位先生都于近年仙逝,借此机会,以我今天的茁壮成长告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