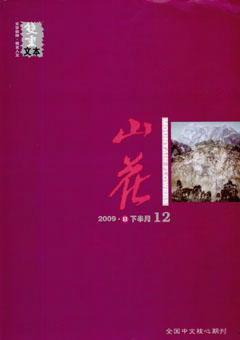贾平凹散文语言的抒情特征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贯穿性人物,贾平凹有着无可争议的地位与影响。贾平凹是一个复杂独特的存在,不同文体经他的灵光照射便能异彩顿生,以一人“兼具数美”,实为当代文学创作界的奇才、鬼才。其小说创作成就巨大,散文创作也毫不逊色,以广泛宏富的内容、超凡脱俗的形式从当代散文创作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西北大学教授费秉勋指出:“与写小说相比,写散文似乎更能见出贾平凹的才情和艺术素质。他的散文确实写出了特色,写出了个性,在全国能自成一家[1]。”
贾平凹究竟给现代汉语写作贡献了什么,自然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也能给当下文坛带来诸多启示。充分发挥自身天赋,融会古典和现代汉语语言的成功运用,创作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文学语言,形成一套独特的、极具个性化的文学语言风格和文学语言价值观,是他对20世纪汉语言文学做出的重要贡献。淡化抒情,朴拙空灵,是贾平凹散文语言风格的重要特征。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审美价值要靠语言来实现。贾平凹认为,写作上“语言是第一的”。与小说相比,散文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甚至有些苛刻。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既是散文的形式,也是散文的内容。小说可以通过曲折有趣的故事、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吸引读者,散文就没有这种优势。散文篇幅短则几百字长不过几千字,语言粗糙缺乏个性,就很难抓住读者。贾平凹对此深有体会:“我当编辑几十年了,你拿出一个稿子,稿面干净、清楚,就有好感,读起来语言好,就有兴趣读下去。如果稿面乱七八糟,读上几段,语言枯燥无味,就不想看了[2]。”
贾平凹散文语言是从模仿上路的,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孙犁我学得早,开始语言主要是学孙犁。”[3]他早期散文语言中孙犁的痕迹很明显,注重主观与细致的感觉,追求“阴柔”意义上的“唯美”。其散文语言偏重于诗情画意,清纯流利,朴素传神,虽显得有些单薄清浅,雕琢痕迹,但其含蓄隽永、优美自然的笔致,却已走在了同时代作家前列,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好评。发表于1983年的《商州初录》,成为贾平凹散文语言风格转型的标志。贾平凹习得沈从文等文学大家语言的精妙,“吸精,吸神,吸髓”,放弃遣词造句的精雕细琢,“删繁就简”,“求素求朴”,疏朗大气。此后,贾平凹散文语言“逐渐摆脱主观抒情的格调,而力求使得作品语言冷静些、清淡些,尽量地少些主观,而多些客观;少些激情,多些冷静;少些抒情味,多些写实性”[4]。他开始有意识地超越自我,与早期“荷花淀”风格拉开距离,进入另一境界:由空灵转向平实,由轻巧转向稚拙,由优美转向素朴,由单纯转向驳杂,人为雕琢痕迹、抒情特征淡化,追求“老僧话家常”境界,朴拙空灵,苍凉雄浑,少了明显的诗情画意与哲理趣味,非常富于质感与张力。贾平凹认为这是一种山石风格:“石头的质感好,样子憨,石中蕴玉,石中有宝,外表又朴朴素素,这影响到我的性格,为人以及写文章的追求。我不喜欢花哨的东西,不喜欢太轻太光滑的东西,我在文章中追求憨,憨而不呆。石头纯以天成,极拙极拙了,拙到极处,又有了大雅。无为而为,是无规律的大规律[5]。”
抒情是散文的一个标志性文体特征,但并不意味着越是抒情的散文越成功。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发展沉浮证明,散文抒情走向泛滥时,散文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散文,更多的是诉诸自己的真情实感,诉诸语言的创造性和个性化。散文的情感需要节制,越是节制,情感的张力反而越大。抒情散文最容易流于虚假做作,虚假做作恰恰是散文的大敌——它消解了散文的本质精神。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走向了激情表达和模式化,贾平凹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散文忌讳那种空喊,那种声嘶力竭的大话、空话、假话、官话。避免激情一泄无余。”“描绘激情不可到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6]”贾平凹在《对当前散文的看法》中,对真情热切呼唤:“中国散文的一兴一衰,皆是真情的一得一失。60年代初期之所以产生一批散文名家和名作,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依赖的便是真情的勃发。但不久社会生活的不正常,散文顿跌于套式,后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人的虚假恶性发展为疯狂,文风以唯美主义又更衍变为一种声嘶力竭的空喊,以至于从此声名狼藉。文学艺术的规律性东西乃至于基本的东西,现在的散文要振兴,关键是为真情招魂。”有了这种文体自觉意识,贾平凹逐渐改变早期散文创作那种情绪过于外化、过于浓烈的主观抒情,开始寻求一种淡化抒情的艺术表达。
淡化抒情是贾平凹散文语言的审美特征,也是散文创作走向成熟和大境界的必然归宿。正如佘树森在《散文创作艺术》中所说,“在洗炼散文语言时,不单要注意形容词语的慎用、少用,避免堆砌辞藻,同时还应该注意尽量避免辞藻色彩(包括其感情色彩和自然色彩)的过分浓艳。其思愈深,其文愈质;其情愈真,其言愈朴。”[7]
淡化抒情是在追求语言的朴拙中实现的。语言朴拙是贾平凹建构散文语言世界的一个重要“法门”,也是其散文语言独特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说过:“我反对把语言弄得花里胡哨。写诗也是这样,一切讲究整体结构、整体感觉,不要追求哪一句写的有诗意。越是表面上有诗意,越是整个没诗意,你越说的白,说的通俗,说的人人都知道,很自然,很质朴,而你传达的那一种意思,那一种意念越模糊。”[8]
贾平凹散文语言的“朴”指的是追求语言的“空白”效果,用的是“减法”,在黑纸上写白字,是“求白用黑抹,求长用剑削”,不矫揉造作,用纯朴的语言最大限度表现事物的本真面目。如他描写一些自然景观:“车开始上坡,山越来越近,似乎要一直爬上去,但陡然路落在沟底,贴着山根七歪八拐地往里钻,阴森森的,冷得入骨。”(《商州初录·黑龙口》)“本来是一面完整的石壁,突然裂出一个缝来;……到了石缝里,才看见缝中的路就是一座石拱桥面,依缝而曲,一曲之处便见下面水流得湍急,水声轰轰回荡,觉得桥也在悠悠晃动了。”(《商州初录·一对情人》)《商州又录》中,一切的人和物都是用最平淡朴素的语言来表现的,那“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那秋天的“果实很繁,将枝股都弯弯地坠下来”,还有“浑圆圆”的山,浓得“扯不开”的雾。这些语言使其笔下的商州世界如真实画卷一般,一目了然却又蕴涵丰富。
“朴拙”中的“拙”指的是,语言“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澜深藏”,“文白驳杂、雅俗共举、冷峻峭拔”,[9]蕴涵一种浑然的气韵。贾平凹非常推崇汉代艺术,给他很大艺术启发的是一块“卧虎”石与一个“汉罐”。这“卧虎”,只“不过是一个流动的线条和扭曲的团块结合的石头虎,一个卧着的石头”;是一块混混沌沌的石头,一个默默的稳定而厚重的卧虎的石头。1980年冬天,贾平凹来到霍去病墓场,看到这只卧虎时,喜爱极了,把它视为自己有生以来所见的唯一艺术妙品,久久揣赏,感叹不已。“汉罐”,原本是一件极普通寻常的汉代器物,贾平凹把它珍藏至今。“在夜深人静,一个人伏案写作,很煎熬了,就常常看着这汉罐,不知怎么,它就给我一种力的感悟……”在那只粗拙沉稳、欲跃未跃的“卧虎”前,从这个破损了随时可能被扔弃在院墙头、茅房角的汉罐中,贾平凹对自己文学创作审美品格终有所悟。他以“卧虎”、“汉罐”的朴拙大度反观散文创作,发现了新时期散文“精神脆弱”、“小、巧、甜腻”的缺陷危机;以“卧虎”、“汉罐”的自然朴素审思自己的散文创作,则对自己的艺术审美品格有了更深刻感悟。
李泽厚先生用气势、古拙,概括出汉代艺术的美学特质:“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10]贾平凹在其散文语言运用中自觉吸收了这一美学理论。他描绘山水时,常短句连用,使行文的节奏感加快加强,形成奔腾放野之气。“凤冠山更是奇特,没脉势蔓延,无山基相续,平坦地崛而盗起,长十里,宽半里,一道山峰,不分主次,锯齿般地裂开,远远望之宛若凤冠。”(《商州初录·龙驹寨》)“而在悬崖险峻处,树皆怪木,枝叶错综,使其沟壑隐而不见,白云又忽聚忽散,幽幽冥冥,如有了神差鬼使。”(《商州初录·莽岭一条沟》)作家摆脱了那些空洞、浮华的抽象抒情文字,努力回复到最自然鲜活的文字表达,去尽铅华,朴拙简约,浑然一体,意味悠远。
淡化抒情的艺术追求,在贾平凹散文创作中得到很好实践,使他的散文变得更为成熟精湛,也是其散文创作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曾令存教授指出,这种淡化抒情的风格契合着贾平凹散文“对厚重历史感和文化意识的言说”,“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更深刻追寻,对精神灵魂的超验拷诘。这种‘追寻与‘拷诘是一种理性与思辨的直逼,是无须任何花巧装饰的直面对话。这种‘实有与‘虚无的对话,这种天地人的会意心悟,任何‘花言巧语都比不上‘赤裸裸的语言有力有分量”。[11]
参考文献:
[1]费秉勋.贾平凹论[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156.
[2]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M].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241-242.
[3]贾平凹,韩鲁华.坐佛·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M].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217.
[4]王永生等.贾平凹的语言世界[M].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185.
[5]贾平凹.与穆涛七日谈,贾平凹文集·第十三卷[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6]贾平凹.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二卷[M].漓江出版社,1993: 214-216.
[7]佘树森.敬文创作艺术[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86.
[8]江心主编.《废都》之谜[M].团结出版社,1993:58.
[9]孙见喜.贾平凹前传·制造地震[M].花城出版社,2001:388.
[10]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87.
[11]曾令存.贾平凹散文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0.
作者简介:
白忠德(1971— ),男,陕西佛坪人,文学硕士,编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西安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