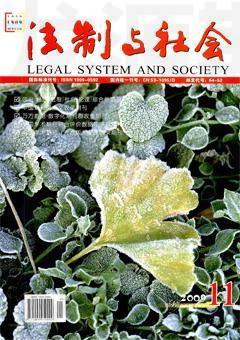社区治理理念下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及发展取向
李素梅
摘要 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我国融入世界进程的不断深化,服务型、福利型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我国交错推进,公共权力开始大范围、大幅度的向社会转移。而社区作为一个市民交流的小范围熟人社会,逐渐成长为百姓生活的一个社会单元。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生活、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社会管制等诸多角色,从成长为现代服务型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而作为具有强烈教化色彩的社会化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将其纳入我国社区治理的程式之中,不仅有利于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而且也使社区市民生活更为融洽,从而得以有效的预防犯罪。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发展社区治理理念,丰富其内涵,将社区矫正纳入社区治理的范畴,利用社区的教育功能、交互功能、渗透功能,创建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的社会环境氛围。
关键词 市民社会 福利型政府 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155-02
一、社区治理与社区矫正
(一)社区治理概述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①社区治理与传统单一的行政治理有较大的优势:其一,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行政主体)转变为多元化主体(行政主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等),广泛发挥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其二,治理过程由原来的行政统治转变为民主协商,强调在协商过程中激发参与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参与者由被动变为主动;其三,治理结构由具有强烈刚性色彩的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弱化了治理主体的中心地位,而提高了参与主体的地位。社区治理就是提供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智力结构”,②在尊重利益多元之客观环境下实现共同价值观念的凝结,达至公民的自主治理。
(二)社区治理与社区矫正的结合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处遇,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构式或监狱式处遇而言的一种新兴的犯罪处遇方式。”③2002年香港著名歌星谢霆锋因妨碍司法公正被香港西区法院判处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这使得社区矫正这一新兴的犯罪处遇方式开始流传于社会之上。实际上,我国大陆早就开始这一方面的探索。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就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④2003年7月1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一下简称《通知》),以法律文件正式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⑤
由于社区矫正符合司法文明演进趋势,具有人权保障之人本主义色调,从而在当今世界普遍得以采用。实际上,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质是借用社区人文交互进化之机理来达到社区行为人行为矫治的目的。因此,社区治理与社区矫正具有诸多的共性:两者都以社区为单元;两者在目标指向上服务于社区和谐;两者部分治理过程的重叠;两者部分治理手段的通用等。故而,笔者以为,这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一方面,社区治理的主要指向是通过社区行为人的各种行为的交互性治理达到社区和谐的目标,从而社区治理必然要对社区中的异化行为主体(犯罪行为人)予以特别的关注和治理;另一方面,社区矫正的对象本来是对社会关系有所破坏的行为人,通过他们的服务性行为可以赔偿其非法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同时又在一定程度完成社区治理工作(惩罚非法行为,教育社区其他行为人),也使该非法行为主体得到了教育。目前,以社会治理理念为背景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一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进路。
二、观念滞后: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及困境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已经进行将近十年,试点地区也扩大到了18个省级地区,其范围己发展到85个地市、375个县(区、市),3142个街道。现有社区服刑人员50083名,其中,缓刑32,882人、假释5783人、剥夺政治权利8074人、折子监外执行1768人、管制1576人。⑥而相较之下,美国早就建立了常设性的专门工作机构。据1997年统计,美国的社区矫正机构共有2931个,其中缓刑办公室812个,占27.7% ;假释办公室有486个,占16.6% ;缓刑和假释合署办公的机构共有1633个,占55.7%。⑦而我国目前却正规的常设性工作机构没有得到设立。可见,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仍旧难以让人宽慰。此外,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由于观念滞后,导致在诸多环节陷入困境:
(一)法律依据缺失
目前社区矫正在我国还处在试点层面,试点依据为两个试点《通知》。该《通知》仅类似于一个行政规章,法律位阶低,内容不全面,给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开展带来了不少法律依据上的障碍。
(二)主体不明确
《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但是依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五类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机关为公安机关,从而使得《通知》规定的主体(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规定的主体(公安机关)发生冲突,导致主体不明,责任不分。
(三)对象范围狭窄
按照《通知》的规定,我国的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下列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而对于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并不具有针对性的适用效力。实际上,西方法治国家的社区矫正对象范围非常大。以2000年数据统计为例,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在全世界最高,达到79. 76%,澳大利亚达到77. 48%,新西兰为76. 15%,法国为72. 63%,美国为70. 25%,韩国和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 9%和44. 48%。⑧
(四)专业机构、人员缺乏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承担矫正工作的主要是司法行政人员。由于司法行政人员往往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而且人员流动性较大,从而致使其无法全心全意的投入矫正工作之中。再者,一旦矫正对象发生异地流动,就很容易出现机制和人员不对接的现象,从而难以保证矫正工作的持续性、规范性。
(五)社区矫正经费不足
由于社区矫正主体和职责不明确,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居委会之间对矫正工作的责任不分,致使社区矫正缺乏固定的国家财政支持,从而陷入资金上的拮据与困境之中。
而从上述困境的根源来分析,其实,这些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其难度也不大。实际上,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之所以举步维艰,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理念上的滞后。
三、以社区治理理念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一)理论更新:以社区治理理念引领社区矫正
社区治理是社区建设在理论和价值观上的培养和整合提升,是一个善治的过程和方法。它强调的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而是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其核心含义为政府从“划船者”向“掌舵者”,还权于社会。其实在理论依据在于哈耶克论论述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⑨意即通过民间生活多样化的交涉促进社会秩序之“内部规则”的自我生长,依靠民众的自主达到政府的“善治”具体来说,就是逐步改变原有单一结构式的政府行政治理模式,顺应经济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让多元化意识、行动凝聚成为一种区域文化和规则,建立区域性的“共同体”,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与动员网络。可见,社区治理理念具有强大的净化力量,不仅能够维护社区之优良传统,而且能够剔除不良观念之糟粕。由此,社区矫正本质上就是要借用社会治理的内核,以达矫正犯罪行为人之异化意识和异化行为。而将社区矫正工作内置于社会治理理念之下可以达到多个方面的天然融合:在社区主体上,犯罪行为人并没有中断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依旧是社区主体之一,在时空上保持了社区成员形象上的完整性,从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其可以凭借日常的经历自然融入该社区的社会治理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社区治理采取一种协商过程,在尊重行为人之成员人格的基础上促使犯罪行为人自动加入社区治理过程,而使得没有观念上的生硬障碍;在行动模式上,社区治理主要采取吸引和劝说的方式,从而使得社区矫正在双方自主意识支配下得以完成。
而从外部规则的建立来看,包含社区矫正的社区治理从本源上切合了目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改革需要,从而很容易为各级地方政府所接受。因此,社区治理理念下的社区矫正就能够获得改变目前边缘化社会地位的契机,而成为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将有利于其获得制度建设的高层支持,有利于其专门机构专业人员的配备,有利于行动经费的保障。从而使得社区矫正能够真正全面运作起来。
(二)制度治理:利用社区治理理念构建社区矫正制度平台
针对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困境,本文以为,可以社区治理理念为理论背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工作:
1.加强立法工作。要改变目前社区矫正无法可依的状况就必须要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结合国外立法的经验,本文以为,我国应当制定一部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方方面面予以立法上的规范。
2.明确社区矫正主体。针对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不明的状态,本文建议与刑事诉讼法衔接,将公安机关确立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而以司法行政机关和社区组织为协助主体。这样既能借助公安机关之强势地位,又能使其他协助主体发挥作用,而且使矫正机构、人员和经费等问题都能够一次性得到解决。
3.扩大社区矫正对象范围。笔者以为,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可以扩大到五年刑期以下的非暴力犯。理由是,社区矫正就是要尽可能的使没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人通过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措施连续性的进行社会改造。
(三)行刑社会化:社区治理理念下我国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取向
从1876年美国纽约州制定世界第一部社区矫正法以来,以社会治理理念之背景,通过社会行刑方式来矫正犯罪行为人的异化思想和异化行为已经逐渐成长为一种世界性的改造方式。行刑社会化通过日常进行的社会治理过程,帮带性解决部分犯罪人的不良思想和行为习惯,同时又给刑事司法带来巨大的效益:节省监禁犯罪人的成本,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人道主义教育方式提高行刑的效果,使犯罪人回归社会,有效地改造犯罪人;最大可能的降低再犯罪率,进而促使社会整体犯罪率的回落。由此可见,以社区治理理念为引导,以社区矫正为模式的行刑社会化进路是我国犯罪行为矫治的未来取向。
注释:
①徐颖.社区矫正:二元化刑事政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探索.犯罪研究.2009(4).19-20.
②[美]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③胡承浩,万志前.理念、制度、技术:三维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江汉论坛.2009(8).127.
④该规定的内容大致为: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从事无偿的社区劳动,并同时由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工作.
⑤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绝大多数的学者和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单纯的法律文件来对待,并没有意识到其社会治理的意义。实际上,该法律文件强调“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从而,应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即从社会治理来予以理解.
⑥李冰.中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概述.社区矫正研究——2006年北京国际论坛文集.2006.
⑦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321.
⑧廖斌、何显兵.社区建设与犯罪防控.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365-375.
⑨邓正来.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