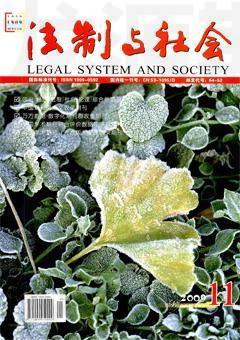中世纪的王权与法
李 锐
摘要 由于缺乏自身的法治传统,转型中的中国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西方,从中汲取法治经验。中世纪的西方王权远非绝对的,它受到来自教会、贵族和人民三方面的制约,不仅是实力上和道德上的,而且还是法律上的,而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传统中所欠缺的。
关键词 王权 教会 中世纪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003-02
人们在谈论西方法治思想的起源时,一般从古希腊罗马的法律建制和法学思想谈起。诚然,古希腊人为西方后世政治和法律思想的探讨贡献了大部分论题和答案,而罗马法将普世法律的思想传遍了地中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谁能够自外于法律。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西方文明的其他传统。整体而言,西方文明的起源可谓是三位一体: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传统、法律建制和物质文明,基督教所带来的犹太-闪米特文化因素和宗教虔诚,以及日耳曼蛮族的语言和活力。要理解西方文明,就必须通盘考虑这三个主要来源,缺一不可。本文将主要从后两个方面来论述西方法治传统。
征服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的王权从一开始就不是专制的,在部落时代,部落决策权属于全体成员参加的部落会议,王权则产生于战争和掠夺。部族对部族的战争以及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战争呼唤着新型战争领袖的出现,这样的角色往往就固定地由某人来承担。在战时他作为军事领袖有义务身先士卒,但却没有任何强制力量来维护他的权威。但渐渐地,军事领袖因为其本领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战士的个人效忠,因而,在和平时期他也享有了比旁人更大的权威,使得他的权力向其他方向扩展。在首领权力延伸到民事领域之后,王权就产生了。但这并没有使人们失去对原始军事民主时期的记忆。在罗马帝国内部问题日益严峻的同时,边界上日耳曼人的压力也开始增大。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日耳曼人进入了原先对他们封闭的罗马内地,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虽然有罗马皇帝绝对君权的榜样,这些新近建立的蛮族王国还是继承了原先的日耳曼习惯法,国王和战士们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国王无权要求臣下的绝对服从,他必须与比较强大的臣下谈判来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胜利的蛮族还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许多既有建制(主要是普世基督教会)和它们对王权的限制,总体而言,中世纪的王权受到以下几种力量的制约:
一、教会神权的限制
蛮族有能力征服欧洲,但是,他们对于征服的土地却不能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在当时的环境下,唯一有组织的既有建制是从罗马帝国中脱胎而来的基督教普世教会。蛮族王国想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赢得基督教会的合作,因为只有教会能够提供有效的民事管理组织和人员。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象征着蛮族军事活力和教会稳定行政管理能力的结合。教会赢得了国家的支持,基本垄断了知识,并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的世俗职位。作为中世纪唯一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教会的神学家和法学家系统整理了教会在王权和法等问题上的看法,提出了在神法和自然法约束之下的王权观念。
早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会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就写出了他那著名的《上帝之城》。他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的邪恶,任何所谓的合法性都经不起对国家起源一分钟的审视。罗马国家起源于罗慕路斯对亲生兄弟的谋杀,王权都是对人民权利的篡夺,政治权力就其本性来说是有组织的恶。而这恶之所以有必要存在,那是因为原罪缠身的人类没有能力在不受压制的情况下维持和平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邪恶的人类需要强力的压制才能建立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只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国家对犯罪的打击不过是邪恶在打击一个更大点邪恶。和基于基督徒相互的爱而结合成一体的基督教会相比,国家是污秽而卑下的。教会的目的——灵魂的拯救高于国家的目的——社会的和平,因而世俗王权应当从属于神圣教会的权力,接受教会的指导和约束。绝对君权是无法与这张世界图式保持一致的。
从十一世纪之后,西方进入到了中世纪盛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逐渐稳定,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世俗生活的意义,这导致了对国家和王权的较为积极的评价。圣托马斯?阿奎那,这位教会思想的集大成者,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的论断,认为国家是人类合群的需要所自然产生的,因而谈不上邪恶,虽然仍然带有一切人类建制不可避免的瑕疵。作为王权组成部分的立法权因此就必须受到自然法和《圣经》中上帝律法的约束,在这个限度之内,王权是自由的,但超出它之外,王权就变为邪恶。教会的责任就在于时时监督王权,并运用教会的权力,将王权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二、贵族权利的限制
贵族阶级来源于部落时代的武士,国王本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他们在战争中支持国王,换得王权对他们政治经济权利的维护。在法兰克王国中,由于经济和技术的落后,中央集权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查理大帝的做法是,派一些“伯爵”作为王权的代表到各个地方建立政府组织,但这些“伯爵”们却倾向于建立个人的统治,并力图取得世袭的地位。加洛林帝国在查理死后迅速瓦解,他的继承人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而这时的欧洲同时面临着新一轮的外部入侵,在南方,穆斯林在新月旗下开始了对基督徒新的进攻;在东方,马扎尔人正在劫掠中欧;而北方的维京人则开始骚扰欧洲的沿海地区,甚至深入内地。伴随着内部斗争和外部入侵的加剧,稳定而和平的生活变成了稀有之物。中央权力已经不能保护臣民们不受内部斗争和外部入侵之害,于是,地方上强有力的人物开始承担起先前由王权承担的责任,领导人们团结起来抵御来自各方面的暴力侵害。这样,原先的贵族权力迅速膨胀,而王权却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新的形势产生了新的政府组织模式,在所谓的“封建模式”中,封主和封臣订立封建契约,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封臣有义务效忠封主,并在军事上支持封主(军事服役并不是无限期的,通常一年只有四十天,超出期限的,封主要给予报酬),还要履行其他政治上或礼仪上的职责;而封主有义务保护封臣,并通过授予封地的手段保持封臣的经济水平。这样王权就受到了契约法的约束,违约就必须面对封臣的抵制。在缺乏双方都接受的评判机构的条件下,这抵制通常就意味着战争。人们认为,上帝会支持正义的一方,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幅封建社会的图景也许并不圆满,但却是明确的、可预知的,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人们认为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模式。
中世纪的贵族出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很少为这种模式提出理性的解释。但后世的思想家们却不乏为贵族制度辩护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王权如果不想堕落成为唯武力是视的专制权力,则独立而强大的贵族是必要的。贵族约束君主,时时提醒他不过是“同列中的首位”,而非与臣民迥然有别。这样,君主才不至于个人权力欲望膨胀,无视他人而一意孤行。他的结论是,专制制度适合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君主制度适合法国和英国这样的中等国家,而共和制度适合古希腊城邦或中世纪意大利北部城市那样的小国家。这样,贵族并不是国家的累赘,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自由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他的意志并不当然成为法律,因为那需要契约另一方的认可。绝对君权理论的再次提出,还需要等到十七世纪王权再度崛起的时候了。
三、人民权利的限制
在中世纪,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属于契约关系,这不仅适用于贵族,同样适用于一般的自由民。自由民来自原先部落社会中的普通部落成员,他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和特权。西方君主的加冕典礼充满了契约性的暗示。教皇或主教代表教会加冕国王,国王承诺维护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贵族向国王表示效忠,国王承诺尊重贵族的特权;人民欢呼接受国王作为他们的君主,国王承诺维护和促进人民的利益。中世纪的议会就在于体现人民对政府施政方针的认同,至少“人民中比较有分量的部分”的认同。如著名的英国国会,始于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包括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但同时也包括郡和市镇的代表,以对国家决策的做出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