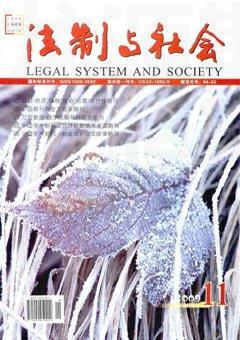对程序正义在刑诉关系中的探寻
董学智

摘要正义是司法的永恒追求,而保护人权也是司法必不可少的内涵之一。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程序正义对于刑事诉讼法而言,是触及整个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每一根神经的。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刑事诉讼法体系与实践的基石。笔者在结合实务的基础上,剖析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参与者间的相互关系,探寻程序正义的可能与实现,以期有所裨益。
关键词刑诉关系 司法机关 诉讼参与人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11-024-02
一、引言
诉讼,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上关键的一环,关乎司法的根本价值。 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和调整的、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①然而,纵观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诉讼法律关系,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二、在“亲密”和“距离”之间寻求公正——论公检法三者间的关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即是学理上所称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被认为是刑事诉讼各机关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②从司法实践来看,公检法三机关在办案中的“分工负责、相互配合”方面虽存在一些瑕疵,但还能够较好的体现公正,然而“相互制约”在实务中却存在较大的问题。
从应然角度看,公检法三机关应呈现三角形结构,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以臻稳定。这种结构在理想层面实现了稳定、科学及高效。但是在实然情形中,往往却是另一种司法工作模式,即线性结构(陈瑞华教授称之为“流水作业”,即三者工作是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犹如机械工厂生产的三道工序)。其本身性质使之难以达到稳态,不仅不能很好的相互制约,还可能造成职能的混同与交错,使得三者间职权相互逾越,最终歪曲了三者间的关系,违背了该原则设计的初衷。(如图)
司法职能混同,在20多年前的“严打”中就有体现,③“公检法联合办案”实质上扭曲了刑诉法所规定的原则,变为“多配合少制约”,形成事实上的“先定后审”,使公检法机关相互制约的应然制度设计失去其制衡作用,导致三者间制约关系的弱化,结构失衡,功能错位,削弱诉讼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利,进而损害司法公正。此外,案件真实情况的还原工作极为复杂,而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故而需要不同机关从各自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出发,以侦查、审查起诉、法律监督和审理裁判等具体方式,去伪存真,逼近真相。如果公检法三机关由于司法职能的混同而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即等于由三者合成一体来断案,与专断则无区别,严重影响了诉讼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影响对案件真相的认识,从而不仅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原则,实体公正也难以达到。
审视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的“流水作业”模式,难以使得法庭审判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首先,侦查机关活动缺乏程序性限制,公安机关处理权缺少约束,而检察机关又没有实际可操作的权力来约束其行为;此外,侦查人员极少出庭作证,法官没有干预侦查机关活动的权力,即“审判前的诉讼活动既没有法官的参与,也不存在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司法机构不能就追诉活动的合法性举行任何形式的程序性审判活动”。④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仅仅站在国家职权的位置,重视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保护。公安机关处于司法三阶段的第一线,其活动会影响起诉审查及审判等其他阶段的司法判断。检察机关只能被动地接受其递交的卷宗材料,而难以审查其真实性与合法性;中立司法机构难以介入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的活动,这样三者相互制约监督的地位就被分割开来。流水线模式使得侦查机关成为了司法断案的重心,与“法院审判为重心”的理念不符,且现阶段侦查机关的权力缺少制约,熟人社会的本质没有根本转变,使得存在的较多的腐败现象,影响了断案,造成诉讼活动中对人权的侵害。
此外,三者间联系的弊端还体现在“公检法三机关”一旦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可以推动程序的‘逆向运行”,这种做法可能使得最终的司法裁判权不在法院手上,削弱了其权威与公正性;并且使得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大大增加了办案成本,甚至违反“一罪不二罚”的原则并导致超期羁押现象的出现,使得刑事诉讼的办案效率大打折扣。⑤
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实践中的运行看来,许多不合程序的情况出现的根源都在于这种“流水作业”机制的不合理。公检法之间或过于“亲密”,相互串通会导致司法腐败;或过于“疏远”,权力的逾越会造成司法职能混同和权力的滥用,却难以在一个适当的距离中维护应有的程序正义。司法机关之间协调一致共同办案易做到,但是必须有实际而非空虚的权力能够互相制约监督。只有把握“亲密”和“距离”的“度”,才可能孕育公正。
三、请容许我的缄默——论公检法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关系
自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无罪推定”主张起,200多年的发展,该原则已深刻贯彻到西方的司法领域之中,并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从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到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有体现。⑥而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有罪推定,宁枉勿纵长期主导着司法审判。
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限定在了法院作出判决以前,都应当推定嫌疑人无罪,体现了无罪推定精神。在实务中,无罪推定还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确立,导致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个案屡禁不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等等长期存在的现象无法解决。
在诉讼中,审问方要以正当方式获得被告人的口供证据,被告人应有权对审问方作出任何只要不过于极端的反应,甚至是沉默也必须得到保障;因为现代参与诉讼的主体应是平等的,从被告方面看,他有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决定作为抑或不作为,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然而《刑事诉讼法》中第93条规定的“应当”二字,否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也在实质意义上摧毁了刑事诉讼中律师制度的价值基础;并且如果隐瞒事实,嫌疑人可能被从重量刑,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结果。沉默权是消极意义上的辩护权,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上升成为诉讼主体之重要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被告地位存在明显的不对等,若不采取有利被告原则,就难以达到控辩双方权益的合理平衡,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法律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尊重他们反驳、控诉或是沉默的自由意志及决定是否同司法机关合作的权利,以体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主体和诉讼主体的地位。更何况,我国刑诉法规定犯罪的举证责任在控方,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为自己无罪提供证据的必要。笔者认为甚至被告人故意提供虚假陈述都不应负刑事责任,因为严酷的刑法在人性的弱点面前,也应滴下温情的眼泪,这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体现。
闻名世界的“米兰达规则”明确了被告人享有的沉默权。我国刑诉法虽然在第46、140等条款中较好地体现无罪推定的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为有罪推定的定性思维所束缚,导致对嫌疑人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收集“毒树之果”及糊涂断案等现象屡禁不止,践踏着我国的民主与法治。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虽规定必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及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课以非法取证以严肃刚性的法律后果。实践中也未完全做到对非法证据的调查和排除使用,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法律上的空缺,使得违法现象普遍,辩方难以维权。中国杜培武案⑦和美国辛普森案的比较对我国诉讼程序的不合理有很好的说服力。辛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却因侦查违反了程序公正收集到污点证据而被判无罪;而“杜案”却因司法机关的主观臆断及刑讯逼供导致实质与程序同时不能达到公正,这种片面追求所谓“公平”会导致公平与效率俱损的结果。
双方在平等地位的条件下,排除威胁、强迫,在能完全表达自己意志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协商,实际上就是对繁杂程序的一种“沉默”,却在实质上达到了对自己权利的主张。这种“沉默”何时能在中国得到有效合理地实施,是中国对人权保障和提高司法效率如何并重的又一思考。
四、一架趋于平衡的天平——论抗辩双方的关系
辩护权是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是公民被刑事追究时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⑧与强大的司法机关相比,被告人显然处于弱小的地位,没有一定制度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会导致诉讼过程的残暴及结果的不公正。
辩护权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中,居于核心地位,它的有效保障与实现是刑事程序保持诉讼三角构造的前提,为维护人权的宪法理念的实现提供具体制度规范,为控辩双方保持平等对抗的格局并为诉讼程序进行的充分性提供了保障。
“从直观角度看,实行对抗式诉讼,意味着刑事诉讼就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程序与逻辑的推演过程,而是由众多诉讼主体参与对话的对流过程,刑事诉讼法的原则、规定及其使用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论辩和阐释,通过说明与澄清才能显示其规范意义,才能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以及适用范围与界限。”⑨而从杜培武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嫌疑人的辩护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他甚至没有获得自行辩护的机会。此外,杨佳案⑩中,一审辩护律师的政府顾问身份遭受质疑;一审二审法庭都违背被告人父亲的意志派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律师,这让我们不禁要问:辩护权究竟是谁的权利?难道被告方连选择辩护人的自由都没有吗? 既然如此,还谈什么平等的诉讼地位,还谈何对司法权滥用的抵御?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变更指控罪名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直接变更,即法院在经过开庭审理,通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控辩双方充分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后,由合议庭对犯罪的事实、证据以及定罪量刑方面进行评议,如果认为指控的罪名与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则法院直接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对指控的罪名予以变更,重新确定新的罪名,对被告人做出有罪判决,法院无需就拟变更后的罪名与控、辩双方协商,即“突袭审判”,它并未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利用程序法所提供的攻击和防御的机会,未从根本上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从维护程序正义的角度看,“突袭审判”是对被告人本应享有的辩护权的忽视与剥夺,使得诉讼过程缺乏本应具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法律是一架天平,它不能达到完全却应总是趋于平衡。如果它总是偏重于一方的利益而使另一方主张被忽视,则法律便失去其公正的意义。中国法制必须实施一定的改革措施,借鉴国外更为完善的制度,亦步亦趋,步步完善,使得这架法律天平在人们心中确立起权威地位,使之逐渐趋于平衡。
五、结语:期待接近正义
“接近正义”(AccesstoJustice),对司法而言,就是保障诉权,就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时代变迁,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公正、更有效地保护人民权利。我国的刑事诉讼的司法改革并不是独立于普遍性的司法改革之外的孤独实践;在各国追求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共通的理念以及可资借鉴的资源。因此,我国本土的司法改革的实践理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带有普遍性的司法改革作出观照和回应。在以“他者”的眼光考察各国的改革经验之后,重新对我国本土的改革实践进行审视,其他国家司法制度改革能提供给我们的除了具体制度设计的变革外,更重要的在于提供了一种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思维方式。
而诉讼关系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司法程序的公正程度,应当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切入点。公检法之间,公检法与诉讼参与人之间,控辩双方之间,我们期待着对这三种诉讼关系的合理调整,这需要很多智慧和勇气,有很长的路去走,但公平正义的信仰不灭,笔者也衷心期待着一个令人信服,公平正义的刑事诉讼体制,期待着以程序正义的理直气壮去发掘事实存在的真相!
注释:
①裴苍龄,易萍.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6(2).
②陈关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③汪明亮.严打的理性评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⑤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35页,第338-339页.
⑥徐升.试述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中国普法网.http://www.legalinfo.gov.cn/misc/2006-11/22/content_464552.htm.2009年5月13日.
⑦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干警,其妻子与云南省万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有染。一日,杜妻与王俊波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以逼取其口供。杜培武最终忍受不住讯问人员无所不用其极的刑讯手段,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二审法院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好在最后真凶因另案案发被羁押,供认自己系故意杀人之真凶,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杜培武的冤情得以昭雪。
⑧蒋炳仁.刑事审判前沿问题.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⑨陈浩铨.刑事诉讼法哲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⑩2008年7月1日,杨佳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捅刺、砍击楼内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造成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日上午对“杨佳袭警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杨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之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