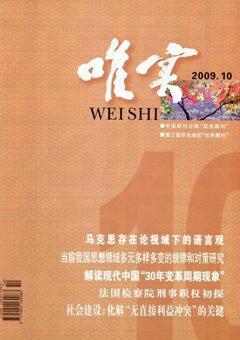论腐败的源头
黄少平 王明高
摘 要:腐败行为的主体是人,腐败的主体是社会制度,腐败的最终后果是对法律制度维系的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人性假设是制度设计的前提。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决定制度实施的有效性,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决定人的行为的规范性。因此,“人—制度—社会”的分析模式是探寻腐败源头的正确路径。
关键词:腐败;源头;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0-0025-04
基金项目:A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的配套项目之一“廉政建设中的文化功能研究”(HHUY2008-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A黄少平(1969- ),男,湖南常德人,怀化学院政法系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讲师、政治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建设;王明高(1957- ),男,湖南岳阳人,湖南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副处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反腐倡廉建设。
腐败为何屡禁不止,是人的贪欲使然,还是制度缺失导致?抑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必须支付的成本代价?诸如此类问题,学者们多有研究。然而,指责人的贪欲导致腐败,又该拿什么去消除人的贪欲?如果说制度缺失导致腐败,那么,制度怎样才能完善到让腐败止步?如果说某一发展阶段必然要成为腐败的高发、多发期,是否对腐败就只能听其自然?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上述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反腐败理念经由了严刑惩治——德刑兼备——依法治腐的发展路径,不断增多的法律制度与不断发生的腐败案件的邂逅仍让人感到些许无奈。于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腐败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要想真正探寻腐败的源头,理所当然应从界定“腐败”开始。
一、关于“腐败”的界定
界定“腐败”是反腐败的基础工作,只有明确了什么叫“腐败”,才可能找到腐败的源头。学者关于腐败定义的探讨已经很多。有侧重从权力角度分析的,如美国学者白利认为,腐败是以公共职位为中心,不正当地使用权威来获得个人利益;[1]有侧重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的,如中国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认为,腐败就是一种寻租活动;还有侧重从社会利益角度来分析的,如学者蓝庆新认为,“腐败”就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利用公众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的活动,且这种活动损害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还有些学者试图给腐败一个万全的解读,学者李文生就做过这样的尝试。他提出:在经济学领域,腐败被界定为一种寻租活动;从政治学来看,腐败是政体的退化形态;从社会学视角观察,腐败是一种消极的越轨行为;从法学角度考察,腐败是一种违反法律规范、有危害性的作为或不作为。[2]这些定义在为人们认识腐败提供更广阔的视角和有益启发的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了某种麻烦。因为,由于人们对腐败的理解差异太大,以致在研究治理腐败的对策时经常是自说自话,不能形成共识,自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常识往往能帮助人们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腐败行为的主体是人,因此,研究腐败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掌握公权者的分析,探讨腐败的源头,必须上推至对一般“人”的追问。腐败又是违背法律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所以,除了研究“人”之外,法律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也是必须考量的对象。社会是人们按照一定行为规范(法律和道德)组成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而腐败则是一些人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其中,拥有公共权力者又是产生腐败的关键群体,因为这一部分人更有条件和可能挣脱现有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约束。由此可见,探寻腐败源头,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从人和制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而不能只截取其中的一段,更何况掌权者的腐败已经是腐败浊流的中下游了。
二、关于“人”
给“人”一个准确的描述是困难的,但给“人”一个恰当的描述又是必要的。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对于人本身的研究从未停止过,也从未得出一个终结性的结论。但是,国家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又必须基于某种人性假设,或人性善,或人性恶,或不善不恶,或亦善亦恶等。人性假设是制度设计的隐含前提条件,若人性假设过于混乱,那么,制度之间的冲突必然增多。树立典型、自我教育、自查自纠、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的潜台词是人性善;死刑、群众运动反腐、“严打”等又是人性恶的必要措施。完美无缺的榜样用于宣传肯定更具感染力,但维持一个“完人”的成本比维持一个相对优秀的榜样要大得多。把人分为“善人”和“恶人”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区分谁是“善人”,谁是“恶人”。破解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善、恶二分法,找到“人”的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就是“人性趋利”。
人性的善恶两分法不仅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和宿命论弱点,还导致了一种错误思维:一个人不是“圣人”就是“魔鬼”。“圣人”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魔鬼”是不会有优点的。当一个“圣人”变成“魔鬼”时,疑问便产生了:还有多少“圣人”本身就是“魔鬼”?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人类永远无法认识自己。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在一个时期里,由于我们用精神之堤严密拦截着物欲之流,使物欲之流在精神之堤出现哪怕一丝缺口时便冲破束缚、一泻千里、无法控制。事实说明,物欲之流需要精神之堤来控制,但完全截断又是绝不可取的。既对物欲洪流加以适当而持久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否认这一事实不行,回避这一事实也不行,承认这一事实还不够,应让这种认识成为一种常识,变成人们的共识。
邓小平的一句话说得很地道:“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146
由于对人的欲望和贪欲无法做出一个精确的划分,我们这里暂且将两者之间做近似的通用。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让反腐败剑指人的欲望,只会减少问题的专属性与针对性,缺乏说服力。生命规律是永恒的法则。人的欲望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由他人有效控制。因为,规划芸芸众生的生活目标决非任何人所能轻易做到,最多只能用相应的制度去规范人的欲望所允许实现的最大边界。
在剖析腐败案例时,腐败分子毫无节制的“贪欲”往往成为剖析者浓墨重彩描述的部分,读者们也已经习惯于跟着这样的思维来解读。然而,有“贪欲”的人是否只限于这些已被发现的腐败分子呢?是否通过对这些腐败分子“贪欲”的批判就能阻止其他人的贪欲呢?答案不问自明,反腐败中面临的“前腐后继”现象也给出了明确的注脚。所以,用批判“贪欲”的方式反腐近似于道德劝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也缺乏说服力和有效性。我们并不鼓励“欲望”的恶性膨胀,但也不要试图拿“欲望”去大做文章。因为,用带有普遍性的原因去说明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不仅没有说服力,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由于人的欲望(贪欲)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应把它作为腐败产生的根源,而应进一步找出让贪欲得以恶性膨胀的原因,这样才能找到腐败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