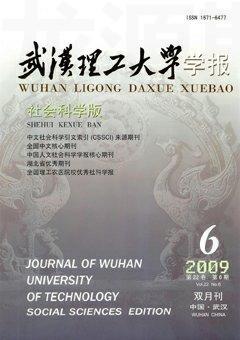太虚法师对藏传密教的融铸
丁小平
摘要:近代佛学思想家太虚运用契理契机的原则,站在整体佛教的高度,认为藏传密教只能是大乘佛教八宗之一,而不能独立于显教之上别为一教;藏传密教讲究修学的次第和大乘精神的实践,但是其自标高明的做法导致了迷信,“男女双运”的做法导致秽行流传,对社会风俗的净化没有成效。因此,应吸取藏传密教的长处,冶藏密为“中密”,为振兴中国佛教和建设世界佛教的宏图服务。
关键词:平等;得失;中密;世界佛教
中图分类号:B949;B946.6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24
一、判摄藏传密教之地位
太虚在写于1941年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一文中,将自己判教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其中,1914年之前的第一期判教,是“承袭古德的”,分佛教为“宗下”和“教下”,密教属于“教下”。之后到1924年间的第二期判教,将中国佛教先后出现的十一个大乘宗派归摄为八,而这八宗,在理论和追求的目标上都是平等的,只是在其宗教实践——“在‘行上,诸宗各有差别的施设。”[1]435
基于“八宗平等”的思想,太虚视日僧空海将佛教划分为显、密二教的思想为“邪说”,认为这种邪说必然“演成有各宗派而无整个佛法的流弊”[2]372。太虚认为,密教仅仅是佛教八宗之中的一个宗派,“大乘教中一部分之特殊行法也”,“不得另成一教”[3]238。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站在这个立场,清醒地看待密教。相反,修学密教的狂热使很多人失去了理智。1922年前后,修学东密形成一种热潮;1925年前后,又出现了学习藏密的热潮,太虚的弟子大勇、法尊等组成“留藏学法团”前往西藏学习,这些不仅使得武昌佛学院的多位院董与太虚离心,将资金转移到密教,而且直接造成武昌佛学院人才的流失,从而给武昌佛学院的佛教事业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挫折。在此之外,一些热衷于藏传密教的人,从显密二分、密高于显的立场出发,直接全盘否定汉传佛教,否定太虚的佛教事业,鼓吹藏传密教比汉传佛学殊胜圆满千百倍,如太虚弟子大刚,在西康连发两份电报给太虚,“令其先往西藏修学正法,再事弘通”[4]342。
太虚认为,密教“教理极于大乘性相,西藏亦但以陀罗尼仪轨为行法,而不别谈教理”[5]。密教在汉土作为大小十三宗之一,开元年间才由三大士传来,出现时间最晚,在发展阶段上,是显教教理向行果上的体现。按照佛教教、理、行、证的四个阶段来判定的话,汉传显教多属教、理,而密教则属行、证,彼此本来相辅相成,而不可截然割裂。具体说,密教的胎藏界和金刚界都依显教教理而得以建立,“胎藏界之教理依般若,金刚界之教理依唯识”[4],所以,密教和显教是“相应一贯”的。
密教的教理以汉传佛教的大乘性相为依归,别无独创之教理——此从契理的角度言之;若从契机的角度看,印度佛教发展到晚期大乘的密教形式,传入西藏后,适应了西藏原有的苯教文化所养成的重鬼神的民族文化心理,所以独得发展[5]347。另外,在太虚看来,大乘佛教中有一种“适应性大乘”,主要是为了适应和满足一时、一类人的心理需要,将自己的宗派予以无限抬高,“专崇密咒者,即以密咒为最胜而低抑一切”[6],藏传密教崇奉自教为最高最胜,也无非是一种方便法门而已。
再从行、证上来说,太虚认为,汉传佛教中,禅宗、律宗、净土宗都是行、证门,加上密教,则构成律、密、禅、净四种行、证门。专从行门来说,四门各有特点,而如果从四门相同之处着眼,则彼此平等,可以相互含摄[1]298。例如,如果因净土宗也依他力而可摄入密教,那么“何不以密宗仗他力故摄属净宗耶?”[7]净土宗和密宗既然可以互相含摄,那么,其宽狭、高下之分也无以为据。再专从证门来说,密教高唱“即身成佛”,一些密教徒以此独标最胜而睥睨显教。太虚从三身佛义进行分析,认为佛之一名,以证得“自受用身”为真实,所以“未圆四智菩提,不得名佛”[4]126。而如果以天台宗的“六即佛”理论来衡量,密宗所谓的“即身成佛”中,多为名字即和相似即位[2]372。他判定说,藏传密教中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最崇之阿底峡尊者,密部判位,亦只顺决择分忍位菩萨”[8]160,这相当于天台宗六即成佛义中的“分证即”位,远非“究竟即”位的“自受用身”佛。
太虚的判教思想发展到第三阶段,是在1924年之后,主要是为了面对整个的世界佛教,“应国际文化交流之世”,提出“教之本及三期三系”、“理之实际及三级三宗”说,认为第三期的密咒佛教,后来流传到中国西康、蒙古、甘肃及尼泊尔等处,“现存于世界上的可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是为藏文佛教”[1]437,也可称西藏系佛教。而三期的佛教,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如何将其圆融总摄起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整个世界的佛教,为建设新时代的世界文化而贡献佛教的力量,这是太虚所关心的。
二、分析藏传密教之得失
太虚对藏传密教的了解,始于1918年,“是冬,大师于密部经轨,就《频伽藏》一度批阅,未为深入研究”[9]50。但从此以后太虚不断利用各种机会深入接触和研究藏传密教。
在接触和研究藏传密教的过程中,太虚敏锐地发现其长短得失,给予中肯、准确的揭示。
首先,从教理建设的整体性、圆融性来说,太虚大师认为,藏传密教中,黄教祖师宗喀巴总持一切佛法,建立严整的体系,重视“道次第”,以下、中、上三士道整合并汇聚一切佛法,是西藏佛教几百年来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宗喀巴建立黄教的做法,最大的特点,在于“不没自宗,不离余法,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皆趣修证”,这样就把佛教的一切教理,都围绕着佛教修行实践的核心,而极为善巧地建立了起来。印度、汉地、日本等佛教诸宗诸祖,为了统摄一切佛法而进行判教,学说纷呈,各具千秋,然而都不及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判摄[2]314。
其次,太虚站在契理、契机的立场上,认为时处今日之末法时代,众生善根日浅,修学佛法,“当以陀罗尼门为众生学佛之方便”,具体而言,此“陀罗尼门”就是指的藏传密教。而且,从当时中国佛教的具体修行实践来看,只有“西藏之密宗,还能真修实行”,与大乘佛教的精神相应。“西藏之修密宗者,必须供养三宝,施济众生”,“无论到何处,如遇到有死亡之人,皆必与之念经咒而作各种之观想以回向超度之,并制药济病等”[10],真正实践“利他”之大乘行。这在当时汉地佛教极为衰败腐烂的情势下,确实显得非常特出和可贵,从而吸引了一批痛心于汉地佛教现状,正苦心寻找佛教出路的进步佛教徒。并且,对于针治汉地传统佛教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痼疾,也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但在赞叹藏传密教之优长的同时,太虚也清醒地看到其缺憾。
首先,太虚结合当时一些汉地佛教徒盲目崇信藏传密教的行为,分析藏传密教的诸多教理和修证上的说法,予以“祛魅”,从而使人们能够客观、清醒地认识藏传密教。
如前文所述,藏传密教以“即身成佛”来标榜,而实际上,即身成佛,并非密教独有之胜义。由即身成佛义而展开,藏传密教有一个传统,即“活佛转世”的制度,这本来是黄教、白教等的一种特殊的宗教制度,欲借此来保证佛教传承、发展的纯洁性和连续性。实际上,“活佛”二字仅仅是人们对“转世修行人”的一种尊称,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称皇帝为“圣上”,清代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一样,没有什么实质的根据和意义,本来稀松平常,“不足为奇”,“若惊以为活佛,斯则流俗之见耳”[8]156。作为宗教家的太虚当然不否认转世现象,他的目的只是要为转世者“祛魅”——“剥落其‘佛号,而将其导向人间”[11]。
藏传密教为了达到其所提倡的即身成佛的目的,有一种特殊的修行方法——“双身法”。这是一种通过男女性行为来修行的方法,太虚从教理的角度认为,“双身法”是一种特殊象征,寄托了“福智双修定慧和合等法”的寓意,真实的目的是用来“净化续生于之男女欲”,“诚为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之极致”[5]454,仅仅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而要达到这种方法所指向的目的地,其要诀仍在证“性空”之理,从佛教理论上来说,与禅宗的“佛是干屎橛,道在屎溺”[1]73同一意趣。然而,藏密末流则纯粹以此为借口达到其“多抱美女”的淫欲目的。其种种秽行劣迹,元朝末年即泛滥于宫廷,极大地损害了藏传密教的形象。
另外,藏传密教在西藏历史上自古至今几为全民所信仰,而且政教合一,却并没有在整个西藏社会的层面化民成俗,全面地提高西藏人民的素质,这不能不说是藏传密教上千年来的一个巨大的缺憾。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拉萨,当时是“民多乞丐,地皆垃圾积聚,尿屎流溢,愚陋无教育,贫病无医药,盗骗淫湎”[12],公共环境之污秽,社会物质之贫乏,民众道德之低劣,令人无法把这些与佛教盛传数百年之后的圣地西藏联系在一起。受佛教之教化且信仰佛教的“一般妇女性少羞耻,曾不稍戢淫乱——此与无上密宗的双身法或亦有关——一般官商则习为巧诈,失于诚实,且廓罗一带游牧人,多有以劫杀为生活者。杀、盗、淫、妄,竟分别蔚成风尚”[12]440。这些现象,太虚认为其原因在于西藏“一般民众,所知惟信佛供僧忏罪求福而已”,佛教在西藏一般民众的层面,成了一种寻求庇护,遮盖罪恶的工具。民众信仰佛教“忏罪求福”的低俗目的以及导致的种种问题,对于长期执掌西藏政权和教权的藏传密教来说,其所应负的责任,不言而喻。
正是在这样的见地的基础上,太虚批评当时的一些没有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的国民,不管碰到一种什么东西,“即倾倒崇奉,极度自鄙自弃,不惟普通留学东西洋者如此,而近年学于藏、学于日、学于锡兰之佛徒亦然”[8]157。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太虚认为,正确的态度应是,站在“‘汉族(即中国)佛教本位以采择佛法之古源(锡兰、西藏等)今流(日本、西洋等)而适应现代中国需要”[3]276,为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的“人间佛教”而起其辅助之用。太虚的这种世界性的眼光,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以及杂取众长、重建中国佛教文化的自强之态度,着实值得钦佩。
太虚还认为,藏传密教“易流于俗情而昧失真谛”,无法承担建设“人间佛教”的重任,所以“非将建在人间之三乘圣法与建在人天之大乘佛菩萨法,高竖起来不可!”[5]436。这样的思路,必然就走向了其“人间佛教”的宏伟建构[5]436。
三、融铸藏传密教之理论和实践
太虚早在1915年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提出派人留学日本,进入西藏学习密宗,重兴密法的主张。1922年,大勇和持松一起前往日本学习密教,之后许多青年争相效仿。1924年,日本高野山东密师权田雷斧来华传法,在12天的时间中,王弘愿就以居士身份获得东密阿奢黎的地位,引发了著名的“王弘愿风波”。一时间,东密在中国的传习蔚然成风。就在这样的热闹之中,当时一些蒙藏喇嘛“形服同俗,酒肉公开”,而某些东密追随者则称“俗形居中太,定妃为女形”,不遵法度,不守戒律,严重地损害了佛教的社会形象。太虚认识到:“今日本与蒙藏之密宗,殆已同昔年之红教,末流之弊,在所不免!”[5]425
为了挽救这种恶劣的风气,避免未来的危险,发挥东密和藏密的长处,1925年,太虚明确地提出了“冶铸中密”的主张,并阐明了建设的原则和方法。
太虚认为,建设“中密”的根本原则是:“一、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以建中密;二、密宗寺当为一道区一寺之限制”[5]425。提出第一条原则,是因为从当时日密和藏密的发展态势来看,如果不以律仪将之纳入正轨,那么“密法未能获益,未能中兴,而己先已为佛教中罪人”[5]425!以西藏密教的挫折与发展为镜,若非宗喀巴严整戒律以约束和发展,藏传密教早就全同世俗而灭亡无存了。所以,当务之急是“以出家戒律为基础,以性相教理为轨范,而后饱参日密及藏密,同化而成一种中密”[5]425。提出第二条原则,是因为“我国民性,素尚俭朴,痛恶奢侈”,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作风。而“密宗之供设,非丰富恢宏则失敬,道场之设备,非妙丽庄严则不尊”[5]425,这种作风显然与汉地传统相违,难以得到大范围的认同,与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情形也不相应,因此必须限制其寺院的数量和规模,否则必然招致世俗的讥嫌和反对,不利于佛教的整体发展。
吸取藏传密教以建设“中密”,太虚认为黄教尤其具有优长,值得学习。1930年6月,太虚为康藏学法团成员恒演《略述西藏之佛教》作序,发现昔日黄教宗喀巴整饬西藏佛教,与自己今日所提倡的“思想必以教理为轨,行为必以律仪为范”等做法,大有相同之处,他认为“重建中国之密宗,更视为非一遵黄教之途辙不为功”[2]336。这就把黄教的经验作为融铸“中密”的主要依据了。
太虚于1926年8月至1929年4月共历时20个月的前往欧美弘法的历程,大大地开阔了太虚弘法视野,从此,他以更为圆融、宽广的理念,推进佛教教育,推进中国佛教向世界佛教改进和发展的道路。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宏图,“八宗并盛”显然已经不够。在 “世界佛教”的理念下,太虚表示只要符合佛教的理论,藏传密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派,都应当采取而熔铸,用以振兴中国佛教,乃至建设世界佛教[2]339。
这种理念,太虚把它付诸于实践。1929年,他把先前在庐山建立的“世界佛学院”改为“世界佛学苑”,明确表示,针对过去“不相通贯融彻……惟有某时某地之佛法”的现状,要打破地域、时代、民族、文字的种种界限,如百川纳海,贯通融摄,“使成世界一味之佛法,以为世界人类之所共尊信者也”[2]380。随后,他又对闽南佛学院进行了改造,把闽南佛学院列为世界佛学苑华日文系,改彰州南山佛化学校为闽南佛学院分院,开设赴锡兰留学团,以作为将来建立世界佛学苑巴利文系的准备。
1930年,西藏政治出现新变化。对政治非常敏感的太虚,于11月前往重庆佛学社讲经,期间与刘湘谈及派汉僧赴西藏学经以加强汉藏沟通、交流的问题时,提出在四川建立“世界佛学苑汉藏佛教教理研究院”,“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13]819。在沟通汉藏佛教的方面,太虚的宗旨很明确:“本院以汉藏教理之名,旨在沟通汉藏佛教之教理。然汉地佛教之特点有禅宗,禅宗重在头陀苦行的刻苦耐劳;藏地佛教之特点在密宗,密宗重在金刚勇力的勤勇精进。中国民族与佛教的复兴,皆将托命于国民与教徒之能刻苦耐劳与勤勇精进。若能从汉藏佛学暂习得这两点殊胜,乃能贯澈本院之宗旨,奠定复兴中国佛教之基石。”[12]346从1932年8月20日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到1950年汉藏教理学解散,近20年的时间里,学院培养了各级汉藏文化研究人才100多人,出版刊物《现代西藏》等共6种,翻译藏传密教典籍《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十几种,完成了当时政治形势下,汉藏教理院作为世界佛学苑的分院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四、结语
太虚去世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藏传密教的传播和发展停滞了较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来,“藏密热”重新兴起,至今依然方兴未艾。半个多世纪之前,在太虚所处的时代,藏密流传之时的种种弊端:藏密学习者的过度狂热,理性和民族文化自信的迷失,佛教的显密二分,以及由此导致的藏密与汉传佛教之间的争讼等等现象,在今天,虽然因为教育的普及,思想的进步,宗教政策的放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另一方面,太虚所提倡的融摄藏传密教以熔铸“中密”,在佛教界,尽管已经有所起步,然而与中国佛教传统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的成熟形态,依然距离较远。而事实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佛教,如何融摄藏传密教以建设“中密”,使之适应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文化特质以及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有机部分,进而乃至为建设“世界佛教”做出贡献,成为世界主流文化中有机的一部分,无疑是已经摆在佛教界和整个社会之前的一个时代性的任务,需要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第一,太虚在东密传播处于热潮阶段之时,批判日僧空海将佛教划分为显、密二教,不仅是站在整体性佛教的立场,而且也意识到了这种适应日本岛国的划分,和中国大一统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理并不适应。尽管中国佛教也有宗派之分,彼此之间往往也有争论,但是,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总是处在主导的地位,差别只是圆融之下的差别,佛教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今天,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社会现实,在佛教文化的层面上,更是要求佛教首先应是整体的——不管是在教义上还是在实践上,当然各个宗派同时又应该具有各自的特色,做到“圆融不碍差别,差别不碍圆融”。
第二,太虚当时针对中国原有的密宗业已衰亡的现实,想学习并采取东密和藏密,“冶为中密”[9]109。但是因为返传的东密动机不良(为其政治侵略服务),所以,太虚把熔铸中密的重任主要寄托在藏传密教。时至今日,国际形势早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东密同样也可以作为熔铸“中密”的源头之一。东密的紧密结合社会现实,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服务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和藏密对大乘“六度”予以切实实践及修行勤勇精进的精神,一道成为“中密”重要的精神营养,进而对中国传统佛教“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痼疾予以纠治,对中国传统佛教远离现实,畸重心性的倾向予以扭转,使之真正发展成为紧贴现实,服务社会的“人间佛教”。
第三,太虚通过对密教历史的研究,认为密教在印度、西藏独立流行后,进入其自身发展的第四期,形成了以“八部众或夜叉众为本位之佛教”,与以儒家为主流的重人事、轻鬼神的汉地文化传统难以相契,所以,“仅可为人间佛教之助行也”[5]436,而无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根据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与民间迷信结合而成为民俗佛教的历史,藏密很有可能因为与汉地民间迷信结合在一起而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的发达和教育的普及同时也限制了藏密与迷信结合而发展的空间。藏密本身的鬼神文化特性,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密”的过程之中,对其予以合理的引导乃至改造,增强其人间性、伦理性和时代性,使之能在成为“人间佛教之助行”的时候,不断减少其鬼神性、封建性和盲目性。
第四,太虚主张汉藏佛法应互相学习,汉传佛教应当修学藏密的密续、佛护、月称、宗喀巴等的中观理论,并补充安慧的唯识。藏传密教则应学习汉传佛教的护法、戒贤、玄奘、窥基等的唯识,以及鸠摩罗什以来的三论宗义和安慧中论释等[13]。这些主张都涉及到汉藏佛教相互学习的具体内容,也是熔铸“中密”的具体内容,佛教界乃至社会在这方面的重视和投入力度,还有很大的空间。除了以律仪来融摄藏密,也是太虚所注意的一个方面。今日同样如此,不仅在汉传佛教方面要注重律仪的建设,而且对藏密也应着重提倡重视律仪的黄教,并以律仪严格规范僧人的行为,进一步加强对佛教的整体管理。这不仅是佛教自身科学发展的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为世界佛学的交流和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太虚大师全书:第1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2]太虚大师全书:第32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3]太虚大师全书:第29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4]太虚大师全书:第19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5]太虚大师全书:第16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6]太虚大师全书:第4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104.
[7]太虚大师全书:第33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261.
[8]太虚大师全书:第28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9]印顺.太虚大师年谱[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10]太虚大师全书:第5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140.
[11]罗同兵.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M].成都:巴蜀书社,2003:207.
[12]太虚大师全书:第27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