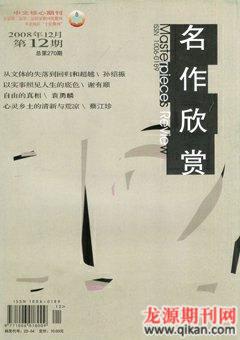从一个“吃”字看到民族无意识中的核心价值
孙彦君
【推荐理由】
孙绍振不满足于把幽默固定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追求是把幽默和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的探索结合起来。他的幽默以歪理歪推见长,但是信手拈来的文献却是经典的。除了中国的历史宝库,还有民俗和普通词汇。这使得他的行文左右逢源,触类旁通,涉笔成趣。他最为在意的往往并不是现象本身,而是其背后深藏着的荒谬和可笑;恰恰是在这些荒谬可笑中,他揭示出汉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并对之加以温和的调侃。
孙先生是学者,他的散文远离抒情,似乎不以审美为务。智趣的追求成为风格的一大标志。对于走马灯似的前卫文论,他常有保留,引起他青睐的只是话语学说和文化批评。孙绍振之所以成为孙绍振,就在于他对西方文论并不五体投地地崇拜,他一再提醒自己:站直罗,别趴下,以创作实践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他相信,任何西方文论如果不与汉语实际相结合,只能像无根的圣诞树。对那些把话语学说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人士,他评价不高。他觉得,如果话语学说和文化批评包含着真知灼见,最重要的不是无条件地加以信奉,对于中国当代散文来说,应该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分析和验证,哪怕是手工业式的分析,也应该在所不辞。
他没有像流行的当代文化散文那样沉醉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他不屑于从宏大的历史画廊汲取资源,他善于通过最平常最简单的现象,甚至是一个说法,一个字,进行思想的、文化的、艺术的探索。他曾经写过一篇《说不尽的狗》,通篇就讲一个“狗”字在中国人,在德国人、美国人心目中文化价值的巨大差异。由于幽默中蕴含深邃的文化价值,这篇文章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他还写过《谈恋爱的“谈”》,《搞恋爱的“搞”》,《论“阿拉”》,都是把思绪聚焦在一个单位的词语上的。《国人之吃》也是一样,就是以一个“吃”字,来探索汉民族的核心的潜在观念。
题目越小,施展的空间就越有限,这等于给自己一个难度,令人想起闻一多先生的著名命题“戴着镣铐跳舞”。舞要跳得好,跳得美,就需要对语言的潜在微妙有高度敏感。本文最初在报纸上发表时,题目是《论中国人的吃饭》,高度语言洁癖使他不能忍受其中些微的生硬,后来成倍地扩大了篇幅,拿到《山花》上去刊载,改成了《国人之吃》,敏感的读者不难从“国人”和“之”中感到原题所没有的典雅和古老的意味。
一个“吃”字,做成近九千字的文章,得力于对词语深层那精妙的多元、深层的探索。
首先,他对之进行文化价值的还原,把习以为常的词语悬搁起来,暂时排开、去除一切凝固的表层语义,让它回到原生状态,矛盾和怪异就显示出来了。
他从“吃”联系到“口”,从词源上追寻其文化心理的原生状态,在“人口”“户口”这种天经地义的说法中,他发现了只有汉语才有的特征:“口”的饮食功能被淡化,人数和家庭的计量单位被强化。经过还原,其中的不合理、不合逻辑,就给文章带来了一种趣味,当然不是抒情的情趣,而是心智得以启迪的智趣。作为理论家的概括力,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广度极大的概括力,不可能从普通人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神仙“不食人间烟火”,红军歌曲“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义和团诗歌“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这些毫无联系的话语之间,发现以吃为纲一脉相承的联系。他曾经提出散文当以非抒情为上,学者散文贵在审智,审智的才能之一,就是在人们看不出联系的地方找到雄辩的联系,在人们发不出疑问的地方提出深邃的问题,在人们感觉麻木的地方发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奥秘。他的智慧聚焦在从熟悉的词语中,发掘出陌生的新意,从而率领着读者从熟知的事物和观念中发现陌生的内涵。他的智慧的感染力的奥秘就在这里。
他的这种追求,和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陌生化”有很大的不同。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日常的感觉,常用的语词,读者自动化地认知了,感觉钝化了,习以为常了,就没有生动感了。作家的任务,就是把语词加以陌生化,引起读者感觉的惊异和注意的持久。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西方文学语言中常用的比喻、暗喻,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段都是以超出常规的用法来创造陌生化的感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红杏枝头春意闹”“草色遥看远却无”,等等,都可以算作是陌生化。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孙绍振意识到这个道理并不完全。在他看来还存在另外一种陌生化:他看到,“吃”不仅仅是生命的维系,而且是全部人生价值的表现,“在艰难的条件下工作,叫做叫吃苦;空想改变现状,不切实际,叫做癞虾蟆想吃天鹅肉”。吃,还和一切成败得失联系在一起,“外部形势严峻,或者手头的钞票不够用,叫做吃紧。吃一堑,长一智,用吃来形容倒霉与智慧之间的正比关系。对于外来的横逆,威武不屈,叫做不吃这一套。吃香,吃得开,说的是广泛受到欢迎和尊重,通吃,则已经超越了赌场上的含义,成为全盘胜利的概括,而吃亏和吃瘪,不但是遭遇挫折,而且是丢脸了。”所有这些由吃构成的词语和成语,是人人熟悉的,但,他发掘出来的陌生化的语义,却并不是作者运用修辞手段创造的,而是词语本身的潜在的内涵。这种内涵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这好像是他特别喜欢使用的一种方法,在《说不尽的狗》中,他这样写:
狗可能在汉语的原初意味中就包括着卑贱的意思。用不着什么形容,只要说“你这条狗”,就是很带侮辱性的。至于说“狗东西”、“狗家伙”、“狗儿子”,那就更狠毒了。若是说“狗x的”,那就可能引起武装斗争了。在汉人潜意识中,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跟狗一发生联系就坏了,至少贬值了。比如说你的脸长得慈眉善眼的,头部像神佛一样,可是一旦和狗有一点点相似,就叫做“神头狗面”,那就很叫人自卑的了,比獐头鼠目还低一等。汉人不知为什么那么恨狗,有时恨得专横,只要是不赞成的事加上个“狗”字就能把香的变臭:“狗主意”、“狗德性”。有时则恨到狗的每一个部分,从头到脚:狗头军师,狗腿子;从眼到嘴:狗眼看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从脑到肺:狗头狗脑、狼心狗肺。中国古代解剖学并不发达,但在诅咒狗方面却是大放异彩。庖丁解牛,世称绝技,而以狗骂人,没有一个不是天才,把狗的每一个零件都拿来损人,连狗尾也逃不过:“狗尾续貂”。最不堪的是,小时候曾见狗在街头巷角交尾,竟有人用竹竿把它们从中间抬起来,像听摇滚乐一样听其惨叫。
同为家畜,牛的名誉就好得多了,“牛脾气”说的是耿直,“狗脾气”说是的蠢劣。狗咬人,当然是该谴责的,却被叫做“狗咬吕洞宾”。为什么老天注定狗咬的一定是吕洞宾呢?明明有许多警犬咬的不都是贩毒分子、车匪路霸吗?就算你一个个都是翩翩风度的吕洞宾吧,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性骚扰:有《三戏白牡丹》为证。退一万步说,这不算性骚扰,白牡丹是和他自由而公开地恋爱吧,对狗的态度也不公平。马咬吕洞宾、蛇咬吕洞宾、狼咬吕洞宾,不也是妨碍自由恋爱,难道就应该给以诺贝尔奖金吗?
孙绍振事实上,是把现代词语当作历史文化价值的化石,进行某种文化考古,难得的是,写得如此的酣畅淋漓,滔滔不绝,谐趣横生。他的散文语言,凡比较生动的,常常有发人猛省,引人莞尔,让人重新感觉词语的功能。但,并不像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借修辞创造,而是凭深邃的语义洞察,不拘一格触类旁通的过程中,孙绍振常常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推理,就是在这种推理中,他获得了最大自由,有时,甚至甘冒出轨的风险。如,他这样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辩论前夕的逸事:
“当时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对于缺乏思想解放勇气,前怕狼,后怕虎的战友,十分藐视,他追问说:‘你怕什么?怕他咬了你的鸡巴!话说得虽然粗了一点,但是,却符合汉语的集体无意识中把人的精神状态与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规律。当然,‘咬还不等于吃,但是,肯定是吃的一种前奏,而且在用力的程度上,也就是在情感的强度上要比吃动作性更大一点。”
和许多当代文化散文家不同,他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并不在古代文人的逸事,而是把古老的语义作为当代历史转折关头的精神索引。他这样的推理,表面有点“歪”,可能有点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并未沦入滑稽的恶趣,这是因为他往往歪得有理。这就构成了他的歪理歪推,歪中有正,歪,可以歪到荒谬的程度,因而是可笑的,而歪到一定程度,又歪打正着,又显示出深邃的正理,这就使得幽默带上了智性的优雅。他善于以最粗野的语言表现最严肃的政治观念,语义的错位幅度与幽默的深邃和奇趣同步,达到水乳交融、亦庄亦谐的境界。他的散文里面有思想的和感觉的亮点,这种亮点,常常在最通俗和最典雅的交叉点上击发出来。这种亮点,不但是思想、语言的亮点,而且是信手拈来的材料的亮点,不管多么骇世惊俗的歪理,他都能提供即兴的论据,它们不是活在人们心头的民俗民谚,就是经典文献,而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
这不能说明中国人特别馋,相反,吃在汉人心目中,绝对不仅仅是口腹之欲,而是与人的生命质量息息相关的。精神品味档次最高的人物,叫做不食人间烟火。屈原的品质是高贵的,所以他吃的东西就不一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西游记》上,妖怪成精,要食“日月之精华”。品质特别恶劣的人叫做“狗彘不食”,而特别凶残的人,叫做“吃人不吐骨头”。
这可真是歪歪得正,歪打正着。虽然,从严格的论证要求来说,论据并不一定很雄辩,但是,读者却乐意认同:被淹没了的文化潜意识被猛然唤醒,读者感到了心智的滋润。这是多么发人猛省啊,我们竟是生活这么矛盾的文化层积之中,既如此天经地义,又是如此好玩。
写到这个地步已经很深刻,也很幽默了,但是,孙先生并不满足,他似乎担心一味发议论,至少在方法上显得单调,为了追求变化,构成内在的丰富,他总是不失时机,用短小的叙事进行穿插:
我小时候,在上海青浦读小学,对于极其厌恶的家伙,喜欢在墙壁上写标语加以愤怒声讨:最常用的一条是:“某某某吃卵三百只!”这个卵,不是鸡蛋的意思,而是男性生殖系统中最突出的一部分,水浒传上和闽南话中都写作“鸟”,粗话叫什么,大家都知道,不便写入文章。现代汉语中,近来,有了一种昵称,叫做“小鸡鸡”,或“小鸟鸟”,正如,小哥哥,小妹妹一样。
如果在抒情、审美散文中,这最多只能是一笔带过,而他却不厌其烦地把语义从各个侧面展开(卵、鸟、鸡鸡、小哥哥),幽默感就在这种链式谱系中被强化了。每逢此类环节,孙绍振总是不放过层层推进的机遇。几乎每一层次,都透露出一重孙绍振式的机智和谐趣。而下面的叙述以小便做药引的尴尬场面,则突出了另外一种风格。如果前面的引文,可以说是包含着讽世的话,下面的引文则是以自嘲,也就是自我调侃为特点:
……就连小便,也是可以吃的。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记忆。
那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逃难到乡下。有一天,吃完晚饭,我被叫到房间的当中,一向严厉的爸爸,破天荒让我站到桌上去,并且拿了一个相当精致的瓷碗放我面前。要我在把小便拉在里面。当时我四五岁,已经模模糊糊感到代表男性的尊严的那一器官,是要严格保密的,不能示众的。不能像小狗那样在大庭广众之间,随便抬起腿来方便,只能偷偷地在墙角。突然间,要我当众把它掏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岂不羞死我也。然而,父命不可违。而且那么多人的眼睛,都放射出期待的光。我勉为其难迟迟疑疑掏了出来,但是,就是拉不出。父亲鼓励再三,仍然无效。最后还是妈妈理解我。说:孩子害羞,大家把眼睛闭上。这一下真是有如神助,碗里顿时就满了。
孙绍振曾说过:抒情是把人物和环境美化,而幽默则不回避“丑化”,让主体人物处在尴尬境地就是自我调侃,这在美国幽默理论中被认为是最有品位的。在桌子上小便的场面,在抒情散文中,肯定避之犹恐不及的,孙绍振却是一层细节、一层心理的变化进行剥笋壳式的展示。越是强调孩子的狼狈,越是显出传统观念中的“吃”文化的怪异,作者的幽默感也越是显得坦诚、率真。
孙绍振在这里追求的,显然是让读者细细品味“审丑”之美。
借助于文化还原,“吃”字本来非常狭小的空间变得宏大。但是,他显然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广度,接着他又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展开他的神思,为文章打开了一番新天地。他运用拿手的辩证法,把事情放在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中国人在小年夜祭灶,用灶糖讨好灶王爷,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对神灵,也是以吃为贿;而另一方面,他指出以《圣经》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却相反,是神把自己的身体给信徒吃:
基督教每周的“主日”(即周日)有这样的聚会,叫“擘饼聚会”,意思是纪念基督的死与复活。基督徒吃的面团,象征神的身体,饮的酒代表神的血液:《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如果在教堂的神坛上,将中国祭祖宗的猪头供上,不知基督是否宽恕亚当后代的罪行。
这就不仅仅是打开了思考的广度,而且提供深化的天地。东方和西方宗教在神和信众之间的关系上,在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救赎的差异,跃然纸上。而这样的思想深度,正是他所追求的“审智”的深度。
他的文风亦如他的讲座,读者感受最强的是他的自由放达,潇洒不羁,如天马行空,思绪纷纭,翻新出奇;如云蒸霞蔚,飘然而至,忽然而逝,戛然而止。他的议论是智性的,带着纵论的风格,循规蹈矩地演绎与他无缘,不屑以论点为先导,更不屑屈从固定的格式。奇思妙想总是起于一种感觉,一个现象,乃至一个语义的还原和比较。反复追问现状,又不断自我非难。即兴感应,随机生发,导入荒谬,激发深思。难得有所记叙,并不依赖时间顺序,涉笔成趣,点到为止。其深厚智趣,得力于逻辑错位,似无理而有理,近武断而深刻。民俗谚语,文献掌故,自我经历,忽聚忽散,无序中有序,逻辑似正似歪,似歪亦正,将谬就谬,歪理歪推,歪打正着,莫不引人莞尔,又发人深思。难能可贵就在于:幽默和智慧达到平衡。
作者系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