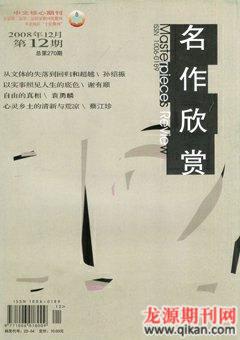从细节上颠覆历史的宏大话语
孙绍振
【推荐理由】
余秋雨的散文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至今没有停息,但是,从学术上也没有进展。原因就在就余秋雨而论余秋雨。其实,余秋雨的评价问题,要和南帆联系在一起才有希望得到解决。大凡对余秋雨无限崇拜的读者,读懂了南帆,就可能理解为什么一些论者总是对余秋雨的散文不满。大凡对余秋雨不满的论者,只要读读南帆就会有无限的欣慰感。
余秋雨的出现,引发了散文界一场大争论,除了文史知识的“硬伤”以外,关键在余秋雨的所谓“滥情”。持这种说法的人士相当广泛,显然,有不够公平之处。如果把余秋的散文当作“滥情”的标本,则许多名家很难逃“滥情”的恶谥。问题可能并不在余秋雨,而在读者。不是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吗?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余秋雨。
一般的读者,厌倦了流行的、老套的自然景观的诗化的赞叹,一见到余秋雨的情智交融,自然而感到耳目一新。而另一个层次的读者,受过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熏陶,他们的文学趣味重在智性,在文学中追寻人生哲理的阐释,在他们看来是最高境界,因而,对于抒情持某种拒斥的立场。对于余秋雨散文中的抒情成分,自然十分厌恶。两种读者事实上是代表着两个时代,两个流派,文学鉴赏经验和趣味相去甚远,争论起来,有如聋子的对话。
批判余秋雨滥情的人士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很少举出超越滥情之作,就是勉强举,也只是顺便提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毕竟时代距离遥远,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站在两派之间的读者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超越审美的、审智的散文在当代世界文学领域中比比皆是,如罗兰•巴特《艾菲尔铁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无用”。但可惜的是,论争的另一方,并不熟悉,甚至也并不认同其艺术成就。如果能举出我国当代的散文,对话的有效性就可能提高。当时,在参与论争的时候,笔者就举出南帆的散文。以他为代表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超越抒情,冷峻地审智,以突破话语的遮蔽为务。但,七八年前,南帆的散文还不具有经典性,此论并未引起注意。可喜的是,事到今天,南帆的散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获得了《人民文学》的大奖以后,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有了南帆这样的成就,再来看余秋雨的评价,就不难把问题的要害弄清楚。
南帆不像余秋雨那样关注自然风物,就是写到也很少赞美。能与自然景观挂上钩的,可能就是那篇《记忆四川》,他也正面写到了三峡,也有些“雄奇险峻,滩多水浊,朝辞白帝,轻舟逐流,涛声澎湃”的词句,但是,他似乎并不怎么为之激动,他关注的是:“李白遇到的那些猿猴还在不在?”等到出了三峡,两岸平阔了,“江心的船似乎缓慢地停住了”,这时,如果要让余秋雨来写可能要大大激动一番了。可是南帆却这样说:“这时,不用说也明白,四川已经把我们吐出来了。”就是日后翻阅日记,在回忆中,也并未被美好的山河所激动,所有的感想,实也仅仅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确到过四川”。从这里,可以想象出能够欣赏南帆这种“酷”、这种冷峻的读者,读余秋雨那样的诗化主导的智性思考,是个什么感觉。
南帆在另外一方面也和余秋雨很相近,也喜欢写人文景观,但是,在余秋雨那里人文历史的价值是神圣的,充满了诗意的,而在南帆这里,历史固然有神圣的一面,但是,他却冷峻地怀疑神圣中有被歪曲了的,被遮蔽了的。他以彻底的权力话语解构和建构的精神,来对待一切历史的成说。他在《戊戌年的铡刀》中,并不像一些追随余秋雨的、年纪并不轻的散文家那样,把全部热情用在烈士的大义凛然上。也许在他看来,文章如果这样写,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了。他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用了一些笔墨考证腰斩那样的酷刑。当然,他才智发挥得最淋漓的地方,却在写六君子中的林旭。为什么要选中这个人,因为是他的同乡?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从林旭身上发现了历史定案存在着的遮蔽。虽然梁启超在他牺牲后为文说他“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把他捧上了天。但是南帆认为这是有意夸张。因为梁启超自己亡命日本,对牺牲的战友心甚抱愧,溢美之词,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补偿”。南帆更感兴趣的是,历史的主导价值如何掩盖了复杂的真相,林旭和林琴南有过联系,触发了他思想突围的火花:如果林旭不是23岁就牺牲了,而是活到70岁,那就是他的朋友林琴南的年纪。英雄林旭会不会变成“五四”时期另外一个林琴南呢?这样的思考,就其价值取向说,和余秋雨是背道而驰的。余秋雨对就义的英雄,绝对不会有这样杀风景的想像。但是,南帆对任何历史,哪怕是全民共识的英雄,也是要冷峻地洞察其中的偶然性的,诗性的赞美,在他看来,可能是为权力话语的陷阱。他还敏锐地联系到陈独秀只比林旭小四岁,鲁迅只比林旭小六岁。面对这样的资源,如果要抒情,可能洋洋洒洒,展示情采和文采,但是,他习惯性地避开了抒情,沉浸在睿智的深思中:谁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谁又注定定格在古代的士人的形象上,是不是必然的呢?是不是也有偶然的因素呢?为什么英雄就一定是林旭,而不是只小了四岁的陈独秀,也不是比他小了六岁的鲁迅?只有历史的非必然性,才能激发南帆的情采和文采。正是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他深邃到不避“荒谬”的程度:林琴南如果不是因为新娶了一个娇妻,贪恋闺房之乐,而是随着林旭一起上北京,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变法烈士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那个反对白话文的保守派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戊戌变法的烈士呢?南帆得出的结论是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正是在这里,读者可以领略他解构主义的神采。当然他与那种霸占话语制高点的人士迥然不同,他的目的不是挟洋自重,而是为了获得高度的思想自由。
这种自由的获得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也不是鸡毛蒜皮的考证,而是从关键的历史细节中重新发掘,他发现,林琴南的一个学生林长民,在今人的心目中,他的重要性只是福州美女林徽因的父亲,然而,事实上,他的最大功绩却是第一个在报刊上发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屈辱的消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时在五月二日,“五四”运动之所以在五月四日爆发,和他的这篇文章的关系是很大的,比他是林徽因的父亲不知重要多少,但是,至今却湮没无闻。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是余秋雨,他可能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遗憾来作高强度的抒情,而南帆却由此而上升到对形而上学的思考:
我的叙述如此频繁地使用“历史”一词。然而,许多时候,这仅仅是一个庄严而又空洞的大字眼,一旦抵近就会如同烟雾一般消散。
从把散文当作抒情艺术的人士来看,南帆好像不像是在写散文了。然而他的确是在写散文,不过,他不是在写传统式的审美抒情散文,也不是写像余秋雨式的把诗情和智性结合起来的散文,而是写另外一种散文,在这种散文里,不是把审美情感放在第一位,而是尽可能把审美感情收敛起来,使之与智性的审视结合起来。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散文中充满了理性,已经不像早期某些散文那样,沉醉于推断,近来,他似乎找到了理性与感性的中介。这个中介不是感情,而是感觉。正像现代派新诗那样,舍弃了抒情,但是,却抓紧了事物的具体感觉。正如洛夫在台湾新诗大系所说,关上了抒情的窗子,却打开了感觉的窗子。因而思想突围并未陷入抽象,而洋溢着理趣。他写到林旭在百日维新期间和光绪皇帝的对话时,特别富于感性趣味;林旭一贯讲福州方言,就是在南京到北京几年的工夫,他的官话,“也好不到哪里”:
那一天召见的时候,光绪皇帝满口京片子,林旭答得磕磕巴巴,许多话根本无法听懂。光绪皇帝皱了一阵眉头突然灵机一动,吩咐太监摆上笔墨。每当林旭福州式官话荒腔走板得太厉害,光绪皇帝就命他将奏对之言写在纸上。往后的日子里,笔墨的辅助竟然成为他们君臣对话的基本模式。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耍弄一些小噱头,但是,在描写上惜墨如金的南帆之所以要特地运用细节,却是因为这个细节不是一般的,而是历史的细节,具有决定变法成败的作用:
……林旭的一张纸片却不慎落在宫里,竟然被李莲英的亲信拾到,上面写的恰恰是康有为的一系列密谋,于是,“新党死机,遂定于此矣。”某些关键时刻,历史的重量的确只像是薄薄的一张纸,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从平凡的细节上看出历史转折的偶然性,这是思想的洞察力也是艺术的雄辩性水乳交融,南帆在这里,真是举重若轻。他是在运用他的学理来感觉历史。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接着说:“其实,我看不见历史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个福州乡亲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有些时候,机遇找了上来,画外音地成全了他们,另一些时候,他们舍命搏杀,历史却默不作声地绕开了。多少人参得透玄机?”相信欣赏过余秋雨的读者,再来读南帆,真正读懂了他追求从细节上颠覆历史的宏大话语,就不难发现,南帆和余秋雨的思想和艺术的距离,不是地理的,而是时代的。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