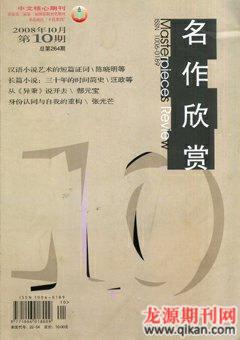超越“伤痕”的伤痕回顾
施津菊
【推荐理由】
《地球上的王家庄》在叙述视角和审美境界上不仅显示了作者与他当时的《青衣》《玉米》等中篇不同的追求,使之更具短篇的诗性;也超越了当代文学对那段历史记忆的伤痕抚慰和政治反思的思维模式,用乡野民间质朴自然的方式,表达了人对形而上的精神家园的永恒渴望与执著追求。可以这样说,小说在尝试建立一种摆脱当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想象与叙事景深,朝着更具人性普遍价值追问的方向衍进。当然文学也没有必要完全摆脱历史视景,因而,从故事的整体架构,尤其是小说结尾,我们依然能明显感觉到那个时代的背影并具有历史的在场感。
毕飞宇(1964- )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小说创作,90年代《哺乳期的女人》等作品为他赢得声誉,新世纪进一步发力,中篇小说《青衣》以及系列中篇《玉米》《玉秀》《玉秧》都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良好反响,长篇小说《平原》也受到好评。他的作品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奖,还改编为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电视剧《青衣》。他对当代农村有着独具只眼的观照,尤其擅长表现女性的悲剧命运与复杂隐秘的心灵世界。在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毕飞宇是有着骄人成就的。
2002年《上海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毕飞宇创作中又一别开生面之作,被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列为当年短篇的榜首。
小说以一个八岁的蒙昧未开的牧童视角和童真的眼睛带领我们走进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地上有个叫做王家庄的地方。只是,这个牧童是在水面上放牧鸭子而非草地上的牛羊。他眼里的世界简单纯净,一群数也数不清的鸭子、一条小河,还有一片水面“特别阔大”的乌金荡。他的日子也由宁静的水面、碧绿的水草、欢实的鸭子以及草虾游鱼组成,王家庄在那孩童的心目中原本是有着天堂般的宁静。然而,幼小童稚的心灵,并不满足于这种宁静,已经在渴望了解世界上那太多的未知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这种渴望依然是不可压抑的人之天性。而在当时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速成式的教育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刘胡兰、雷锋的故事已经像随风飘散的种子播撒到了“我”懵懂颟顸的小小灵魂里。小说到此都一直氤氲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轻描淡写之中,那个历史时代的疯狂与斗争的激烈氛围都被滤去了,这也为后来王家庄年轻人的精神探索做了含蓄自然的铺垫。
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的风雷激荡,王家庄之于“我”,仍然是水乡牧鸭式的天堂。而这天堂里的不和谐因素,居然是父亲。父亲似乎不属于王家庄,他永远也晒不黑的双手和屁股便是标志,这也就注定了他是孤独的异乡者;正如他儿子所说,人间的麻烦是如此巨大,他不问不管,却去操宇宙的那份心,而面对现实的沉默、白眼和对黑夜之中宇宙星空的迷恋,又使他完全不附和那个时代激励人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革命潮流,而显得乖戾并成为异端。更甚的是,父亲带回家并挂在山墙上的那张世界地图。可谓一图就激起了王家庄年轻人心底的千层浪。他们那诸多的问题如果单纯地从科普知识的角度看,即使是上个世纪70年代,也已经有了《十万个为什么》,或者是父亲手中的《宇宙里有些什么》,只要有一套这样的书在手,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但地球上的王家庄就是没有。所以才自然而然地引发出那些让他们一度恐慌不得安宁的问题。
仔细想想困扰王家庄的年轻人的那些问题,就像世界“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大”这样的疑问,似乎太形而下了,恐怕只有王家庄的人才会这么小儿科。当然,在知识和文明遭到践踏和封杀的年代,只要是从来没有见过家乡之外的世界的人,不管是李家庄或赵家庄的人,都可能也只会用那样的眼光衡量和思考外面的天地。虽然每一个人眼中的自身和世界都可能是不一样的,但人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却又有着共通之处。小说的自然巧妙之处也就在于借一张世界地图表达了人类心灵共性中的一部分——即使是那个渺小的在世界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王家庄,即使是处于那个特定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蛮荒岁月,即使是在那个意识形态的灌输替代了科学知识传播的政治高压年代,也仍然没能泯灭王家庄的年轻人、包括蒙昧无知的“我”,对自身、对世界的求知渴望和对未知世界以及世界尽头怀有恐惧的自然天性。固然,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文化精英科学家在前仆后继地探索着人的自身,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宇宙航天等等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在从不同的路径用不同的方法在不断地揭开人的秘密、探索世界的奥秘和通向宇宙的道路。他们的探索专业精深令人敬佩,而王家庄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用那种幼稚的热情和那种率真的口吻所表达的疑惑与恐惧,说到底其实和历来的科学文化精英们所做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只是路径和方式大相径庭而已。哲学家在问“我是谁”,文学家在想“我在哪儿”,现代思想家感叹人是“大地上的异乡者”,而王家庄的人则愤慨地说:“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对此,谁能说王家庄的人所表达的不是对自身存在的关注和对世界疑问的探求呢。
对于现存的价值与人的存在,历来属于人对形而上的哲思层面之最。王家庄的年轻农民当然不懂哲学,甚至他们对世界地图和整个地球的理解都带有盲人摸象的性质,所以,他们的表达是“如果我们像挖井那样不停地往下挖,不停地挖,我们会挖到什么地方去呢?”由此便引出了终极与存在之间或关系密切或无关紧要的疑问:“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托起了我们?是什么支撑了我们?”这些问题均出自一张世界地图引发王家庄农民的思考,似乎很能够传达那个时代的一些什么,因为知识的匮乏,他们的担忧很有些无师自通又自作聪明,也很有些杞人忧天的味道。然而,那些问题仅仅只是对掘井式的穿透地球之后人便无处着落的忧患吗?当然可以简单地这么认为,它就是那个年龄段的那些人在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忧患意识的自然流露,同时,它又远远超越了王家庄那个具体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它实在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中的那些爱想事的人都可能会想一想的问题,甚至,它是摆在任何一个社会化文明化的个体或群体面前的一种难以回避也无可逃脱的价值选择与终极取向。是什么托起和支撑着眼前的这个世界,难道仅仅是地球和包围着地球的大气层?从地理课本上的常识角度看,这么说当然没错,但还有更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就是传统、文化、现存的伦理规范、社会观念、价值体系等厚重的文明系统。这才是人有别于动物并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王家庄的年轻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好像幼稚得可笑,当然掉不到地球的外面,肯定还在地球上。同时,这个问题又极为深刻,我们的肉身依然还在地球上,但没有了心灵的支撑,便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大地上的异乡者”,就是人们掉进那个“什么地方”之后的状态——永远漂泊和流浪在寻找家园的路途上,但注定永远无家可归,灵魂备受煎熬永无宁日。这是怎样的虚空和疼痛。还好,虽然王家庄的人也承受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之痛,但至少,地球上还有个王家庄包容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一切蒙昧与狂妄,至少,那时的他们还可以在自己的家园里继续他们切身而又空灵的思考和争论。
“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这就是说,我们掉下去之后,既不会被摔死,也不会被淹死,我们只能是不停地坠落,一直坠落,永远坠落。”面对一张把地球一分为二的世界平面地图,按照王家庄青年农民的思维逻辑来看,确实总有一刻会走到地图边缘那条清晰而果断的弧线上,抑或,在暗夜里真是一不当心便会跨过那条弧线,而那条弧线之外,在地图上的标志确实既不是陆地,也不是海洋,那又会是什么?在王家庄的年轻人看来那就是无底的深渊了。既然是深渊,人就只有一种状态——坠落。由一张地图生发出对世界尽头的想象和恐惧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地图上的那条弧线以及世界尽头的想象,不仅在王家庄人的心中,也在所有的人心中暗藏着另一层更为深层和隐秘的恐惧。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当生命跨越过那条可以感知的弧线——生之后,生命进入了怎样的状态呢?已经死了,不能再死,所以,“不会被摔死,也不会被淹死”,而生命的单程性注定也不能再生,那么,已死的状态便成为人们想象中的一个莫大的虚空和巨大的黑洞。基督徒们有天堂的彼岸,穆斯林们有真主安拉的拯救,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宗教会给灵魂一个死后的安放,而那个时代的王家庄的年轻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都没有。深渊中的坠落便是他们的认定,所以,他们必得承受“无边的恐惧,无尽无止的恐惧”。同时也因为是无神论,唯物的客观存在又安抚了他们内心无助的忧惧,让他们能够很快地回到眼前的真实存在。但这也已经让他们真实地体验了一次灵魂的历险和精神的探索,他们的争论和恐惧让他们明白了世界之中确实存在那种 “奇异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其实,这种未知的力量不仅存在于王家庄之外的世界,也还历来就暗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正因为如此,八岁的“我”,在经历了这次心灵历险之后,想用自己的脚和眼睛去寻找答案:“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一个八岁的村童,划一条小舢板,赶着一群自己都数不清的鸭子,去寻找世界的边缘,去做当年哥伦布式的探险壮举,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何等的浪漫执著,又是何等的稚嫩可爱,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以上是这篇小说叙述的意义层面之一,它用人物简单幼稚的方式、直白的语言和朴素的动机,生动地传达出人们探索世界奥秘的本能渴望和对生命与世界终极的深刻追问,而这又是不论任何时代中的任何环境,或任何种族中的任何个体,都可能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自然流露的天性使然。
小说的另一意义层面,就是父与子之间的那种神似。尽管小说在结尾之前有几处都流露过“我”对父亲的不理解甚至是不屑,但不论是先天遗传基因的神秘选择,还是后天习得的情感趋向,在一个小男孩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我” 产生了心理危机的时候,还是“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我”的历险不能不说与父亲的暗示有关,父亲在黑夜里用他的眼睛去探索宇宙的奥秘,而“我”则像父亲说的“要用你的脚”去寻找世界的终极。“我”骂过父亲神经病,是在那一刻确实觉得父亲就像别人说的那样是神经病,而王家庄的人叫“我”神经病,则是认同了父亲对“我”为寻找世界尽头而丢了鸭子的评价。在王家庄的人们眼里,我们是一对神经病父子,都属于异类。试想一下,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文化沙漠的王家庄,这对父子以其对世界和宇宙幼稚但执著的探索行为而有别于周围的人们,获此殊荣,当然也就不足为奇。
小说的结尾既是历险故事的结局,在那个时代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同时也从叙述的技巧,回应了前面对父亲的铺垫,完成了观照一个小男孩的成长中对父亲的天然依恋以及如何获得心理平衡的过程。这也是人性光芒中的一缕吧。
《地球上的王家庄》采用的是儿童视角,实际上寄寓着作家自身的深沉思考。小说反映了父子两代在那个失去精神家园年代的迷惘与寻觅,是超越了“伤痕”的对伤痕年代的回顾,因而别具一格。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