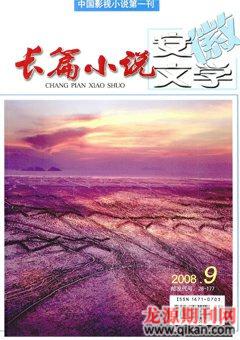墙上挂着一张弓(外一篇)
韩 光
乡下老家的东山墙上,至今仍悬挂着一张弹羊毛专用的弯弓。深褐色木弓衬在斑驳陆离的灰墙上,如一幅凝重、静穆的油画。每次品读,都能读出谢世多年的父亲佝偻的身影。
父亲青年时期在归德(商丘)府跟师傅学过擀毛毡手艺,后又在界首毛纺织厂当了几年师傅,土地下放毛纺织厂关闭,他重回到泉河边小刘庄,边务农边做擀毡的零活。
父亲庄稼活不大在行,擀毡的活又极少,随着不断添丁加口,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八口之家眼看揭不开锅了。他说我要出去找活!正当一家人为此计划欢欣鼓舞时,一个不容置疑的难题凸显出来,弹羊毛咋办。
擀毡的第一道工序是整毛、弹毛。油腻的绵羊毛须用干土拌、棒槌捶、菜刀剁、竹篾抖、弹花弓弹。羊毛纤维长,拉力强,容易打刺条揭辊子,一般的弹花人家不愿揽这活,平时父亲跑五六里远的一个朋友家去弹,出外做活,到哪里弹羊毛呢?
那几天晚上,父亲一个劲地吸着手拧的喇叭筒烟,满屋子呛味。有天夜里忽听父亲说,咱也制一张木弓吧,在归德学活时,弹毛都是用木弓。
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将我喊起来,一起掘了粪池边一棵桑树。借来木工的锯斧锛刨,又锯又砍,再用麦糠火烤、石磙压、麻绳绑,忙活了半天,一张弯弓捏成了,父亲到泉河南岸李湾皮匠家,割了十多根皮弦。我怀疑,这玩意能弹羊毛?
父亲不说话,将绳子一端系在梁上,一端系在木弓中间,下置一木板,木板上是整好的羊毛。父亲左手执木弓一端,右手挥动木槌。木槌拨击皮弦,那弦被拉紧、拉紧,当弹力大于张力时,皮线冲出木槌的阻碍猛力弹向羊毛,噗地一声,弹上缠满羊毛,操作者将带毛的弓弦移开,用木槌拨击皮弦,嘭、嘭、嘭,缠在弓上你拉我扯的毛被突发的力量撕裂、崩烂、振碎,瞬间,羊毛似春风吹拂下的朵朵梨花,飘飘洒洒落满案头。噗,嘭、嘭、嘭……噗,嘭、嘭、嘭……随着节奏极强的弦响,个头不高的父亲侧着身子,挥动右臂上下跃动,那姿势是我眼中最美的舞蹈。
自此,父亲用辆旧自行车,带着擀毡棍、擀毡布和那张自制的木弓,长年累月辗转在河南沈丘、项城、平舆乡村,为人们擀毡坎毡裤毡靴毡袜毡帽。
擀毡的活,从整毛、弹毛、铺毡、蹬毡、洗毡,样样都得掏力气,一道工序下来就是一身汗。有回队里催要口粮钱,娘让正上小学的我去找父亲,我循着线索找了三天,跑了十多个村庄才找着。记得正是隆冬时节,我穿着棉袄仍冻得直打牙颤,正弹毛的父亲穿一件几近灰色的白粗布单褂,后背透湿,他看到我仍不做声,噗,嘭、嘭、嘭……只管斜身跃动,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下,我发觉父亲的腰比先前更弯了。
我心一阵颤抖,不忍心说出要钱的事,还是他先说了,队里要口粮钱了吧?说罢从衣兜里掏出二十块钱,我接过那钱,觉得异样沉重。
后来,我们兄妹大了,我到城里上班,父亲就带弟弟妹妹们在家开了个擀毡作坊,擀成毡条裁成棉鞋垫出售,生意一度红火,相继添置了柴油机、弹花机。家里人多,房浅屋窄,那张闲置的木弓没处放,娘随手挂在山墙上。
1991年父亲得了喉癌,气管切开不能说话,双手仍不停闲地喂牛、拉粪、抱孙子。闲暇时,他的眼神时常游移在山墙上,用那凄婉眷恋的目光,抚摸着那张曾浸透他汗水的木弓。父亲去世那年65岁。
每到年节全家相聚,娘总指着墙上的木弓对我们说,要记住,你们是你爸用这张弓绷着吃长大的。再看那张木弓,在土墙上划过一道流畅的弧线,拱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泥房子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父亲用泥巴团筑房子的故事。
父母结婚后被爷爷分了出来,两人合计了三个半夜,开始在村前砂礓坑北边的一处荒宅上做文章。父亲从坑底地头挑来两大堆细土,撒上碾碎的麦秸作稔草,好似现在盖房子使用的钢筋,从砂礓沟底一桶桶向上担水浇上,待土浸透,赤脚上去反复地踩着,土里时有碗碴或瓦片,将脚底板刺破一个大口子,殷红殷红的血掺进了泥土,简单包扎一下,又要上去踩泥,踏过一遍再用钉耙扒翻一遍。父亲虽出自农家,却是个没大气力的手艺人,不等泥巴翻一遍,双手已满是血泡。这活不能歇呀,他不停地用钉耙翻着,使铁锨铲着,血泡磨破了,再长出来,长出来又被磨破,半晌下来,钉耙把子被染得通红!
泥巴翻过一遍之后,还需再撒麦草,再浇水,再踩,再翻……就这样,要经历撒三遍、泼三遍、踩三遍、翻三遍,一堆墙泥总算和成了。
开始搭墙,母亲用双手从泥堆上挖出一块,将泥巴块团成一团,父亲用钗一团团地燕子衔泥般往上垒,这般如此三五天,一圈子泥墙齐着腰窝深。父亲抡起三股钗,刷刷刷削去多余的部分,这叫作刷墙,原来看上去疙疙瘩瘩的泥巴堆,半晌工夫,魔术般地变成一截齐崭崭的矮墙。
如遇天晴,需等上三五日,便可继续搭第二截墙;如遇阴雨,则要看天说话。新墙如豆腐嘛,须等墙体结实些再往上垒。这期间,也不是闲时候,又要挑土,担水,和泥,一遍遍简单重复着无休止的繁重劳作,这堆墙泥刚和成,那边又要搭第二层墙了。搭第二层墙,形式上是对搭第一层墙的简单重复,可劳动强度却大大增强。一块斤把重的泥团,要搬人把高。搭第三层墙时,更是吃力,搭上简易的脚手架,将泥团举过头顶,一天成百上千次地“举重”。脱坯搭墙,活见阎王,即使是铁人,也会累折,父母忍着痛,咬着牙,用他们单薄的躯体,硬是将八九尺高的新墙堆成了。
大小戏是一样的唱法,请来木匠砍房料,安门窗,装山上梁,绑上向日葵杆阁子,铺上高粱秸廊子,摊麦糠泥,自下而上一层层铺麦秸草,前后合龙,泥脊盖瓦,天爷爷,两间泥巴房,历经一个多月总算盖成了。
娘说,每盖一次房子,人就得蜕一层皮。
俺家宅基地势低,大雨小雨都能使泥房子脚脖一软,立马瘫在水里。水后再搭,搭了再淹,老天尽与人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那软软的泥团,磐石般沉重,压得父亲母亲长年喘不过气来。
我记事的时候,社员建房子采取互助的形式,叫吃房子会,大伙出资出力,较之以前的单打独斗优越多了。那时盖房子已经有人用砖墙根脚了……七十年代初,始有“砖封檐,瓦简边”较为时髦的房子。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场大水,将全村二百八十间泥房子、瓦简边、砖墙根全部淹倒。大水过后,父母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在村中大塘的西北沿老宅上,三天时间垒了一间坐西朝东的临时趴趴屋。八口之家,咋能住下呢?挨着北头又接了一间,后连续接了三间。人家给我提亲,相家的看了说,他家住的是一节一节的火车皮呢。
当人们的手头开始活便起来,村里对群众建房开始规划,我家新划的宅基在原生产队东边的打麦场上。一家人紧挣紧省,连磨带借,1980年夏,终于建起了三间砖瓦房,父亲说这下再不怕发大水了。至此,村里已相继建起了一排排的砖瓦房,前年,有冒尖户开始建楼房了。现在不大的村子,楼房已建起好几栋,泥房子连影子也找不到了。
出自农家的我,终于从泥房子破“壳”而出,化蛹为蝶,在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间飞翔,即使飞得再高,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始终连着那片曾经生长泥房子的土地。
责任编辑苗秀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