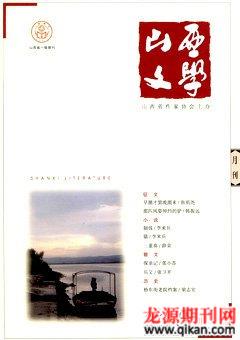那匹风姿绰约的驴
韩振远
一
1982年的10月,我刚刚建立的家庭里添了一位新成员——那匹风姿绰约的母驴。
那年的秋天十分古怪,不停刮着燥热的风,没有一点秋高气爽的感觉,麦子播下去没多少天,地里已是一片绿色,呼呼往上长,眼看就要拔节。各村的土地都分了,几十年来见惯了成群结队干活的人群,麦田里零零星星的人倒显示出一种久违的从容与悠闲。那天是周末,公路上到处是家在农村急于往回赶的人。在学校一周,我有点想念新婚妻子了,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到家门前时,才想起妻子这会儿大概还在镇上的一个小工厂里上班。
家里静悄悄的,走进院子,眼前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我家后院上房门前竟拴着一匹缁身粉嘴的驴。从我记事以来,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动物,我也从没想到家里会出现一匹驴。看见有人走来,这位不速之客惊讶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美丽修长的眼睛传递着惶恐。我惊讶地盯着这匹驴看,发现她竟长得如此秀气,黑色的皮毛缎子一般油光灿亮,身段匀称,淑女一样亭亭玉立。见我望她,一对长耳轻轻摆动,眼睛里有了几分含情脉脉的意思。那一刻,我甚至有点怀疑这驴是不是新婚妻子变的,在故意和我开玩笑。
她出现得太突然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不明白我家为什么会拴着一匹驴,但意识到肯定她与我家有关系。她似乎也在猜测我是谁,一双眼睛痴痴地望着我,作沉思状。一个人和一匹驴相互观望,总显得怪怪的,把我家破旧的四合院都弄得有些尴尬。她好像想和我打声招呼,粉白的嘴往上扬了扬,修长的颈扭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同时喷出一声优雅的响鼻。一瞬间,我认出她是谁了。她应该叫黑女,没错,粉白的腮部正中间那一块黑点,证明她确实是黑女。
我想起了她小时候的样子。三年前,我是个已经在村里做了八年农活的生产队社员。春天,去地里耕地,我赶的是一匹快生驴驹的草驴(我们那里把母驴叫草驴),每次套上牲口,饲养员老泉叔都会特别叮嘱:她怀着驹,该歇就歇一会,千万别使过力。一个月后,那匹草驴果然生了匹草驴驹。我眼看着驴驹从母驴的子宫里一点点钻出来,先是两条细腿,然后是湿漉漉的身体,最后是小小的头。刚落地就想站起来,跌倒了几次,最后终于颤颤巍巍两腿打颤站了起来,眼睛里充满着淘气顽皮,对这个世界好像一点也不陌生。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再赶那匹草驴耕地时,小驴驹已经能跟在她妈身边调皮,一出村,望见空旷的田野便撒欢地跑,一会儿便没了踪影,急得她妈来了驴脾气,怎么喊也不听使唤,梗着脖子往那边跑。老泉叔十分喜欢这匹小驴驹,常抚摸着她腮上的黑点,一声声地喊黑女。遇到这种时候,她小巧的蹄子轻轻地敲击着地面,温驯地用粉白的嘴蹭老泉叔,看上去像个温顺羞涩的小姑娘。
我在塞外古城上了三年学,最终只是由农民变成了个教师,相貌并没变,还是那样黑瘦丑陋。人讲究从小看到老,我从小就其貌不扬,估计到老也就这样了。她若是个人的话,应该属于那种天生丽质的美人,从小就是个美女坯子。让我惊奇的是才三年没见,她已俨然是个体态丰盈,风姿绰约的驴中佳丽了。
认出了她是谁,我很快明白她为什么来我家,也明白她此刻的身份,我相信她已经是我家的一员,便不再有生疏感,上前抚摸她光滑的皮毛,她很善解人意,眼里露出妩媚的光,用带黑点的粉腮轻轻地蹭我的肩膀,那黑点便如同美人痣一样在我眼前晃。可能被拴在这座寂静的四合院里的时间太长了,长时间没人搭理,她像迟暮的美人般有些寂寞,用玲珑的蹄子轻跺地面,一副烦躁不安的神态。我起了怜香惜玉之心,解下了缰绳,牵着她在我家的四合院里转,驴蹄敲打在院里的青砖上,吧嗒吧嗒响,在院里奏出一种怪异的声音。她驯良地跟在我身后,从前院走到后院,又从后院走到前院,蹄声轻盈而富有节奏,如同身后跟着位穿高跟鞋的美女一样清脆撩人。
我想起了在农村八年使用过的许多驴,叫(公)驴、阉驴、毛驴,当然还有草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谦逊。它们永远在用低垂的头颅和怯懦的眼神,向人类演示谦逊是怎样一种美德。其实人类倡导的许多美德,驴身上都自然存在,不过谦逊在它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罢了。这驴好像不是一匹普通的驴,谦逊的优点似乎并不突出,她身上最明显的应该是多情。我又想起了书里的驴,唐·吉诃德胯下的公驴,潘丘骑的毛驴,柳宗元笔下的黔驴。对了,俄罗斯的塞居尔伯爵夫人那匹会回忆的驴,应该与我这匹驴有相似之处,只是不知道她这会儿想起我是谁了吗?
二
十月天的午后,天气才带上一丝凉意,暮色沉沉,天快黑了。我把驴重新拴到上房门环上时,她不停地用嘴拱我的腰,好像在提示我什么。
妻子回来了,原来因为这匹驴她并没有去上班。结婚快两个月了,我还从没见过她这种样子,满头大汗,头发上、脸上都粘着草梗,一手提着一只蛇皮袋,里面分别装着青草和麦草,那是为驴准备晚餐。真是难为她了,一个新媳妇,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些东西。好在她是本村姑娘,弄这些东西应该不会受太多的难堪。不过,以往周末下午,她如果在家,这会儿早就给我准备好了饭菜,骑了40多里自行车,我确实饿了。今天她倒好,先给驴准备饭去了,把男人忘在一边。
妻子很兴奋,放下两袋草对我说:看见了吧,咱家的驴,拈的!
我不明白,问:“什么拈的?”
妻子说:“拈蛋啊,我妈拈的,村里一多半人都拈了空蛋,我妈拈了三个蛋,全是实的。”
妻子那会儿真是喜形于色。我觉得这实在不好,拈了三个实蛋就值得那么高兴吗?她不懂得谦逊的道理,更没有谦逊的美德。一个才20多岁、结婚还不到两个月的年轻媳妇,看到分别一周的丈夫没有任何表示,反倒为一匹驴高兴得忘形,出一头大汗,粘一身草梗,总让人感到不正常,一点也不可爱。
妻子继续为驴兴奋,那天她心里只有驴,驴就是她的全部,我的存在只是为她分享驴的快乐。我回来两个小时了,还没听见她问候一句,所有的话题都是家里的这匹驴。准确地说,那是她的驴,与我没多少关系,她只为她的驴忙碌,好像有了驴就有了一切,有没有男人都无所谓。
妻子从来没喂过牲口,还没有孩子,平常她喂的只有她自己,却对喂牲口十分在行。找来洗衣服的大铁盆,把两种草混放进去,再倒入一些麸皮,用棍子拌匀,放在驴面前。这可能是来我们家后的第一顿饭,那驴咕哧咕哧,吃得有滋有味。办完了这些事,妻子好像意犹未尽,仍没有想起给我准备饭,喂一喂丈夫饥肠辘辘的肚子,开始详细地讲村里这几天发生的事。
其实不用她讲,我也知道,经营了20多年的生产队解体了,地分了,农具分了,现在牲口也分了。以后,要各种各的地,再也没有人管你种什么,怎么种。更没人天天敲钟催你上工,开会,板着脸训你。
上个星期天我回来时,曾代替妻子参加过分农具。我虽然和妻子在这个村子生活的时间一样长,也曾在村子里劳动过8年,但我参加工作了,当了教师,就不再被视为村里人,去参加分农具
只是妻子的代表,没资格与大伙为一件农具争得面红耳赤。
说是分农具,其实是采用竞价拍卖的方式。一村人散乱地跟着队长,在农具库前的场子里转。走到一架耧前,队长用脚踢踢,大声喊:“50块,谁家要?”七叔喊:“我要!”那边五哥喊:“我要,60!”七叔瞪圆了眼,骂一声:“狗日的,跟我过不去,我今儿还非要这架耧170,我要了!”那边五哥伸伸舌头,一脸鬼笑,说:“算了,我不跟你争,让给你。”
村里大到马车、拖拉机,小到装粮食的口袋、木锨,都是这么分出去的。这次分牲口,队长觉得这办法不妥,牲口本身价格高,这么分无形中再次抬高了价,大伙会接受不了。最后商量的办法是先找几个人把牲口标好价,按户往下分。但是很快发现这样也不行,因为村里共有78户人家,只有36头牲口,计:骡子3匹,马1匹,驴6匹,牛26头。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家会分不到牲口。又在一起吵了几天,最后的解决的办法是:碰运气,抓阄,也就是妻子说的拈蛋。
抓阄是上午进行的。事先,在纸条上写好几号牲口,什么价格,与空白纸条混在一起,然后大伙按顺序去抓。那天,妻子去镇里上班,大舅哥已与岳母分开过,有事不在,内弟还太小,三家人全由岳母代劳了。老太太这辈子其实只交过一次好运。十三四岁死了父亲,跟着老妈从河南逃荒来到山西。在我们村巷里要饭时,从一间破庙里走出来一个少年,小姑娘眼前一亮,再也不去别的村子讨饭,让她妈找人说媒,非此人不嫁。不用问,这少年就是我后来的岳父。那时岳父正遭霉运,母亲刚去世,父亲是个柔弱的读书人,世道一变,做不了一点庄稼活,好大一份家业很快败光,家里几座院子全卖给别人,父子俩穷得一文不名,不得已住进村西头的破庙里。我到现在也没敢问老太太那时候看中了岳父什么。但从此岳母交了好运,岳父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一个工厂的厂长,岳母自然而然地成为厂长老婆,虽然还生活在村里,日子过得总是比村里人宽松些,时不时地带儿女去城里住几天,那种风光是村里人根本没有的。
带着这样的好运抓阄,老太太一抓一个准,件件不空。先为大舅哥抓了村里最好的一匹骡子,接着为内弟抓了一头犍牛,最后为女儿抓了一匹草驴。在村人的一次次的羡慕声中,老太太一次次地牵去了代表自己运气的牲口。最后,拍拍手,在大伙妒忌的目光中,乐不可支地离开了现场。
院里拴的那匹驴,就这么被老太太的好运带回了家。
妻子说完后,叹一口气,说:“可惜老泉叔,给生产队喂了二十多年牲口,这次也没抓着,老汉气得直骂手气背,连连朝手心吐唾沫。还有,队里的几个干部也都没拈上,平常他们在村里那么神气,这会儿运气偏不照顾他们,你说怪不怪!”
三
等到妻子准备好饭,吃完已是十点多钟。那边,驴还在大铁盆里拱,不急不慢地嚼,缰绳上的铁环不时哗哗响。妻子又开始为驴忙碌,饮水,添草,清理粪便。院里响起了蝈蝈叫声,夜已深。不知谁家的驴昂昂的一阵好叫,声音高亢悠长,在宁静的夜里十分嘹亮。这边我家的草驴听到了,竖起耳朵,激动得浑身战栗,跟着仰起了头颅,嘴唇翻起,露出白白的牙齿,昂的一声长鸣。她可能听到了同伙的呼唤,再也没有淑女般的平静。
妻子说:“是七叔家的驴叫,七叔今天拈了一匹叫(公)驴。”
给驴添了最后一遍草料,妻子总算睡下了。躺在我身边,心里想的还是驴,说:“早知道前几天就该把队里的那副铡墩买下,现在有牲口了,可没办法铡草。”
我说:“队里一共只有两副铡墩,谁想要就能要吗?”又忽然想起买铡墩的人,问:“我记得有一副铡墩是前巷的老于买去了,为这还和七叔憋了劲,不知这回拈上牲口了吗?”
妻子说:“没有,气得老于都蹦起来。”
我问妻子:“你真想养这匹驴吗?喂牲口很麻烦,你还要上班想喂也没时间。”
妻子说:“我也没想喂,只是高兴,高兴咱家能拈上牲口。”
我明白了,原来妻子只是为好运气兴奋,并不是因为驴的美貌,或者说美貌的驴,依她的耐心,过不了三天就会心烦的。
妻子又想起了什么,捅捅我说:“你得准备钱!这驴220块,队里规定一个月内交清。”
我开始为驴发愁了。我两个月前结婚时还在等待分配工作。母亲在我婚后第八天,就去了父亲工作的山东,那里还有五弟、六弟,家里本来就不宽裕,给我结婚后更加拮据,母亲走时只给我留下不到10块钱,作为我参加工作前的生活费。到现在我参加工作才一个月,还没领上工资,就算领上,月工资50多块,要四个月才能攒够驴钱。我生平第一次开始为钱发愁了,原因竟是为一匹驴。
那一夜,妻子摸黑爬起来为驴添了三次草。
第二天清晨,迷迷糊糊之中,我被妻子急促的叫声惊醒,睁开眼,妻子站在面前,泪水涟涟,说:驴没了。
我说:怎么会没了,不是拴在上房门环上吗?
妻子说:“我就出去到我妈家借了竹筛,准备给牲口筛草,回来后驴就没了,前巷后巷都找了,哪儿也没咱驴的影子。”
我想了想,说:别着急,丢不了,我知道她在哪儿。
想起昨晚七叔家的那一阵高亢的驴鸣声,我料定她一定是和那匹叫驴约会去了。走到七叔家门前,只见大门紧锁,七叔两口子都已经上地,我家那匹驴再多情也不可能来这里。情急之中,我又想起了一个地方,快步朝队里的饲养场跑去。生产队刚解体了没几天,饲养场已不是原来的样子,破败,荒凉,大车没有了,牲口没有了,只有牲口粪味还淡淡飘散,延续着二十多年的余韵。尽管没有牲口,饲养员老泉叔还住在饲养室里,昨天才把牲口分下去,还没来得及搬回去住。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闻了二十多年牲口味,也许一时舍不得离开。
走进饲养室,在幽暗的光线中,我看见了我家的那匹草驴,原来她跑到这里叙旧来了。此刻,正用粉白的嘴朝一个人身上蹭,那人抱着驴颈,抚摸着她粉白的腮,喃喃说:“黑女呀,昨晚上没吃好吧,再吃点,我知道你会回来,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家那匹多情的驴适时地喷了下响鼻。我想,要是人,她已经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忽然,她又“哦”地一叫,那声音凄凉悲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她大概是哭了吧。以前,我听过女人的哭声,每次听到都会跟着哀伤一阵,母驴的哭是第一次听到,竟也如此让人受不了。这多愁善感的驴呀!
那人是老泉叔,养了一辈子牲口,他可能和牲口已处下了感情,尤其是像我家这匹如此风姿绰约又有情有义的驴,怎能让老泉叔割舍得下。我没打扰他们,悄悄离开了饲养室。
见我空手回来,妻子问:“驴呢?还没找见?”
我说:“别着急,一会儿就会回来。”
果然,不大一会儿,老泉叔牵着我们家那匹驴出现在巷口。那驴可能已经恢复了平静,还是那么神态优雅,迈着长腿,节奏感极强地跟在老泉叔身后,背上一边一个驮着两个袋子。等走近了,老泉叔说:“这驴调皮,可讲情义,你看才一天没见,就又跑到饲养室,她爱吃苜蓿,我专门给她
藏了两袋,给你们带来,仔细喂,以后可就没了。”
妻子接过缰绳,老泉叔又说:“夜里勤给她添草,驴和人一样知道饥饱,别委屈了她。”
老泉叔60多岁,一脸白花花的大胡子,看上去粗犷雄毅,说着说着,声音哽咽,眼看连眼泪都快流下,急忙扭过头摇摇手,又朝饲养室那边走去。
妻子说,昨晚她带回来的那两袋草,也是老泉叔给准备的。
那天下午,我又回县城上班了。临走前那驴还拴在上房门环上想事情,垂着头,摇晃着耳朵,看不出一点表情。我顾不上她了,也暂时顾不上妻子,以后的一周,就只有她们姐儿俩生活在这寂静的四合院里。
四
在学校一周,闲暇时,除了想老婆,我想的最多的还是那匹驴,她能不能适应四合院里的生活,能不能与老婆和睦相处,还有,老婆有没有时间给她找草料,晚上能不能按时喂她。我知道,四条腿的动物有时候要比两条腿的人难伺候得多。
到了星期六下午,一路上想的还是驴,回到家,院子里空空荡荡,妻子上班还没回来,那匹风姿绰约的草驴也没了踪影,让我与上次看见她出现在院子里时一样吃惊。已是深秋季节,地里没活,不可能是谁家借她去耕地。我们这里是平展展的土地,出门都骑自行车,不可能有谁家媳妇骑她去回娘家。门锁得严严实实,她也不可能像上次那样自作主张,跑回故居怀旧。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草料,连那个大铁盆里,也泡着没来得及洗的衣服,除了上房门前她留下的骚味,满院里找不到她的一点痕迹。她去了哪儿?
妻子回来了,满脸愁容,我问:咱的驴哪去了?
妻子说:“别提那驴了,都快不是咱家的了。村里有几个人咬得厉害,队里要收回去。”
我问:“为什么,驴不是你妈拈的吗,怎么能收回去?”
妻子突然拉下脸来,问我:“我的户口你到底办了没有?”
一说起户口,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妻子娘家就是本村的,本来根本不存在办不办户口的事,问题出在拈蛋分牲口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如果妻子户口还在娘家,尽管她是韩家唯一顶门立户的媳妇,却意味仍然是她娘家人,她这一户就不存在,根本没有资格去拈蛋,那匹草驴也就不应该属于我们家。妻子说:“那些人的意见是把咱家这驴收回去,让没有分到牲口的人家再拈一回蛋。”
仔细想想,这些人还真会“咬”,是往根儿上咬。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你没有资格,运气再好也没用。那会儿,我有些同情这些乡亲了,为了一匹驴至于吗,尽管这驴确实长得风姿绰约风情万种,但那毕竟只是一匹驴。又想这些人的心理,就明白了这些乡亲们为什么要咬,村里有多少人家需要牲口,你一个男人不在家的老太太凭什么一下就拈去了三头牲口。尤其是你闺女,全家只有两口人,男人在县城里教书,女人在镇里上班,要一匹驴做什么,而且还是那么好的一匹驴,放在她家不是可惜了吗?
见我不说话,妻子着急了,问:“你到底办了没有?”
我说:“你别管,想咬让他咬,咬得越厉害,蹦得越高越好。”
我带着点气了。我们家在村里是老户,在这个村子里已不知生活了多少辈子,三年前还是村里人口最多的家庭,劳力也不少,没有少为那个解体了的生产队出力,我和四弟、二嫂都曾经在村里干过多年活。后来,我和四弟分别考上大学;父亲单位落实政策,把母亲和五弟、六弟户口迁到了山东;二哥把二嫂和侄儿侄女迁到了省城。才一年多时间,一个大家庭就从村里全部搬走,家里前后两进四合院,20多间房子空荡荡。我在上学前三年就订了婚,毕业后,还没参加工作,母亲就急于让我结婚,老人家的想法是反正你媳妇是农村户口,娘家也在本村,娶过来,咱那个大家里就会有人守着,不至于荒了。没想到,我们一家人才离开不到三年,就不被视为村里人了,而且要把已经牵到家的驴再牵回去,有点欺侮人的味了。
当然,如果妻子的户口没单列,人家有意见我也没办法。
我成竹在胸,不去想户口的事,现在最关心的是那匹驴到底去了哪儿,是又跑到饲养室与老泉叔叙旧,还是已经被收回去。
这回提到驴,妻子脸上又有了喜色。
原来,我走后,那驴三天之内又去了老泉叔那里三次,她好像认准了那里才是她的家,老泉叔才是她的亲人,把驴的执着发挥到了极致,妻子已被这驴的拗劲弄得心力交瘁。老泉是妻子的本家叔,我离开家的第四天,老泉叔来找妻子,说是他反正还在队里的槽头住,那里什么东西都不缺,不如把黑女先寄养在那里。这么好的事,妻子怎么能不同意。其实我一走,她就开始为这匹驴发愁,她要上班,根本没时间喂牲口,就是想喂,草料从哪里来?铡刀、槽头还要再花一笔钱。老泉叔好像巴不得替我们义务养这匹驴。他太喜欢这匹驴了,只要能让他天天和黑女在一起,做什么他都愿意。
晚上,我去饲养室里看黑女。槽头里拴的牲口不止黑女一个。分到牲口的人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见老泉叔反正养着黑女,纷纷把牲口牵来,交给老泉叔代养。饲养室里又恢复了生产队时的气象,槽头拴满了牲口。黑女的右边,拴的是一匹灰色的阉驴,这匹驴我在生产队时多次使唤过,性子缓,听话,与其它驴在一起时就像位长者一样,从不争草料,看来老泉叔把它和黑女拴在一起确实用心良苦。七叔的那匹叫驴,被老泉叔拴在墙脚,中间隔着几头牛,可能是怕这个骚劲十足的家伙欺侮了黑女。
与同类在一起,黑女更显得风姿绰约,油黑光滑的皮毛,妩媚明亮的眼睛,都向人证明她是一匹优秀的驴。她好像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看见我,耷下了眼皮,神情冷漠,仿佛怕我再把它牵到那个寂静可怕的四合院。
饲养室里弥漫着浓郁的牲口粪便味,晦暗的灯光下,一排牲口在黑暗中眼睛闪着亮光,咕咕嚼草。牲口槽对面,用土坯砌成个阁状小屋,里面是饲养员睡觉的土炕。老泉叔正端着烟锅坐在炕沿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半天不说一句话。
我说:“我不想要这驴了!”
老泉叔眼睛一亮,立刻又低下头,说:“为什么,这么好的驴,多少人都眼红呢!”
我说:“我在县里上班,一个女人家忙不过来。”
老泉叔说:“是呀!再说你家就你媳妇一口人,只分了二亩地,也漂不住个驴。还有,从现在起,到明年春天地里的活开了,才能用得上牲口,这几个月牲口实际就在歇着,光吃草料不干活,还得人专门招呼。”
老泉叔说得对。那几天,村里已经有好几户把刚得来的牲口卖了,原因就是老泉叔说的要闲好几个月。
我忽然有了一种想法,对老泉叔说:“我想把黑女卖了,我不懂牲口,想请你明天去牲口市帮我卖。”
我的话好像出乎老泉叔意料,他一愣,脸上有了复杂的神情,吐出一口烟,说:“行!”
五
我们村紧贴着小镇的东城墙,牲口市就在村头的一条大路边。我和老泉叔把驴牵去时,那里已经有许多头牲口,挤满了买卖牲口的庄稼人。黑女一到,几个人立即凑上来,翻嘴唇,扳耳朵。老泉叔有些气,大声说:这驴还值得这么看,你看这毛色,看这身子,就知道是匹好驴!
一位紫脸膛的老汉说:我知道是好驴,你给个实价。说着把手伸向老泉叔。两人的手捏在一起,又藏到衣襟下,显得极神秘,两个人都望着对方的脸,表情随着藏在衣襟下的手不断变化。那老汉每捏一下都好像费了很大劲,老泉叔脸上更多是轻蔑的笑,不断摇头,说不行不行,你再看看这驴,我在队里当了二十多年饲养员,这驴是我从小喂大的,知道斤两,这数不行。
紫脸膛老汉说:“再好,不就是个驴吗,总不能卖个骡子价。”
老泉叔说:“谁说驴就不能卖骡子价,你看清楚,这可是匹草驴,才三岁口,正能生哩!明年身边说不定就跟着骡驹子。”
紫脸膛老汉说:“那也不值这价。”
两个人的手一直在衣袖下捏。我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们到底捏出了个什么价。按照我的想法,只要不低于从生产队买的价就行。
两个人终于从衣袖下把手撤出来,紫脸膛老汉悻悻离去。老泉叔抚摸着黑女,大声说:“给那个价,怎么能卖了这么好的驴。”
我问:“他给什么价?”
老泉叔说:“240。”
我说:“那怎么不卖了,赚20块呢!”
老泉叔说:“你不懂,队里作的价本身低,这个数卖就亏了。”
一个上午,不停地有人和老泉叔在衣襟下捏手,不停地有人抚摸着黑女的皮毛赞叹,在老泉叔轻蔑的笑声中,最后都带着失望悻悻走了。深秋的阳光照得人暖烘烘,黑女皮毛发亮,依然风姿绰约,亭亭玉立在牲口市上。在老泉叔与买主频频捏手时,她一直垂着头好像在思考什么,神情冷漠,精神委顿,买主一走,立刻又恢复了风采。这是一匹有感情有思想的驴啊!
我不能再陪老泉叔卖驴了。下午有自习,我必须在四点钟前赶到学校,离开前,对老泉叔交代:“看着差不多就行了,别掰得那么硬。”
老泉叔嘿嘿笑,说:“你放心,我知道行情。”
六
一周后,我再回到家,妻子一见面就急了,说:你到底把户口办了没有,那些人听说你卖驴,咬得更厉害了。
我说:“是吗,那就让他们再咬咬。”
其实早在妻子过门后的第五天,我就办好了户口,村里的户口由大队会计管,因为大队会计与我们不在一个村,村里人并不清楚妻子的户口到底转了没有,所以才一直有意见,见妻子拿不出转户证据,吵得更厉害了,有人甚至已经向老泉叔打听我家那匹驴的价钱。我感到再不弄明白妻子会和我发急。第二天上午,找到大队会计,开了证明,同时把东拼西凑借来的220块钱一起交给队长。队长呵呵笑,说:我早到大队会计那里问了,给他们说,就是不信。
老泉叔还是没能把黑女卖掉。小镇上农历三、六、九逢集,这一周,老泉叔又把黑女牵到集市上两次,又牵回来两次。每次回来都给妻子说:“人家还给那个价,咱不能卖,再试试。”
我再没心思想风姿绰约的黑女了,她毕竟是匹驴。
一个月过去了,每逢集日,老泉叔便会早早把黑女牵到牲口市,一呆就是一天。我感到他好像在利用热闹的集市,展示着黑女的风姿,享受人们对黑女的夸赞,并不急于把黑女卖出去。老汉太喜欢这匹驴了。那是他从小养大的黑女,在他眼里大概如同女儿一样可亲可爱。我想,反正这些天黑女也一直由他养着,饲养室有队里剩下的草,妻子只需准备些麸皮,就让他和他心爱的驴多呆些时间吧。
已经到冬天了,刚下过雪,老泉叔披着一身雪花来到我家,把一双粗糙的手伸在火炉上搓了又搓,神情尴尬,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问他有什么事。
老泉叔有些难为情,说:“你看,我都把黑女牵到牲口上有一个多月了,人家给的价最高是270,你看这价行不行。”
我说:“怎么不行,让你受这么多累,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其实早就该把她卖了。”
老泉叔说:“我舍不得呀,要不这么着,干脆就那个价给我留下,这是270块钱,你收下。”
老泉叔掏出一沓钞票,放在桌上,我说:“我只要220,与队里给的价一样就行,你养了黑女这么长时间,多余的应该归你。”
老泉叔狡黠一笑,说:“你能让我留下,我就心满意足了,270块,是我沾了你便宜,你还是收起来。”说完,起身走出去。
雪已经停了,我突然想再去看看那匹美丽的驴,她毕竟在我家生活过几天,同时把那多出的50块钱还给老泉叔。巷里铺着厚厚的雪,上面踩出几个零乱的脚印。我向饲养室方向走去,远远的,看见老泉叔正牵着黑女朝村外的雪野里走去。太阳出来了,把雪地照得发亮,我看见那匹美丽的驴正在用粉白的腮朝老泉叔身上拱,老泉叔回过身,又在抚摸他的黑女,一脸慈祥的笑,就像望着自己的女儿。那一刻,我明白自己犯了个错误,从一开始,老泉叔就想把黑女给自己留下,他那么喜欢这匹驴,这一个多月其实一直故意拖着不想把驴卖出去。我为什么就没看出来呢?
责任编辑:鲁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