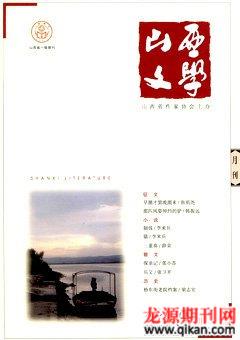真想再和您聊聊天
钟小骏
嘿!
老头!
能跟您聊聊天不?
算起来已经有日子您不跟我说话了。即使以前我在外面上学的时候,您也基本上一个月会给我打一个电话的。虽然每次都要四十多分钟一个小时,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基本上脸已经熟了,而且还会有明显的左右耳听力不一的状况。但是看到同学们惊讶而羡慕的目光我还是很得意的——谁家国际长途能牛成这样,简直跟不要钱似的。当然了我回国后知道您竟然真的是用家里的电话,也就是说每一分钟通话时间都直接对应五块钱的时候我也很生气。不过话说回来,我知道这一点之后反而觉得更牛了。
但是,既然说起来上学打电话的事情,我就又忍不住要批评您了,怎么能又这样呢?嗯?我刚出国上学的时候,第一天,不,第一个星期,甚至第一个月,学校的电话边上就没断过人,同志们都能接到家里来的电话,嘘寒问暖,殷勤备至,到第二个月头上的时候全新生中只有我没有接到家里的电话。我记得我还跟您说过,那个时候要是听到有人喊名字说是来电话了,我边上的同学全都自动地把目光从我身上移走,生怕看到我又愤怒又羞愧又悲伤的眼神,不客气地说,那个时候我要是照照镜子,把我的表情眼神都记下来练会了,那现在什么“影帝”、“影神”的表演可就都不在话下了。呵呵,就像您每回得意之时哼两句歌之后都会说“我要是不抽烟,那就是一个不错的男中音”一样,以后我有了儿子,我也能在他面前吹两句了。
但是没有,您当时没有不抽烟,我当时没有照镜子,我没有再出国,您也不会在我愤怒的要求中开始给我打让我觉得自己很牛的电话。
甚至没有梦到您!
我还专门查了做梦的资料。第一种说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觉得这一条不符合我的情况,起码并不是完全符合。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确实没有“日思”,不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无思”,傻不啦叽的跟块木头似的,自然没有“夜梦”了。现在想起来我对头十天唯一有印象的就是送您的那天,好多人啊,真烦。以前要是有这种场面,我早就打个招呼之后就溜了,可是那天溜不了,我还抱着您上了三楼的新家。实际上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在上楼的时候我的心疼得厉害,像是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从里面要钻出来似的,我努力地把那种感觉记了下来,想试试体会一下您在走的时候的感觉。但是我估计我的尝试不成功,因为那实在是太疼了,要是您当时是这种感觉的话,一定不会面无表情的。他们说,我见到您的时候您的表情就和刚发现您的时候一样,如果您不同意我使用“安详”这样有点拍马屁意味的词语的话,起码可以肯定的说那一定不是“痛苦”。所以很多人都说您的运气好,一下子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痛苦。我就“啊,啊,对,是的”点头表示同意,实际上我真想说的是“放屁”,您五十六岁就走了,凭什么说这叫有福气!
对不起,老头,我有点激动了,说粗话了,您别见怪啊!咱们说回到做梦的问题上。我虽然前几天根本就没法有思想,可我后来有思想的时候,或者说能思考的时候想的可全都是您啊,头十天加起来睡了十七个小时,或许可以说没工夫做梦,可后来我疯狂地想您,还是不做梦,这就不对了吧?所以说,这个理论是一个破理论,它只能被动的解释,而不能主动的导致。也就是说,只有在做梦之后根据梦的内容回溯日间的想法,解释为什么会做这个梦。逆推则不成立。不能说日间的思念一定就会导致晚上的梦境内容。“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苏轼这个王八蛋,运气真好。嗯!不好意思老头,骂人了。可是他凭什么能够梦到想梦到的人?我嫉妒!
第二种关于梦的解释,怎么说呢,解释方面比较清晰,比较合理,比较严密,比较有逻辑性,但操作性方面差得太远。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来自弗洛伊德这个把一切行为都和“性”挂钩的奥地利老头,所以关键词是“欲望”,我仔细地研究(呵呵,就是找来资料看一下,没能力真的去研究)了一下,他一旦碰到难以解释的问题的时候就会使用“潜意识”这个词。这就麻烦了,“潜意识”之所以为“潜”意识,就是对应“意识”这个可以操控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不可控。这个构成描述物基本特性的元素就限定了我的努力,也就是说我再怎么努力、尽力、全力地想您都没用,我还必须得在潜意识里也想您才管用,才有可能梦到您。可我再怎么想也不是潜意识里想,可怕的是我这样想还影响不了潜意识,让潜意识也想。我都快绝望了,根据这个理论,难道我在潜意识里竟然不想您么?这也——然后才忽然意识到这个外国老头成名作竟然叫做《梦的解析》,原来他也是一样,只是在梦的解释方面下功夫,根本也不能主动地控制梦的内容。您猜到了吧?呵呵,我说这也是一个破理论。
于是,我现在可以严肃地对您说,我是一个卑鄙的实用主义者。甭管这理论,那解释,如果不能让我梦到您,就都一边待着玩去。
梦不到您,很痛苦。但是有时候又觉得也还好。别误会,请相信我一定是真心地想见您的。只是,每当想到要是见了您,我说些什么呢?万一,您对我做的事情不满意,我就又会看到您黑着脸的表情了。上帝作证,我高二那年竟然误掉了期中考试的时候,您的脸色已经在我之前岁月中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在梦中出现的次数仅次于我在高考数学的时候发现没带圆规。
所以呢,我就狡猾一些,提前设想一下您会说些什么。
可我想了半天,怎么也想不出您会怎么说。就好像即使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国,第一次利用假期回来的时候,您在首都机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眼神,挥手半天还看不见”,您知道当时我本来准备挥泪之后接猛扑入怀这个动作的。或者像是上初中的时候,您一出差回来,我准定跑出去迎接,但您第一句话一定是把手中的大雀巢咖啡瓶子版茶杯往前一递,“去,把茶倒了,重泡。”要不然就是像那回您出差,老妈抓住机会要给我减肥,连着吃了一个星期的稀饭,我抓住机会利用给您接风的名义大吃一顿,您好像是等我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才说的第一句话“结账”。
但最有可能的,或许就是您什么也不说,就是笑吧。
关于您的笑,老妈和我前两天还专门讨论了一下,我说您的笑基本上都是以坏笑为主,她不同意,说是聪明为主,坏为辅。鉴于她身为女人和您妻子这双重不理性的身份,我就不说她了——肯定不客观。
我前年经历了差点在打篮球的时候被闪电劈着,上厕所的时候里面的门把手断掉,首都机场只不过小了一个便就被人把行李箱偷走,明明堂哥洗澡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我一进去淋浴莲蓬头就四分五裂还崩得很远等等这些在我看来很不幸,您却总是听得哈哈笑的事件之后,您给我起了一个血统高贵的名字“黑背”。并且还算出像我这样的环境保护主义狂热分子,深刻认识到水资源重要性因而不愿意在任何途径浪费(实际上就是不喜欢洗澡)之人的洗澡时间,专门在浴室的大镜子上贴一张纸条,上书“黑背,洗澡的时候务必拔掉电热水器的电源,以免本不可能发生的漏电情况”。那个时候您脸上的,一定是坏笑。不
过,我估计我见到您的时候您脸上的应该不是这种。
傻大个这样的一个省局级干部在复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句话时经常会在第二个先生处打磕巴,“先生之什么来着”,您学他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的那种笑,也是坏笑,傻大个叔叔在旁边听着也只有“你这人,怎么这样”的一笑,然后两个貌似老混混之人就会一碰杯。您见到我之时露出的笑容应该也不是这种。
光来叔叔爱饮而总醉,您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也总带着坏笑,比如卡拉OK之时歌声忽起,众人遍寻不获,惊回首,那人却在柱子后悄悄地唱;又比如酒至半酣,忽然陌生人进屋,“这屋里是不是少了一个客人?”大家急忙清点,果然,光来叔叔隐匿无踪,桌上桌下,两处茫茫皆不见。来人就说:“去我们那里看看是不是。谁也不认识他,进来就坐下,还怪我们怎么上趟厕所的工夫就把菜重上了,使劲和我们干杯,不喝不行,急了骂人,赶也赶不走。”实际上来人就在隔壁,几步路的工夫能说这么多话,看来也是委屈得紧了。您见我的时候脸上会是带着这种笑么,我想也不会。
那应该是这种,在我宣扬自己在国外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而沙拉做得深得老毛子之三味之时,取出一瓶葡萄酒,爷俩二人对坐小酌,说出“父子多年成兄弟”时脸上带着的那种笑;是我写出一集剧本,第二天导演打电话盛赞之后您对我讲述时的那种笑;是我拿回毕业证时您脸上的那种笑,那种看着自家院子里菜终于绿了的笑!
其实,是我想看到您对我这样的笑。我让您这样笑出来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您先对我笑,那这事就好办多了,我就怕您板脸训我说:“说话啰里啰嗦,逻辑不清,主次不明,毫无重点。”不过,今天是咱俩聊天嘛!谁规定聊天的时候还要围绕中心,言简意赅的?咱又不是谈干部问题。
我最近在学您呢!还记得有一回咱俩聊天,您说:“你看我看的都是什么法制频道,探索频道,百家讲坛,天元围棋,可你呢,就看什么体育频道,音乐,电影频道之类,唯一说得上还能提高点素质的就是世界地理了,你还不怎么爱看。”可我现在真的发现您说的那几个频道有意思了,除了围棋,那东西我跟您学了三年都没学会,也就不费那功夫了。倒是葵爷假模假式的每次来家都要转到这个台,可看不了五分钟准睡着,为这个不知道被老姐说了多少次了。
说起老姐,最近脾气好了很多啊!看起来当初老姐带着葵爷来家的时候您所说的准备“嫁祸于人”的愿望没有实现,老姐“嫁于人”,可不为“祸”了。有时候我在想,您要是在,看着老姐现如今的表现,是不是会故意给他们捣捣乱什么的,要不然简直不是记忆中老姐的风范了。
倒是他们家的狗,除了您总是带着到处跑,四处给人家瞎改名的大狗“泡泡”之外,又养了一条萨摩犬,名字叫“米莱”。白色的,我开始看着挺漂亮,心想如果要是叫“雪莱”多好啊,听着就显得那么有文化,可是在家里只待了一天我就明白了,这家伙智力低下,举止轻浮,除了随地小便之外,还疯狂掉毛,要不用食物引诱它就不明白你在叫它,所以我估计最原始的名字实际上应该叫“米来”才对。泡泡前年被剪掉的毛慢慢地长出来了,终于不再像拉布拉多而变成了真正的金毛。但是不怎么敢让它回来,因为它每次看到林叔叔的车总是会扑上去,又跳又叫的。林叔叔说那是因为以前您总坐他的车,泡泡以前就是这么表现的。老姐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哭,会拉着泡泡告诉它说“姥爷不在了”。我原本不相信泡泡能记住车,可是一次那个一喝多就喊着“谁对你不满意就派一个机枪排突突了他”的王叔来的时候,泡泡也表现得很兴奋,我这才明白这个狗东西真的能够把和您有关的人事物都和您联系起来。
对了,小熊,大款叔叔的女儿,您走之前不是正在看她的文字,以便给她出的散文集写一个序吗?那本书出来了,做得挺不错。我当时本来想如果可以我来给写序的,呵呵,还好大家的理智都还健全,没同意我这个要求。因此一气之下我给一位同学的爷爷写了一个墓志铭,那玩意儿可真难写!
还有谁呢,您猜。嗯,是海林叔叔和晓媛阿姨的闺女睿子也结婚了。实际上我特烦这个“也”字,为什么也结婚了,她可比我还小哪!所以婚礼我就没去,其实是害怕到时候一堆叔叔伯伯、大爷大妈都过来问我结没结婚,有没有女朋友,需不需要介绍等等。您也知道,作为一个大龄未婚男青年如果不是豁出去了完全不怕这个问题,那就一定是特别怕这个问题。
说了这么半天,听不到您的批评,听不到您的建议,听不到您的点评,也听不到您的赞扬,于是就变得挺无聊的。再跟您说个事就不说了。
前几个月咱们院里的李叔的老爷子也不在了(这个该死的“也”字),当时去了不少人。那个时候您刚走不久,我完全没心情去注意来的人,就一个人蹲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发呆。当时人来人往的,我身边蹲着一只小吧儿狗,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被这么多人吓到了,睁着圆圆的湿乎乎的眼睛怯怯地看着地面,身子趴得低低的。我一下就感觉,是不是这个小东西往常都和老爷子在一起,如今老爷子一走,它找不到依靠了。没人再给它挡风,没人再给它遮雨,没有人再在晚上摸着它的脑袋跟它说话,没有人再会那么全心全意地注意它,关心它是不是吃了,是不是病了?
《说文》里面解释,祭,祀也。实际上就是供奉神灵或祖先,对死者表示追念的仪式。麻烦的是作为动词讲的时候用的是象形义,甲骨文中“祭”是有酒肉的祭祀。不过,董桥写过一本书叫做《文字是肉作的》,所以一篇文章加一颗心便也应该够得上“祭”了。
嘿!
老头!
真想再和您聊聊天!
责任编辑:孔令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