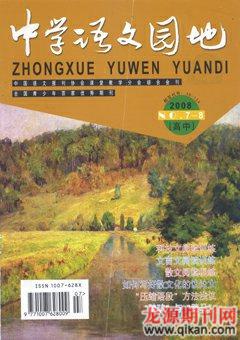凤凰随笔
王译唯
一个好事的人,若从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寻找,一定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竿”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有一个小小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了数千户人家。不过,一切城市,大部分皆因交通、物产、经济的情形,而生成、发展与荣枯。而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
——题记
车子经过近9小时的颠簸,终于进入湘西境内。
一、湘西的山水
车在山路上盘旋,撩起窗帘,就能看见车窗外的山和山脚下的河。湘西的山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山因水生,水因山活。河水缠缠绵绵的极像湘西女子。这里山型柔和,如同抛物线一般,起起落落也不会让人觉得突兀。水的幽怨冲击着山的温暖,含威不露的山围绕着清凌凌的水。这让你觉得山本该如此,水本该如此,这样的水本该生出这样的山,这样的山本该被这样的水依偎。
二、凤凰——沱江
刚一下车,就有不少人围上来问我是否要住宿,我坚持要住江边,选了一家靠近沱江的客栈。穿过一条小巷,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往下走,石阶平铺得不很规则,光滑的阶面上泛着微微的青色,看上去颇有些年头了,大概走了二三分钟的样子,就看见沱江了。
沱江并不是很宽,但足够长。绿玉一样清亮的江水潺潺而下,溯流分三个阶段,跳岩向上为上游,从跳岩向下至沙湾为中游,这也是沱江最繁华的地段。阶段处的江水“哗哗”而下,几十个古朴的石墩裸露在河面,连接沱江两岸。江中还有用四五根木头捆扎成的小木桥,踩在上面颤颤咿咿,桥下有不少人在洗衣服、被面,女人们卷起裤管的双脚浸在没膝的江水中,举着木棒把衣服、被面捶得啪啪响。
江中有许多木船,船夫撑着长长的竹竿,摇摇荡荡漂进远古的荒蛮,漂进这细雨如丝的古城,飘进凤凰人世世代代迷离的梦乡。倘若兴情所至,船夫便会扯着嗓子吆喝几声,唱上一支山歌,洞穿天地,洞穿苗、土女子幽幽怨怨的情愫,洞穿凤凰城所有的喜、怒、哀、乐。
江边是凤凰独具特色的吊角楼,翘壁飞檐,白墙青瓦,经过无数次细雨的冲刷,除去浮华与污尘,雕刻在吊角楼上的是永远也抹不去的风情画韵。
三、南方长城
去天龙峡的时候,车顺便在南方长城停了一会儿。这样的一次停车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我对天龙峡没多大的印象,而对南方长城的记忆却颇为深刻。
自明、清以来,凤凰就一直是苗汉兵家必争之地,而南方长城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采取镇压的产物。长城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王朝统治者规定“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
驻足在南方长城脚下,想象着二百年前的烽烟四起,想象着二百年前的腥风血雨,想象着二百年前尸横遍地的疆场,想象着二百年前英雄如注的热血,如惊雷一般的呐喊,想象着二百年前朔风中军旗猎猎,森森号角,横卧在山顶的苗王大刀,映照着英雄圆睁的怒目与不屈的魂灵。那些历经百年风雨剥蚀的深邃岩缝记录着战争的无情与岁月的沧桑,那一段被血与火、生与死填满的历史,在一声声叹息中随着一阵又一阵的烟尘,散了,散了。
古城依然,王府依然,两个王朝却没落、消亡了。风沙不在,但一次次对命运的抗争,边城人铁骨铮铮,浸染风霜的勇气不改。
历史不属于英雄,在被岁月风干的青史里,找不到纯粹的英雄,英雄活在民族的精神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大大小小各具魅力的“精神英雄”,一个民族才能强大起来。
后记
去凤凰的第三天,去了沈从文先生的墓地,我在先生的墓前深深地鞠躬。在文坛已故的先辈中,我最尊重的便是先生。正如先生的姨妹张充和女士的撰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撰联概括了先生一生的高风亮节。坐在车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凤凰造就了先生还是先生点亮了凤凰?先生用属于他的如冰峰一样坚毅的笔把故乡把爱与恨装进了他的作品里,但可惜的是现实的凤凰却随着旅游业的扩展一点点一点点与先生作品里的湘西背离了。
(指导教师:杨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