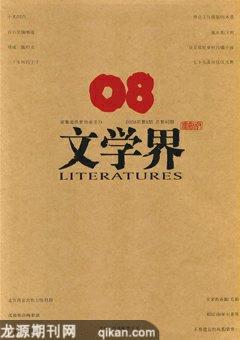逝去的它们
范精华
一、村里的牛
牛,这个从久远岁月里跟随我们祖先一同走过来的神祗般的动物,既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又与人类有了生死之交。无论是它提供的动力还是奶水抑或以身体作的祭品般的最后奉献,都是养育人类的间接或直接的方式。
我的故乡在洞庭湖畔,那里只养耕牛。耕牛,总是要奉献力量的,这是它们的天职。如果说历史是一架老犁,很长的岁月就是耕牛拉过来的。当城镇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而来,当土地上爬满了蜻蜓般现代化的农具,耕牛,这个牛的族类中最勤勉的一员,却在悄悄淡出人们的视线,就象一个情同手足的兄弟,正在离我们而去,蹒跚的背影,且行且远。
1
假如你能想像我的父老乡亲是如何在田里劳作的,那你也就能想像村里的四头水牛是怎样劳作的。村里的四头牛,担负着近两百亩水田的耕作。
过完大年不久,春寒料峭之际,耕牛率先走向田野,就是春耕。
洞庭湖滨的春天是美丽的,它的美丽在于它鲜艳的色彩。大地的主要色调有两种:翠绿和金黄。紫云英摇曳着绿浪,一望无际直铺到天际,是望不到边的。油菜花金灿灿,成几何图形镶嵌在绿毯之中,一片片的亮丽,一片片的辉煌。生产队的耕牛就忙乎在这金黄和翠绿之间,它们看上去只是一个移动的小黑点,犹如在花丛间缓缓移动的蜜蜂。
被泥土磨得雪亮的犁铧插进田里,犁把式一声吆喝,那犁铧就翻开黝黑的泥土,连同翠绿的紫云英一起翻耕到地下,此时的牛就摔着尾巴边走边啃着田里的紫云英,真正的工间餐。犁开的土坯是成行的,一行接一行,颇有点像竖写的诗行,整体上是直的,但也不乏一些曲与折的小小的变化。耕牛天生就有这种本领,再大的一丘田,它也能将犁坯拉直。
这时候的劳作是以牛为主体的,先犁田、后耙田,再用蒲滚来滚平,都必须牛来做,人没有这么大力气,说这时的牛,干的是最重最累最脏的活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春耕春插是多么富有诗意啊,空气湿润着,散发着混合着各种气味的花香,燕子、云雀飞来了凑着热闹,在空中呢喃、歌唱。男女老少似乎都在吆喝,都在奔忙,脸上都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插秧是妇女和少男少女的事,他们心灵手巧,相对的不太腰痛。开插这天是全村的一件大喜事,是要放鞭炮庆祝的,称之为“开秧田门”,大意是祈求一年的好收成。春耕春插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边耕边插。此时的耕牛,似乎明白自已劳动的重要性,只是一味的鞠躬尽瘁,用自已无声的劳动打造出一个璀灿的春天。
我与耕牛的第一次的“神交”, 就是在一个忙碌的春插的日子里。其时母亲背着半岁的我去插秧,背个孩子插秧总是不方便的,于是母亲就将我放在窄窄的田埂上。队里的三爹是个不太能管事的人,赶着大水牯——牛在前他在后慢悠悠地从田埂上走过,那牛走到了我身边他还懵懂不知!许多插田的人看到了惊得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人们瞪大了眼睛,就看着牛的四只脚如何决定我的生死了。此时是万万不可声张的,以免牛受惊对我更危险,无声的紧张真要让人背过气去!结果出人意料,大水牯用它的大鼻子居然在我的脸上嗅了嗅,蹭了蹭,四只脚从从容容从我的身上跨了过去。过去后,还抬起头朝田里插秧的人望了望,好像在说,这种事也要你们担心?
这以后,大家都说,这大水牯通人性,了不得。
2
当晚稻插完了以后,牛就完成了庄严的使命,就得闲了。由谁来看养它们呢,这是生产队的大事。
洞庭湖区的秋天明朗而又寥廓。此时牛儿们被放到了湘江河中的一个洲上。这个洲叫萝卜洲,兴许形状似萝卜吧。萝卜洲在洪汛期只剩下了一点点,即最高的那一点,在滔滔洪水中变成了一座孤岛。土坯建的一间房子就伫立在这岛的尖顶上,看上去既危险,又可笑,可就是坚持不倒。不过在这岛的周围,是栽种了很多的柳树的,那柳树在洪水中就只剩下树冠了。可是大水一退,这洲倏地就变大了,洲上的爬根草,没日没夜的疯长,没几天,那洲就变绿了,显出勃勃的生机。这时,各村的牛就来了。洲的四面环水,牛儿们要去洲上时,还得用渡船送他们去呢。所以,它们是没有地方可以溜走的。它们很悠闲地啃着肥嫩的青草,快乐地甩动着尾巴。没有人管它们,它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只有在这时,它们才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已的天地。这段日子,是耕牛们最惬意的日子,仿佛生活在世外桃园。他们甚至有时间谈情说爱了,追逐、嬉闹,斗架,那是多么浪漫而洒脱的时光啊!
寒冷的冬天来了,洲上的草也差不多吃光了,没有吃光的也枯死了。牛儿们又回到了生产队,这时,是人们服侍它们的时候了。
冬天的牛栏是有些特别的,虽然也是茅草盖的,但它相对矮些,为的是空间相对集中,暖和些;自土墙以上,又架上了隔层,用几层草席铺就,所以,牛栏里是不太透风的;加上里面还要烧一盆炭火,人一走进去,就会感到热乎乎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混合着牛粪臭的暖烘烘的气味。牛儿们就在这里享受它们的冬天。它们吃的是煮熟了的稻谷拌上切得只有一两寸长的稻草秆,是所谓的精料,它们豁大的嘴巴如两扇磨盘慢慢在研磨着,不时“噗噗”地喘口粗气,如此这般吃得有滋有味。
还得有人住在牛栏里,因为得有人给牛喝水,拉下的牛粪必须及时清理,更要注意的是,牛的尿是不能拉在地上的,否则那尿岂不流成河了?牛拉一泡尿可有大半桶,它要是在外干活,边拉边走,一泡尿可拉两里地远呢。
所以,住在这牛栏里的人,必定是生产队里德高望重者,必定是责任心极强者。其它的不说,这牛拉尿是要催的。生产队的牛棚就在我家的屋后,每当滴水成冰,北风呼啸之际,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常从梦中醒来,听见护牛人一声接一声的吆喝:“屙尿……!”“屙……尿!”“你这懒家伙,怎么还不屙啊?”牛的那泡尿不撒下来,护牛人就别想睡着。那牛也是,正是睡意正浓时被叫起来屙尿,想必也是极不情愿的,睡眼惺忪也就不那么听使唤。于是,那护牛人的吆喝就继续,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还听到他在那里吆喝。吆喝归吆喝,骂归骂,但决不至于打它们的。
大水牯是生产队里的脊梁,护牛人是必须和它睡在一间房子里的,至于黑毛牯子、花背牯和大母牛只好将就一点睡一间大房子,类似于低档客栈的“大统铺”,中间只用木桩隔开。此时,凛冽的寒风就在空阔的田野里穿过,发出呜呜的叫声,树枝上都结满了冰凌,人们在夜里醒来时,还会听到那冰凌断裂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响……
开春的时候,牛就从牛栏里牵了出来,队长就会率领记工员和大伙儿过来,围着牛评头评足,看这牛的膘长得如何,接下来就会按膘增减的情况给护牛人记工分,通常,这段时间里,护牛人得的工分就比别人多出许多。
牛的大力气和勤劳的秉性,也是在人们对它的尊重中产生的。
3
我是伴着牛儿长大的,队里的四条牛我都看养过,我了解它们就像了解自已的手指头一样。
学校一放假,母亲就要我去放牛,并且要我专放大水牯,她是不是觉得跟大水牯在一起很安全呢,我想是的。可是大水牯老了,干活远不如前,生产队长不乐意我去放牧,说它要有经验的人来看护,有时还得为他配点精一些的饲料。再后来,大水牯走都走不动了,如何办呢?
记得有位伟人说过,牛是农民的宝贝。湖区的水牛,只要它还能干活,是千万不可杀的,即使它不能干活了,要杀了,也得举行全体社员大会讨论进行公决,还要呈报到公社批准,未经批准宰杀耕牛是违法犯罪,听说还要处以徒刑。为了大水牯,队里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是不杀,“杀它良心上过不去!”很多人说话声音就磁磁的,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同时决定:派专人看护。
又过了一个多月,大水牯终于走了,他是寿终正寝的。它的皮被用来做了鼓皮,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如果说,大水牯身躯高大,骨骼粗实,拉力大,是生产队的主要牛力,从不惹事生非,一副当家人的作派;那么黑毛牯子就是典型的“愤青”,它总是要给我们找点什么麻烦。它是抵帐回来的,个头比较小,干活却不懒,每天下来犁田的亩数,和大水牯不相上下。而更有特色的,是它的脖子上面的一溜黑色的长毛,又密又粗又硬,颇似马脖子上的鬃毛,所以跑起来很有点威风凛凛,它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它还有一对与众不同的犄角,别的牛角是弯弯的,象初三初四的鹅毛月,它的两只角差不多是直的,从头的两侧张开去,就像两把装在头上的匕首,成了斗架的利器。
那年“双抢”完成得早,暑假尚未结束,我便去放牧它。一天收工时,邻村的麻水牯“发烈”了,就是现在说的发狂了,村里人叫法不一样,叫发烈,实际上就是发了脾气,并没有真正的疯。却说麻水牯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朝我冲来,吓得我没命似的逃窜,我一边跑它一边追,其情景真是恐怖之极!当我正往黑毛牯子身边跑过去时,却见它扬起四蹄,低着头,弓着背朝麻水牯冲了过来,一场恶战就此拉开。一时只听到牛角碰到牛角的噼啪响声,好不惊心动魄。后来战场移到了一座石拱桥上,黑毛牯子斗得性起,叫了一声“嗯呀”,用角猛力一顶,竟将比它大得多的麻水牯顶落到桥下!随着“扑嗵”一声巨大的闷响,水花溅起一丈多高,真的将我又吓懵了,我只担心麻水牯要是在大水沟里淹死了,我可脱不了干系。虽说“看牛伢子没牛赔”,但也是不好交代的。好在麻水牯又从沟里几番折腾爬上了沟堤。看着它气喘吁吁落荒而逃,我倒是放心了。
后来,自然地,我和黑毛牯子就成了最好的朋友,只要一放学,我就会去割青草喂它,还牵着它,经常去清水塘里洗澡。它对我几乎是百依百顺,队里的小伙伴谁也驾驭不了它,但只要我一声吆喝,它就会抬起头来张望,那眼睛朝上睨着,在日光下黑黑的,又亮亮的!看清我在哪里后,就一路小跑过来与我在一起。
一九七八年秋,我背上薄薄的行囊,要离开家乡了。正当我站在船舷,向岸上送行的朋友致意时,忽然发现,黑毛牯子也站在了高高的河岸上,它居然挣脱牛绳,追赶两里多路来到了湘江河边!望着我们那渐行渐远的轮船,它忽然就长长地“嗯呀”地一声,我知道那是在呼唤我!要不,近三十年过去了,那声音怎么老回荡在心头呢……
二、回望鸟窠
鸟窠,是我童年的行动的坐标。每当我蹒跚着跟外婆从外面回家,老远就会指着村里最高的喜鹊的窠对外婆说,我们就要到家了,因为那个鸟窠“是”我们家的。
从我还不懂事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了鸟窠。所以,它是我童年最早认识的事物之一。这种高高在上的存在,神秘、灵巧、生动,天生就是老天为孩提时代的我们准备的最好礼物。
鸟类总是讨人喜欢的,鸟窠当然也不例外。我家前面的菜园边有一棵高大的榆树,这榆树上竟然有三个喜鹊的窠,木架结构房子的楼椽上有一个燕子的窠,而茅草屋顶的屋檐下,有几个麻雀的窠。与鸟鹊为邻,人生幸事,时闻鸟语,不亦乐乎!有人说,在鸟语中长大的人是快乐的,那为什么我长大后快乐不起来呢,因为我还没有长大,鸟窠就看不到了,鸟语也快没有了,我们失去了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东西。
那时候,当我享受着这一切,我觉得是应该的,仿佛我的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便觉得异常的珍贵了。先是田园化建设,要砍了那不知长了几百年的榆树,喜鹊窠没有了,喜鹊就再也没来过了。开始我还以为仅仅是我们家的这三个喜鹊窠毁了,事情可不是这样,在我们那地方,喜鹊至少二十年不见了踪影。
这种快乐的吉祥鸟一大早就从窠里钻出来飞到地上以它特有的热情亮出它粗大的嗓音,以让人忍俊不禁的调门和凌乱可笑的姿态歌唱着舞蹈着,寻找他们需要的食物,甚至闯入鸡群争抢不应该属于它们的东西,把个宁静的农家院落吵翻了天,黑白相间的身躯既简洁又明快,又直又长的黑尾巴不停地一翘一翘,似乎在为自已并不高明的歌唱打着滑稽的拍子。喜鹊,我以为它是一个天生的滑稽表演艺术家。它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青鸟呢。
喜鹊还会干一些偷摸的勾当,例如家里晒在竹盘中的豆子,晾在篱笆上的淡干鱼,它也是要免费亲口尝一尝的。它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角色,可是这些行为从未受到过人们的责难,倒是博得乡人轻松的一笑,好像人们欢迎它这样做似的。也许,是因为农历七月七日那天晚上为牛郎织女搭桥的出色表现形成的光晕效应,让它一劳永逸吧。
喜鹊见不到了,好歹还能见到燕子。后来,我家里的茅草房翻盖了,变成了亮堂堂的砖石结构的楼房。燕子呢,春天是照例要来的,它们总是带走秋天的第一片落叶,也衔来春天的第一朵鲜花。也幸亏它是候鸟,只住几个月,只落个临时户口,要不它的住所更成问题。即使这样,它要安家也难多了,它必须在光溜溜的墙上做窠,做出来的窠如同漏斗状,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形状,而原来在楼椽上做,做出来的窠是半球形的。看来燕子也在适应人类的变化,适者生存。我们常说需要诗意地居住,燕子可谓这方面的行家。燕子本来就是一种喜欢与人亲近的鸟类,它不但用它小巧的尾巴剪出了一个明媚的春天,还给人带来许多的念想。仲春之夜,蛙鼓如潮,当我就着飘忽不定的煤油灯,游走在字里行间,在不经意间就会听到我头顶上传来它的呢喃,犹如幼儿的梦呓,引起我一种莫名的感动。此情此景,在城里居住你就别奢望有了。
燕子好歹有个安身之所,麻雀倒真的成了流浪者,跟我拜拜了。麻雀有点笨,只会在茅屋的屋檐下做窝,如今茅屋全都变成了瓦屋甚至水泥浇注的平顶的楼房,它又去哪里做窠呢。只偶尔看到它在空中飞,也不知家归何处。众所周知,麻雀是不甘寂寞的,总在絮絮叨叨有说不完的故事,也许这些故事很美妙很神秘,只可惜我听不懂,现在可好,快要听不见了!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