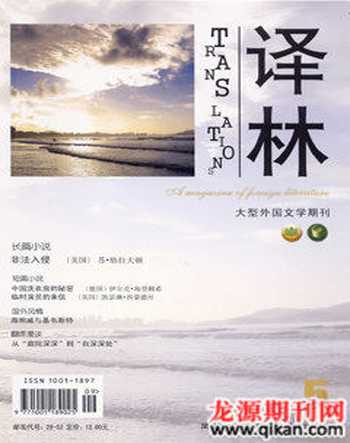孤独与荒诞
孙志农 戴鸿斌
摘要:《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表现了荒诞与孤独的主题,在结构上具有典型的元戏剧特征,手法上使用了非同寻常的悖反话语和重叠的意象,是一部典型的荒诞派戏剧,表达了贝克特当时对现实的无奈与绝望。
关键词:孤独 荒诞 元戏剧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克特在创作了名剧《等待戈多》和《残局》之后,笔耕不辍,于1958年又推出了另一部名剧《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该剧在主题、结构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传统戏剧相去甚远,是一部典型的荒诞派戏剧。
一、孤独与荒诞的主题
经历过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心有余悸的人们失去对世界的美好憧憬,开始质疑与反思现行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逐渐体会到人类的孤独,意识到人的处境既荒谬又毫无意义,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一样,明知巨石永远不可能被推到山顶,却还是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做着同样徒劳无益的工作。“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荒谬,一切历史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注:尤奈斯库,《出发点》,载于《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8—169页。) 此时,贝克特写出了《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旨在真实反映人类之孤独与世界之荒诞。该剧与贝克特以往的戏剧大相径庭,仅有一个名叫克拉帕的主人公,整部戏剧由他的一系列动作以及独白组成。故事发生在一间破房内,主要展示了六十九岁的克拉帕独自聆听自己三十九岁时录制的一盘磁带的情景。在一定程度上,克拉帕独居一室而又无人交流的状况体现了他的孤单与受隔离,同时也影射了人类的孤独现状。戏剧舞台背景的设计同样体现了孤独的主题。作者让“桌子和近旁笼罩在一束强烈的白色灯光下,舞台的其余部分则隐在黑暗之中。”(注:Beckett,Samuel.Krapps Last Tape and Embers.London:Faber and Faber,1959.下文中对该小说的引用出自同一出处。)克拉帕则坐在桌子旁边。这种黑白分明的舞台背景似乎是为了告诉读者:世界充满黑暗,死亡无处不存。在这样的世界里克拉帕与外界隔离,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后来,克拉帕说:“围困在这黑暗之中,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了。”显然这话有悖常理,因为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明白:黑暗只能使人孤独。克拉帕的言不由衷恰恰加强了他害怕孤独、不承认孤独却又万般无奈的痛苦感觉,同时也体现了世界的荒诞不经:生活其中的人只能靠昭然若揭的谎言来安慰和欺骗自己。录音机内的磁带里多次出现克拉帕用“颤抖的声音”唱出的歌词:“白天已尽,黑夜将至,阴影……”这显示了他的极度无聊空虚,突出了他的孤独状态。从克拉帕在三十九岁生日时所录的磁带里,我们听到他说,“与近几年来一样,我静静地坐在酒馆里,纪念这一特殊时刻。那里没有一个人。我闭眼坐在炉火前,手里捻着谷子……”可见,克拉帕的孤独并非一时的现状,而是早在他年轻时就存在了。接着在克拉帕的回忆中,“母亲的安息”和“永别的爱情”涉及的都是凄婉的“分手”场面,更加突出了克拉帕的孤独。此外,《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充满了荒唐可笑的镜头。克拉帕的“白脸、蓝鼻子和蓬乱的灰头发”、“太短的黑色窄腿裤”和“又脏又大、又尖又窄”的皮鞋令人觉得滑稽可笑。他把过去的磁带称作精神伴侣,却又骂它们是“小流氓”、“小恶棍”,实在引人发笑。总之,戏剧中有关人的孤独和荒诞的场面随处可见,充分体现了作品的主题。
二、元戏剧特征的结构
《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剧中嵌入了“戏中戏”情节。“‘戏中戏手法的运用被普遍认为是元戏剧最显著的特征。”(注:何成洲,贝克特的“元戏剧”研究,《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第81页。)1963年,李昂内尔·阿贝尔提出了元戏剧的概念。他认为元戏剧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表现已经戏剧化的生活。(注:Abel,Lionel.Meta睺heatre:A New View of Dramatic Form.New York:Hill and Wang,1963.)也就是说,元戏剧通常运用“戏中有戏”的手法,剧中人物意识到自己在演戏。到了80年代,理查德界定了元戏剧的几种不同类型,即“戏中有戏”、“戏中的仪式”、“演中有演”、“文学和真实生活中的指称”和“自我指称”,并指出:“元戏剧很少仅属于某一种类型。这些类型一般在某个戏剧中一起出现或者互相交融。”(注:Hornby,Richard.Drama,Metadrama and Theatre.London:Associate University Press,1986.)《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的元戏剧特征包括“戏中戏”与“自我指称”。一般说来,包含“戏中戏”的戏剧中仅出现两场戏:观众直接看到的那场戏和该戏中包含的另外一场。《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里的“戏中戏”却有三场戏:第一场戏是观众直接看到和听到的,由六十九岁时的克拉帕在舞台上的动作和他回忆过去一年的录音组成;第二场戏则由三十九岁时的克拉帕表演,他讲述了过去一年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想;第三场戏的主角是二十多岁时的克拉帕,他的表演同样由独白构成,讲述了二十多岁时的生活以及与名叫“比安卡”的女子的交往。三场戏大部分内容由独白构成,逐次展开后,又互相交错,最后回到第一场戏中。通过这复杂的多重“戏中戏”场景,贝克特延宕了观众对孤独、荒诞的主题的感受时间,加深了观众的感受,从而产生了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化”的效果,而“‘陌生化是元戏剧的真正意义”。(注:同②。)《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的另一个元戏剧特征表现为“人物的自我意识”(注:“人物的自我意识”指的是在表演中的演员意识到自己在表演,并且把这种意识毫无保留地传递给观众。),也就是指前面提到的“自我指称”。由于全剧包括三场戏,如果没有阐明戏与戏之间的过渡关系,戏剧会变得一片混乱,观众也就会感到困惑迷茫。贝克特正是通过剧中唯一的角色克拉帕的“自我意识”巧妙地完成剧中三场戏之间的过渡。当六十九岁时的克拉帕表演的戏暂停,开始以三十九岁时的克拉帕为主角的第二场戏的表演时,磁带里传来克拉帕的声音:“今天我三十九岁了……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或者大概如此……”从这场戏向以二十多岁时的克拉帕为主角的第三场戏过渡时,磁带里克拉帕的声音又起了重要作用:“刚才我听了自己前些年随便录下的几段话。我没有去查账本,但至少是十年或十二年前录下的。我想当时我仍然和比安卡住在凯德街……”从第三场戏回到以六十九岁时的克拉帕为主角的第一场戏时,克拉帕说:“刚刚听了自己三十年前所扮演的那个蠢家伙所说的话,真难相信我那时竟是那么差劲。谢天谢地,这一切总算过去了……”艾斯林指出:“通过由每年录制话语建立自传性资料库的这种手段,贝克特对于不断变化的自我身份问题进行图解式的表达。”(注:Esslin,Martin,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London:Penguin Books,1980.)而借助“人物的自我意识”,贝克特将剧中由“图解式表达”组成的三场戏衔接得天衣无缝,使戏剧带有明显的“元戏剧”特征,同时又让观众认识到人类的孤独现状。通过元戏剧这种特殊形式,贝克特有效地对抗了现存的规范与秩序,在为荒诞派戏剧增加了表现手段的同时,也为其平添了几分魅力。
三、悖反的言语与重叠的意象
贝克特的作品中,语言的危机是非常明显的,他“戏剧风格的一个主要倾向在于越来越多地使用独白的形式”。(注:Eliopulos,James.Samuel Becketts Dramatic Language.Mouton:The Hague,1975.)《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不存在任何传统戏剧常用的对白形式,这种对语言交流的背弃表达了贝克特的观点:在荒诞的世界上,对话与交流只能是一种奢望。于是,他选择了人物的独白形式进行创作。然而,独白也是一种语言的运用,而贝克特即使对于这种语言形式也是耿耿于怀。因此,在剧本中,他竭力去嘲弄语言和架空语言,正如他曾经的评价:“语言对我来说越来越像那一层必须揭去的幕帘,……我们没法一劳永逸地摒弃语言,但我们至少能竭力让它彻底的名誉扫地,把它钻上一个窟窿眼,使它背后逡巡游荡着的东西——无论有东西还是没东西——能渗透出来;我实在想象不出,今天的作家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的期望了。”(注:转引自盛宁:贝克特之后的贝克特,《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为此,贝克特经常使用矛盾话语来否定言语本身,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他对自己不同年龄阶段的评价。三十九岁时,他回忆:“那时我还断断续续地和比安卡一起住在凯德街。总算结束了。天哪!真是没得救!……”到了六十九岁时,克拉帕不仅与三十九岁时的克拉帕一样嘲笑二十多岁时的克拉帕,而且对三十九岁时的克拉帕也没有好感:“刚听了三十年前那蠢货的磁带,难以置信我竟这么糟糕。谢天谢地总算都了结了。”虽然这些言语流露出他对过去的不满和否定,但他在剧中却多次重放过去的录音。而且他每年都录制自传性磁带,并且时常聆听这些磁带,这些都说明了他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与珍视。于是,语言层面上的自我否定还被他录制、播放磁带的戏剧动作所消解,语言一如既往地失去意义。除了运用无意义的语言外,贝克特在剧中还经常使用“停顿”和“沉默”。当克拉帕在思考问题或者迟疑不定时,作者往往让他保持沉默,或者在剧中给出“停顿”的舞台提示。这样,作者巧妙地传达人物在不同语境中的心理活动,同时经常打断克拉帕的独白,使戏剧变得支离破碎,给人一种杂乱无序的感觉,从而符合贝克特本人的艺术观:“这只能表明需要有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容纳混乱的生活而不试图改变混乱的性质……寻找一种能容纳混乱的形式是当前艺术家的任务。”(注:Worton,Michael.Waiting for Godot and Endgame:Theatre as Text,in Pilling,Joh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cket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0.)
依贝克特所见,言语混乱不堪,无法充分完成交流目的。因此,为了表现主题,他在戏剧中创造了一系列与主题有关的意象。“当哲学家们只会用充满理性的思辨来讨论人的精神情形,贝克特则将它化作一个印象、一个故事,化作那一组组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注:朱虹,荒诞派戏剧的兴起,《荒诞派戏剧集》,贝克特等著,施咸荣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在《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近七旬的主人公克拉帕在简陋的小房间里播放、聆听和录制磁带的意象场景。全剧围绕这个意象表现出来的孤独主题而进行。因为这个意象的反复出现,就算读者读完剧本后可能忘掉一切,唯一挥之不去的恐怕就是这个孤单老头的形象了。除此之外,作者还塑造了笨重的录音机的意象,并且描写了克拉帕回忆中的“母亲的安息”和“告别爱情”等场景。由于语言的支离破碎,作者最终没有留下完整的故事,而是呈现了一系列片断,在读者心中留下一组组的意象,从而使读者在重构故事的同时,领略到作者的艺术风格,加深对主题的理解。
四、结语
艾斯林指出:“今天,当死亡和衰老日益被委婉语言和安慰性的谈话所掩盖,生活受到催眠性、机械化和庸俗大众消费窒息的威胁,使人面对他的真实处境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大。因为人的尊严就在于他面对没有意义的现实的能力;没有恐惧、不抱幻想地自由地接受它——以及嘲笑它了。”(注:Esslin,Martin,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London:Penguin Books,1980.)贝克特在戏剧中所揭示的主人公的处境归根结底并非个人的处境,而是人类共同的处境。《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结束时,克拉帕说:“也许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已过去了,那时曾有快乐的机会。可是即使我心中之火尚存,我也不要他们回来。不,我不要他们回来。”这完全可以看作是贝克特对自己的真实生活的写照。紧接着“克拉帕一动不动地瞪着前方,磁带继续无声地转动着。”可见,面对现实的困境,克拉帕已经麻木不仁。毋庸置疑,贝克特利用《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对现实的无奈与绝望。
(孙志农: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邮编:200036;戴鸿斌: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邮编: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