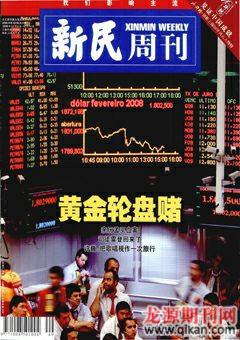走近“燕园之父”
傅国涌
司徒雷登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或者说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话,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闻一多演讲那天,正是司徒雷登受命于危难之时。这算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在20世纪中叶之前,司徒在中国的影响的确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他一生的命运也和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燕园之父”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先在杭州传教,后来到金陵神学院教书,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司徒在燕京的20多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六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一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很同意这个判断。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十数次赴美,募到大约250万美元,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6万元,并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但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筹款方面长袖善舞之外,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更有赖司徒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说白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出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位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
燕京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開“社会主义”课,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他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49年之后,燕京教授和学生中先后有56人被评为院士,成绩不可谓不显著。
但在他看来,“中国化”并不排斥“国际化”。虽是教会大学,燕京校园里弥漫的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宗教的氛围,比如与世界许多大学都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比如男女同校授课等。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长,融会中西,这就是司徒平常所说的“燕大精神”。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大学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一个堡垒。在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抗日教授的背后,如果没有司徒强有力的支持,燕园这个堡垒决不可能支撑4年之久,不断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30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3年8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一校训植根深远,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影响至大。
20世纪末,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书信中谈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训。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李慎之先生在信中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
“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
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
李慎之在3月11日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即便相隔多少年后,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常常禁不住哽咽。这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所在,是教育在人心中播下的种子。
———情系燕园六十年》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