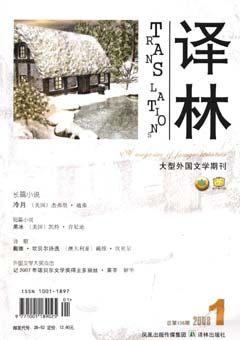城市男孩
(美)苏珊·穆迪
唐克胜 译
每人都听说过一见钟情。幸运的人甚至还能亲身体验。体验过的人会了解血液顷刻间在体内奔涌的全部奥秘。那颤抖的双腿,那穿越拥挤的屋子相遇的目光。这目光被行为研究者们称为交配的凝视。异性相吸嘛。
那天下午,伊芙·库克听见有人敲门去开门时的感受,与那种感觉是比较接近的。她站在门前的台阶上,与那个男子目光相遇,顿时觉得热血沸腾。他的皮肤是那种烤得较嫩的面包的颜色:锈褐色眼睛,姜黄色眉毛,小胡子像麸皮,发亮的头皮上稀疏的沙滩色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的身体健壮结实,撑满了没有棱角的裤子和短袖衬衣。虽然她不想,但她还是能够透过起了球粒的棉布衬衣,看见他的乳头。他脚穿尼龙袜、凉鞋,脚边的台阶上放着一个破包。遇到这样一个人,在起初的几秒之内,可能产生如此多的情感吗?特别是初次见面的时候?
“是伊芙吗?”他问道。“伊芙林·豪?”
“我是。”
“我是吉姆,你的堂兄吉姆。从南非来。”他把手伸出来,她条件反射似的握了握,然后放下。有一股汗味,令人恶心。她想在裙子上擦擦。
“喔,从南非来的?是罗斯婶婶的儿子?”
“对。”他说道,然后提起包,往前走。跨过门槛时,他推了一下她的背。“我可以进来吗?”不管她怎么回答,这时都为时已晚。他已经走进来,并将门在身后关上。
“嘿,”他说道。他跟着走进厨房时,那双狐狸般的眼睛在整个房间里扫来扫去。“非常不错嘛。”
“对。”她机械地把水壶装满,放在炉子上。“喝茶吗?”
“请给我来点儿咖啡,速溶的我也不介意。”他从木桌下拖出一把椅子,坐下。“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修的?”
“18世纪末吧。”
“这么旧?”他轻轻地吹着口哨。“一定值不了几个钱。告诉你……”他笑起来,露出两排奶酪色的黄牙。“…… 好像从那以后就没有装修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在这儿的时候,把这些墙涂一涂。”
“你在这……”她紧张起来。“你要在这里呆……”
“你为客人准备了房间,是吗?”他轻松地说道,然后站起来,走到老式石制水池上方、面对花园的一扇窗户前。“这块地不错。不过,需要修整一下了。这我也可以帮你。”
“我不想修整。”她的紧张性头痛又发作了。正是为了避免紧张,她才独自住到乡下来。与爱德华生活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需要挂念。早晨在整洁、干净的卧室里醒来,看到光线从没拉窗帘的窗户里射进来,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床上躺一天,或者穿着睡衣走出门去。中午吃早餐,半夜吃晚餐,随心所欲的那种自由使她充满了满足感。在过去,这种满足只能从狼吞虎咽奶油圆面包、法国面粉糕饼、巧克力、饼干、超市中的各种蛋糕来获得:这种满足来得很快,因为它暂时遮蔽了爱德华的声音、需要以及询问。
刚到这里的时候,她担心太孤独。她不知道怎样打发日子,以至于刻意去掩盖那些空虚的时日。用什么办法打发这漫长的时光?她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候。首先,应该把屋子收拾一下,也就是让它看起来简单一些。使她感到吃惊的是,她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很少,几张桌子、一张床、几把椅子、一把舒适的扶手椅、一台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至于厨具,一些炊具、几只陶器和几副餐具就够了。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她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卖掉了。现在,她喜欢慢慢收集一些反映她目前单身身份的东西:旧货市场上的几只盘子,虽然很旧,但还算漂亮。几只不成套的杯子与茶碟,几只玻璃杯,几个小水壶,还有几件让她奇想无边的零碎东西。她把这些东西放入墙上的碗柜里,嵌入墙里的碗柜差不多占去了厨房一面墙的位置。
她一边整理房间,一边欣赏花园的景色。她对这里的一切还有待熟悉,它的野性,自然界的扩侵,杂草的蔓延,水果的四处滚动,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帮助和鼓励,居然能破土而出的花朵。夏天,花园周围是一道由接骨木树形成的豪华篱笆,上面缠绕着犬蔷薇、树莓,斜倚其上的紫丁香和一层层欧芹。春天,花园里开满了苹果花和梨花。到秋天时,这些花变成了甘美的金黄色果实。冬天,这里有冬青树、红豆杉、树莓和花楸。树根、树叶和浆果自个儿持续地生长着,不需要她付出什么,自由自在地以本色示人。她觉得自己似乎不配享受这样慷慨的给予。
直到想起爱德华,她才知道这是对她的报答,对她多年谦恭、柔顺的报答,对她最终有勇气结束他们之间一切的报答。
第一年夏天,她拨开黑莓矮树丛和接骨木灌木丛,从中走过的时候,她发现一个地方,簇叶丛生。有人曾经在这里种植过无核小水果,树叶间挂满了悬钩子、草莓、醋栗和黑醋栗,有的呈白色,有的呈黑色,还有的呈深红色。这些年来,她伺候着它们,给它们浇水,给它们施肥,不让花园中其他植物入侵此地。使她感到抱歉的是,尽管她害怕侵扰花园,但有一年夏天,她还是在花园中种上了莴苣和红花菜豆。迄今为止,她一直让花园中的植物们随意生长,她不希望自己的侵入让植物之间相互隔离。但事实上,花园似乎已经接纳了它们,菜豆茁壮成长起来了,莴苣也破土而出了,生长情况不亚于专业人士所种。自那以后,她又试着种了欧芹、萝卜、羽衣甘蓝、花椰菜,都长势良好。
园艺成了她的新职业,她蓬勃发展的事业。多年来,她一直参加艺术班,尽管爱德华对此嗤之以鼻,尽管茶水有意无意泼到她的速写簿上,尽管学习资料被没收了,尽管他每周都不让她去艺术班学习,但她坚持下来了。现在,摆脱了他的束缚,也有了自己的时间,她开始把自己身边的一切画下来,然后大胆地寄给一家代理机构。几乎不能相信的是,她有这么好的运气,这些速写被用作生日卡、明信片、日历,甚至书籍的插图。她挣了很多钱,过着比过去奢侈的生活。她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心中无比快乐。
吉姆来到这里的那年夏天,一个个无核小水果成熟了,又大又圆、又沉又多。她一个人吃不完,又不能全部保存在缸里,或者做成果酱,或者放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工棚的大冰柜里冰冻起来。其他植物也长得十分茂盛。那是一个异常丰收的夏天,花园边缘全是疯长的草本植物:黑莓、黑刺李、野李子、山楂子,甚至茴香、山柳菊、接骨木、车前草、茄属植物、紫草科植物等等,犹如重头草一样丰富繁多。
他喝完咖啡之后,她领着他来到花园里。看到这么茂盛的植物,他感到很压抑。站在膝盖深的草地里,他四处张望着。“乱糟糟的,不是吗?”他不安地说道。
“我喜欢这个样子。”
“谁想到的?”他问道。
“想到什么?”
“住在利物浦的人会来这么一个地方居住。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说,如果路边没有娼妓,或者街对面没有舞厅,你会渐渐凋谢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是那种女孩。”
“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变了。”
“我没有,我是一个城市男孩,而且以此为荣。我喜欢人行道,喜欢街道对面舞厅里的人。这样的地方使人感到焦虑不安,几里路也没有一个邻居,连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
“正是这样才显得完美。”
“完美?”从他鼻子里传来一种不太悦耳的声音。“但是,就像我跟你讲的一样,修整修整还能卖几个钱。”他挥舞着手臂,太阳在他的姜黄色头发上闪烁着。“把草割一割,把篱笆整一整,把那些植物归拢归拢,把所有的杂草拔掉,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他充满深情地看着她。“你不知道怎样修整花园,是吗?”
“你是什么意思?”
“我虽然是在城市里出生,在城市中长大,但连我都知道,那些都是杂草,那些带花边的草。那边。”他指了指前方。“欧芹,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它会四处蔓延。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好好整一整,今后要用它做什么都行。”
“什么意思?”
“计划许可证,”他说道。“应该不太难弄到。如果他们给你出难题的话,就送一点钱吧。”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她在后门外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开始剥早些时候从菜地里摘回来的豌豆。一些红色围绕在他周围,好像他红棕色的肤色融化于空气中了。
“可以想象,这是很值钱的一块地。特别是从那个角度看的时候。”他说道。“你可以在这块地上再建五六座不错的小一些的房子,你仍然有住在乡下的感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附带一个车库。我们称之为起步者之家。”
“起步者之家?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钱,伊芙,我说的是钱。只凭它的外观,就可以弄几个钱。比如厨房,完全跟中世纪的如出一辙,还有生锈的破炉子。”
“它是非常好的阿加炉,不是什么——”
“墙上的油漆剥落了。厕所的墙上全是黑霉。”
与爱德华在一起的那么多年使她习惯了逆来顺受。她听命于他,对他敢怒不敢言。眼前这一位,又如此无礼,缺乏起码的教养。“如果那样的话,”她平静地说道。“你去找个更舒适的地方呆着吧。吃完午饭就走吧。”
“伊芙,”他说道,语气突然变得亲切起来。他走过去,她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恶臭与汗味。他额头上全是晶亮的汗珠。“伊芙,老妹子,不要生气,我说的话都是有根有据的,我一贯如此。我当然不会这么快就离开,扔下你一个人,我们毕竟兄妹一场。”
“我们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现在成为朋友就更加理所当然了,是不是?我现在是独自一人,你也是孑然一身。你从来没有生过孩子,是不是?现在也没有丈夫了。我们两个人应该同舟共济。”他的腰很粗,弯下去有些吃力。他在她的椅子旁蹲下来。“不管我说过什么样的话,我确实喜欢你的房子,比较……奇特。”
“不,”她说道。“你是对的。这房子是需要维修一下了,这个样子不太适合客人住。我已经习惯了,但我想你肯定会喜欢更舒适一点的地方,酒店或宾馆什么的——”
“你不会赶我走,是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又才重逢。我的意思是,这里的冬天一定很冷,而我已经适应了南非的气候。我想,冬天装上暖气不难吧。不知道你是不是买得起?”他的额头皱了起来。
“我买得起。”
“是养老的钱,是吗?准备将来不时之需的?”
“没问题,谢谢。”
尽管她一再暗示,那天晚上,他还是住了下来。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他也住了下来。一天早晨,她醒来时,发现他在她家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了。她下楼去放水壶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恐慌。他会不会一直赖在这里?怎样才能让他从自己的生活中离开?她多次请他离开,他都好像无动于衷,她也不想通过公开对抗的方式把他赶走。跟爱华德这些年,已经使她受够了。再说,罗斯婶婶一生善良,自己欠她很多,现在只好通过这个令人不快的儿子来偿还了。
他无处不在,她无法躲开。如果她上楼到自己的卧室去,他就去敲她的房门。如果她说她想去散散步,他就尾随其后。他整天跟着她,唠唠叨叨,满身臭汗。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屋子,使她感到窒息。不仅仅是汗味使她感到窒息,还有湿衣服的味道,从来没有洗过的衣服的味道和脚的味道。还有他的声音。他发元音时舌头的位置不对,发得太平,这使她的脸因为厌恶而扭曲。她去工棚中的工作室,他站在身后,喘着粗气,对她的画指指点点。
“应该可以赚几个钱。”他说道,好像她画画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他在的时候,好像整个花园都黯然失色了;他走过的地方,花草也开始枯萎。
一次,她发现他翻看了自己的东西。“他们好像很喜欢你的作品。”他恬不知耻地说道。“我不知道你挣了这么多钱。”
“你怎么敢偷看我的东西。”她说道。
“别这样,说真的,伊芙。如果他们出那么多钱,而不跟你要几张花草和樱桃素描的话,也许你就得不到那么多。”
“不要碰我的东西。”她说道。她怀疑他已经翻了她的抽屉,偷看了她的银行账单和建房互助协会名册。
“我是你的堂兄,”他说道。“你唯一的亲人,你当然不应该有什么东西瞒着我。特别是当——” 他停下来,考虑如何表达。
“当什么?”
“几天前,我到城里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去了一趟,让律师起草一份新的遗嘱。我没有多少东西,伊芙,但我想把那点东西给你。”
他等待着,几乎可以肯定,她不仅会对他感激不尽,而且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我要去律师那儿把我世间所有的东西馈赠给你,好像他们两个人已经套在一桩可怕的婚姻之中。她怀疑他在撒谎,即使没有撒谎,他也没有什么东西给她。她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打开电视机,看起足球比赛,房间顿时淹没在一片嘈杂喧闹之中。
她又渴望独处了。这座房子已不再属于她自己。她的平静被打乱了。
他似乎认为,她除了照料他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做饭、洗衣、伺候吃饭、饭后抹桌子和洗碗,而他什么也不做。他的胃口很好,食欲也很强。他自己取饮料喝,打长途电话不付任何费用。他跟她一起购物,篮子里全是他需要的东西,从不花一分钱。
有一次,他们从村子里开车回来,他说道:“我们正好到这里了,我去一下议会办公室,询问一下计划许可证的问题。”
“干什么?”
“为了别墅后面的那块地啊。还记得我曾说过我认为这不会太难吗?我是对的吧。有一个业主已经同意了。开个先例吧,明白吗?他们是很难拒绝你的。”
“我为什么需要这样?”
他短粗的食指在拇指上擦了擦。“伊芙,不要告诉我你要拒绝。对你来说,那个花园太大了,你自己很难打理。你看看里面乱糟糟的样子。”
“我喜欢。”
“现在,你也许喜欢。可是五年、十年以后呢?”
“听着,吉姆。”她平静地说道。“我不想要什么计划许可证。我不希望后花园里建一些可怕的小房子。我不希望我周围有着很多人,我也不想你在这里。”
他哈哈大笑,姜黄色的短须从他下巴上的厚皮中戳出来。“好了,好了,”他说道,“你知道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我是。”
“但我是你的堂兄。”
“那又怎么样。”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我们必须相依为命。”
“我想让你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有主意了,回家以后,你跷起脚休息,我来给你沏一杯茶,怎么样?”
一晃两个星期过去了。她困惑极了,彻夜难眠,满脑子都是他。一旦成眠,他又潜入她的梦中。即使他不在眼前的时候,她也惦念着他。当初遇到爱德华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整天想的就是他。一见钟情。爱与恨是何等的相似!
她的作品变得粗糙起来。她不再画田鼠在有穗的玉米间荡来荡去,而是画一些黄鼠狼在矮树光秃的树枝上淘气地恶作剧;她不再画罂粟或者麦仙翁稀疏的花瓣,而是画延龄草和大戟。蘑菇出现在她画面的背景中,颓废、充满了威胁,而以前的背景是一片树叶和草地。以前她以多汁的黑莓给画镶边,现在镶边的是茄属植物和苦艾。她用最丑陋的名字给那些植物命名,什么飞蓬、什么芹叶钩吻、什么荨麻、什么伤草。
她的编辑克里斯汀给她打来了电话。“你怎么了,伊芙?”她开门见山地问道。
“什么怎么了?”
“我刚刚收到你的邮件快递。”
“怎么样?”
“我虽然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我也看得出来,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男人吗?”伊芙听见克里斯汀猛吸了一口香烟,对着话筒吹过去。
她从心底里已经没有了感觉,于是说道,“男人,自从爱德华之后,我这屋子里就不想再有男人了。”
“那就是别的原因。不管是什么,把它销毁了吧。做日历表的人是不会采用你寄给我的那些东西的,我甚至不用交给他们就知道。”
吉姆从楼上下来,伊芙循着他沉重的脚步声走进厨房。她听到冰箱门打开的声音,然后是勺子碰到陶器的声音。她不用看,就知道他未经允许在享用冰箱里的东西,就像一只晒黑的猪那样,直接从碗里或者盘子里吃东西。
“你想说什么,克里斯汀?”她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把对他的憎恶喊出来,也不要把让他离开和渴望回到她如此钟爱的独居时代的强烈愿望喊出来。
“我在说,如果你不振作一点的话,我们两个都要失业了。”
“有那么糟吗?”
“你看了你最近的作品没有?”
“……”
“你寄给儿童自然书籍的那些画——别提了。你本来是想让那些你所爱的人享受一下田园诗般的乡下生活,然而,他们被你误导了。你刚刚寄给我的那些东西很可能让他们晚上做噩梦。”
伊芙没有说什么。全是他的错。如果他不走的话,她精心构筑起来的一切就要全部毁掉了。
克里斯汀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下个星期到我这里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吧。我们好好谈一谈。”
“我明天要去伦敦。”伊芙说道。
“我也去。”他的额头和稀疏的头发上全是晶亮的汗珠。
“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有公务在身。”
“也许我能帮得上忙。”他看了她一眼,希望她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他们知道你现在不是孤身一人,也许对你有所帮助。有一个人在密切注视着你的兴趣与爱好。”
“不行。”她重复道。
“好吧。我就一个人清静一天吧,”他说道。“午饭怎么办?”
“我今晚会做一些,走之前准备好。我还要给你摘一些无核水果,你可以跟乳酪一起吃。”
“太好了。”他看着她,充满了柔情。“你对我太好了,伊芙。我有点承受不起。”
“我知道。”
他笑起来,好像她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前一天晚上做的砂锅菜只需要翻热一下。她来到外面,从挂满露珠的草地走到覆盆子架子前时,整个花园都在欢迎她。欧芹抚摩着她的裙子。树叶间还有许多水果:她摘了一大碗,又加了几片薄荷叶。她来到厨房,在上面撒了一些糖,然后放在冰箱里冰冻起来。他吃完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砂锅菜和她故意留在碗柜奶酪盘里的斯第尔顿奶酪。
她回来时,他已经死了。跟克里斯汀吃过午饭之后,她故意多逗留了一会儿,参观了皇家艺术院,观看了一部由马吉·史密斯主演的受到热评的影片。她要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死去。
她报了警。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后,警察赶到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她把电话线拔掉藏了起来,让他求助无门。在等待他们到来的这会儿,她把电话线重新插上。她将早先写好的一张便条订在橱柜的一个丝杆吊钩上,然后倒了一杯白兰地,来到花园里。他吐过。临死之前,他的五脏六肺都畅通了,再加上他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有毒的气味。他倒下的时候,折断了一把弯木制成的椅子。
“我留了一张便条,”法医在检查他的尸体时,她这样解释道,并断言那具姜黄色尸体可能是由于呼吸系统衰竭所致。从法医的初期诊断来看,最大的可能是中毒,吃了花园里有毒的樱桃而中毒,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今天早上,我把这个便条放在橱柜里。你知道,我走得很早,我不想打搅他。”
“冰箱里有你的午餐砂锅菜。”一个官员大声念道,“只需要加热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水果,随你吃。我今晚大约11点回来。祝你今天过得愉快。伊芙。”
“是我的错,”伊芙说道。“我应该记得。”
“记得什么?”
“他对乡下的事情不太了解,比如,对植物之类的不太了解。他总是说他是一个城市男孩。我应该早就意识到,我早就应该替他采摘一些水果。他一定是午饭时间跑出去,抓到什么樱桃就吃,而不知道会中毒。”
“不要伤心了,库克夫人。”
“但他死得这样惨,这样痛苦。不管怎么说,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死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
“这不是你的错。”
“我尽了力。”她哭着说道。“我愿意照顾他,毕竟他是我的堂兄。”
“这么多年之后,自己屋子里又有了一个人多好,有个伴。我们虽然有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们俩很快熟悉起来,从来没有吵过架。我真的会想念他的。”
“你不需要烦恼。你不可能知道他会认为茄属植物是能吃的。”
“真的搞不懂他怎么会这样——那些樱桃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是有毒的,不是吗?”她附和着。当然,除非外面裹一层糖,和悬钩子、草莓、红葡萄干混在一起,然后用薄荷叶子盖住那种味道,才能吃得下去。
“没有人会责备你。”警察安慰道。“这是一个悲剧。”
爱德华的死也是一个意外,或多或少是一个意外。他是在他们出去散步时从悬崖上摔下去的。爱德华一直喜欢散步,而她从来没有从散步中获得过乐趣。
她抬起头来看着警察。“没有吉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活,”她悲伤地说道,“他现在走了,我又要孤身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