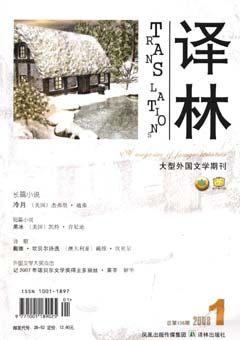黑冰
(美国)凯特·肯尼迪
陈新宇 译
我上前查看陷阱时,看到那位太太家门廊上的灯还亮着。已经是早上了呢。“这真是太浪费电了。”我告诉爸爸后,他这么说。他呵出的热气在空中成了一道白烟,好像在抽雪茄一样。我们给兔子剥皮,去了皮的兔子身体冒着热气,而剥下的兔皮看上去像只手套。
剥兔子皮喽——以前妈妈给我洗澡前,脱衬衣、汗衫时,总爱这么说。每只兔子贝利先生给我三块钱,他用来喂狗。我把兔子装在一只木盒子里给他带去,盒子上画着一个苹果。肉铺里兔子每只才两点五美元,不过贝利先生说他更喜欢我的。我已经存了五十八美元了,我想买一辆自行车。
爸爸觉得把钱存起来是好事。游客们围在地产中介的窗户旁,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指指点点——爸爸觉得他们是群疯子。当路上头的那位太太买下那套房子,当“已售”的牌子插在地上,人群散后,爸爸走过来。他从墙壁上抽出一块墙板,低头看着那些腐烂的榫头,鼻子里哼了一声,仿佛硬憋着不打喷嚏。“那位太太可是个十足的怪人,”他说,“这些榫头全烂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房子,手里卷着一根香烟。“这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平。”他说着,踢了那块隔板一脚。我也跟着踢了一脚。
那位太太搬进来后,我不再去山上设陷阱了。我沿着湖边的小路走进森林,小路是兔子们踩出来的,我把自己变得像兔子一样小,用我柔软矮小的爪子穿过小路。我看什么都不一样了。看到兔子们坐着休息的地方,它们用鼻子嗅嗅河柳的根,一条条咬下树皮,吃掉。
你得设好陷阱,干脆利落地把兔子杀死。机关要是卡在兔子腿上就不太好。整晚兔子都会哀叫、滚来扭去,早上你只得再杀一次,而它的眼睛会盯着你,在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贝利先生说他简直不信我能在离小镇这么近的地方逮到兔子。我告诉他,只要仔细观察,算好在哪设陷阱就行,就这么简单。他微微点了点头,只看得到他下巴扬了扬。“你知道怎么做,比利。”他说。
他付我钱后,我们一起喝了杯茶,看看他的那些狗。它们认识我,知道我来干什么。它们见到我时眼神都不同。
最近,早上起来时,什么都结冰了。山上全是枫香树,每次我看到它们,就想起在学校里的那一天,那次我是对的而佛莱先生错了。佛莱先生拿出一张枫香树的图片给大家看,还说这种树在秋天落叶,其他家伙一听,马上埋头做笔记。我觉得有些话脱口而出,我说,不对,它们不掉叶子,它们掉树皮。佛莱先生说,全班只要我一开口,肯定答错。这真是千真万确。现在,我看着那些树光着身子站在薄雾中,回想着佛莱先生说我错了时,我拼命摇头,而其他家伙只是坐在那里笑,低头盯着自己的手,等着放学,就像那些狗等着兔子一样。
树叶的味道闻起来像咳嗽糖浆一样,湿湿的树皮五颜六色。一天,我看着这些树叶,眼睛开始变得古怪起来,我飞到空中,低头看着树梢,它们一蓬一蓬连在一起,像罗娜姑妈家扶手椅上那些鼓起的一团团绿色东西。这回事我对谁都没说,甚至爸爸也没告诉。刮风时,树们就大声说话,它们安静时,温柔极了。我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可能是谈论雨水吧。它们长出新芽时,全身都是树脂,在空中颤抖。也许是太兴奋,也许是太害怕。
不过现在是冬天,树看上去灰头土脸,缩小了一圈,好像它们靠切断思维来苦挨日子,就像我爷爷中风后,爸爸说他的身体在慢慢关闭。路上,淤泥里有冰凌,你可以凑近点看,冰凌是长条状的,长成一排排,泥土越烂糊,冰凌塞得越紧。这是在夜里,在寒流下冻起来的。你把脚放在泥坑边上,轻轻一踩,冰凌全碎了,成了冰碴,像小溪水一样流出来。
有时候,兔毛上沾着霜。我用手把它掸掉。兔
① 黑冰是一层很薄的、几乎看不见的冰层,如在道路或人行道上,通常由霜雾造成,极易造成交通事故。毛很好闻,味道像地衣或干苔藓。妈妈留下来的几双手套的衬里就是用兔毛做的。一次,我把热乎乎的手从手套里抽出来时,闻到了妈妈的味道。“你号什么?”爸爸问。我把手套藏在床垫下。每次摸到它们,就好像摸着绿叶,那么柔软、那么干燥,韧劲十足,根本不知道秋天到了。
看见那位太太家门廊灯亮着的那个早上,爸爸给我戴了顶新帽子,因为我生冻疮了。新帽子是他用兔皮做的。他用他的毛衣使劲揉着我的耳朵,痛得我紧紧咬着牙,然后他把兔皮帽两边的帽耳朵往下扯了扯,系上。“等你带着兔仔们回来。”他抱着两手站在那里,说完就给炉子添柴去了。
一天,有个在饲料供应站打工的男孩,在学校里对其他孩子们说,我们那里很落后,甚至都没有冷、热水供应。他说,“水是接到家的,就像递送上门的那样。”我问爸爸递送是什么意思,他卷着一支香烟,说为什么问这个。接下来他买鸡饲料的那次,他要求当天递送过来。然后他给炉子添了好多柴,把火烧得旺旺的,水汩汩地开了,喷溅出来,直冲到屋顶,又像下雨一样落下来,声音听起来像饮料店里奇妙的咖啡机发出来的。当这个男孩带着饲料来了后,爸爸让他把饲料倒进箱子里,接着问他想不想去厨房洗洗手上的灰。他去了。我站在那看着母鸡们,把自己变得跟它们一样小,我的脚四下里扒拉着,感到稻草就在我的爪子下,我用尖硬的喙啄麦粒时,麦粒在我嘴下碎成粉末,就在那时候,一声惊叫,男孩从厨房里冲出来,两手高高举起,红彤彤的,像塑料一样。他跑过时,爸爸在后面叫道,“别忘了告诉你的朋友们。”
我把兔子塞进麻袋里,听到亮着灯的那所房子里传来音乐声。是小提琴的声音。我抄近路走过山坡时,看见买下房子的那位太太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到门廊上。她穿着新罩衫,你都能看到衣服上的折痕。她头发跟狐狸毛一个颜色。看见我,她脸上立刻放光,人也兴奋起来。虽然她根本不认识我——就像学校的女医生,她们总是在我身上做些愚蠢的检查,还说些傻里傻气的话,希望我立即编些话说出来,可又不给我时间想想。
她说,“嗨,你好,怎么不说话,舌头给猫抓住啦?”她搽了口红。我想她可能要去教堂。
我说我没有养猫,她眉毛往上扬了扬。
“这么冷的天,你起得可真早。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她说,好像我们打算合伙开谁的玩笑一样。我给她看最上面的兔子头,她的嘴张得老大,她说,“哦,天哪!哦,可怜的小东西!你干吗杀它们?”
我说卖给贝利先生。我说它们死得很快,陷阱机关总是正好卡在它们的脖子上。她双手紧紧抱着自己,摇了摇头,说,“天哪,”她看着我的兔皮帽,我慢慢转着头,好让她瞧个仔细。
她突然问我,是不是住在山脚下的房子里,我说是的。她说那个位置好极了,可惜给那里通电太贵,不然的话,她就会买下来。不过她挑的这个小地方也不错,一块黄金宝地。她说朋友们都说她疯了,可是等房子涨价时,她才是笑到最后的人,她还要把这里扩大。我等着她说完,好走。我感到兔子在袋子里慢慢变硬——我闻得到它们的味道。
“你叫什么名字?”最后她问我,我说比利。
“你上学吗,比利?”
我看着她,说大家都得上学。她眼睛眯起来,又高兴起来。
“难道那是所特殊学校,为特殊儿童办的?”
我不明白她说些什么。也许她对学校不了解。我说不是的,接着我的嘴巴不受控制,脱口而出,“你的头发跟狐狸毛似的。”
她笑了,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天啊,”她说。“你真怪,不是吗?”
一个穿着红色睡袍的男人走出来,站在露台上,那位太太说,“看,亲爱的,地方特色。”“多可爱的帽子。”那个男人对我说。我等着他们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可那个男人只是一个劲抱怨天气冷得要死,谢天谢地,他们装了中央暖气。太太说是啊,整个地方的改造进行得还不错,然后她又看着下面的小路,说,“唯一的问题是,看不到该死的湖。”接着她又说,“比利,给罗杰看看你的小兔子,亲爱的,”我掏了一只出来,罗杰说,“哦,我的天!”
他们笑啊笑的,最后罗杰说,“嗯,这看起来像灯亮着而家里没人。”这不对,他们都在家,可灯才关掉。
当我走下小路,经过那个急弯,穿过路堑时,我的靴子踩在黑冰上咯吱直响。你得十分小心,可不能在这上面摔个狗啃泥。人们说黑冰看不见,其实不是的——你得蹲下来,凑近点仔细瞧,看哪里的水结了冰,又化过一点点,然后又冻起来,整个晚上反复几次,直到它看起来像老瓶子上的一片玻璃。
我回家时爸爸冲完澡了。兔子皮不太好剥,因为耽误了太长时间。剥皮的声音听上去像把他们在学校医务室里往你膝盖上贴的创可贴撕去的声音。那天在学校里,有人撞了我一下,我膝盖磕在水泥地上,我贴着创可贴回家后,爸爸说,“撕下来。”爸爸望着我,我一把把它们撕下来,膝盖又出血了。“那也叫急救?太可怕了,”爸爸说。“让它们透透气。”我看着膝盖,觉得它们里面的油渗出来后,好像里面的合叶生锈不灵活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人们开车来到山上,整修那位太太的房子。你可以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还有机器声,不久一个非常尖的新屋顶竖起来,比树都要高。太太的朋友们,就是曾经笑她发疯的那些人,一开始都过来了,天越来越冷后,他们就没露面了。湖边已结冰了。一天我悄悄爬上去,看见那位太太站在新露台上,露台整个刷了一层粉红油漆,她抱着两手站在那里,盯着那些树出神,看上去不太高兴,整修的事什么都才做到半道上,花园里全是稀泥,周围堆着一大堆石头,感觉她在等人把它们搬走。我看见一只鸭子安静地呆在树下,像树下其他东西一样。我再走近点,她看见我了。
“嗨,比利!”她叫道,我走过去,发现那只鸭子是假的。
“看那些该死的树,”她叹了口气,说,“我讨厌看到它们。”
她又穿着那件罩衫,不过看上去不怎么新了。
“比利,那些树到底是什么?”她说,我说它们是枫香树,她笑起来,不等我说完,就说她本该猜到我会这么说,而我还在想着接下来该说什么。
我说今晚又有寒流,天会更冷。她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开始跟她解释,可她没听进去——她低着头,看着下面湖边的林沟,头转来转去,像在商店里买衣服的那些太太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决定买还是不买。
三个星期后,我爬上树,只想听听它们的声音,再找些个好地方设陷阱,可是发现了一棵树生病了,这是第一棵。我摸着它的叶子,知道它要死了。它是棵老树了,很大很大的老树,过去它的嗓门很大,现在却只能张着嘴喘气。它在流血。有人绕着树干砍了一圈,树液滴干了,这是树的血,爸爸说的。那人用的是一把小锯子,后来还用了斧头,不管这人是谁,我看得出,他不会用锯子,那一圈周围都是刮痕。我救不了那棵树。我想痛快地把它杀死,这样它不会站在那里看着我,挣扎着活着。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又发现了一棵这样的树,接着发现七棵最大的树被砍掉了。我到处仔细察看,我爬到树上,从树顶上看,发现死的树从那位太太山上的房子附近一直延伸到湖边,成了一条线。我回到地面,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比利,你逮到兔子了,”我走过来时,贝利先生说。“没有你,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今天这两只又大又肥。”
我拿了钱,朝山顶上那位太太的屋子走去。透过树丛我看见她在花园里种什么东西,爸爸说整个苗圃的生意现在都靠着她。
这次我轻轻地,直走到她和她的假鸭子面前,她才看到我。她往后退了一步。
“天啊,小鬼,别烦我,好吗?”她说,全身发抖。她披着条头巾,几缕头发滑了出来,你可以看到红色的头发就在那里止住了,下面的头发是深褐色和银色的,这真奇怪,因为有时候狐狸的尾巴也是这样一道一道的。
“上帝,这鬼地方,”她嘴里嘘着气说,扔下手中的泥铲。“这里的人还不够冷淡吗?你不用偷偷摸摸的,像……一样,”她停下来,说,“算了,算了。”我发现她戴了个护膝,我还在盯着她的护膝看的时候,她开口说话了,语调跟刚才完全不同,“比利,你这个盒子是哪里弄来的?”
我说,“从那边棚子里弄的。”她笑了。我低头看着盒子,上面有个苹果的图案。
“从你的棚子里?那是个殖民时期的指形榫盒子,比利。你知道它们值多少钱吗?”她的声音很兴奋。
“把它卖给我,怎么样?”她说。
我说那是装兔子的,她问我,棚子里还有没有。我说我可以去看看。她是个疯子。爸爸有时候把这种盒子劈了扔进炉子里当柴烧,或者用来放钉子、螺丝之类的。
“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好多这东西,”我说。“就在弗兰克林汽车修理店里,有好多卖的。”她的眼神看起来有点像铁丝网后头贝利先生的狗。
“什么时候?”她问。
“星期天。有好多这种东西卖。”
“比如?”她问道,接着又说了一长串的名字——拨火棍?烙铁?碗橱?——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好多这种东西,”我说。“好多这样的盒子,上面还写着字、画着澳大利亚的地图、鸸鹋之类的动物。”
她抱着双手,盯着我瞧。“画着鸸鹋、袋鼠的盒子?还有这盒子一样的合叶?”
“没错,”我说。“不过你得一大早就到。六点半,或再早点才行。因为有些人从城里过来。”
她问我弗兰克林汽车修理店在哪,我告诉她了。
“我能比那帮商人到得早,”她说,看着山下的树,从山上直到湖边,树正悄悄死去。
星期六,我设了个陷阱,就在湖边的草丛里。爸爸说没有好的理由杀生不好,但我知道兔子们不会介意的。树们现在很安静。浓雾就要出来了。月亮已经升起,周围一圈黄晕,就像你在有雾的夜晚拎出来的汽油灯。
我心里想着这事,几乎睡不着。我想着她夜里出来,手里握着从五金店买来的新锯子,割开树皮,兔子们那长须的、柔软的嘴一路嗅着,贝利先生的狗不停地吠叫着,由于被链子锁着声音有点哽塞。
我起来时,天还很黑,黑得像学校操场上空中梯子的钢条,冰凉的金属硌痛你的胸口。我发现陷阱里一只兔子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真为它感到难过。我知道她也会的。因为在一个太太的脑子里,你可以为兔子伤心、着急,却不会为树难过。
夜里泥土结了冰凌,在那个急弯附近,黑冰像玻璃一样光滑。我很仔细地摆弄着兔子,就像仔细设陷阱一样。兔子看起来还像是活的,坐在那里,坐在路中间。
弄完后,我回到床上。我又摸了摸妈妈留下的手套。
爸爸再来叫醒我的时候,他居然知道我起来过了。我搞不懂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最好去检查一下你的陷阱。”他一边生火,一边说。
在那条路上,法雷尔先生的拖车正把她的车从沟里拖出来。车撞到一棵枫香树上,挤扁成了一团,树叶和枝条散得满车都是。法雷尔先生说救护车来帮忙时,那群笨蛋他们自己也差点在该死的冰上滑倒。“她这样一个女人,天又黑得要命,星期天起这么早,干吗去?”法雷尔先生一边套上钩子,一边说:“该死的疯子。”
她的前轮下,我看到白白的皮毛,从里翻出来,像是只手套,像我的帽子。我向下穿过树林,摸着一棵棵生病的树。在路上,我一脚踩进了荨麻丛里。爸爸说:如果你自己不小心,哭也没用。我四下里看了看,发现了一些酸叶,我涂了些上去,奇迹般地好多了。一切有毒的东西,它附近总有解毒之物,只要你四下里看看。这也是爸爸说的。
我点起火,用烟熏熏我的陷阱。再过五个多星期,我就可以买一辆山地自行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