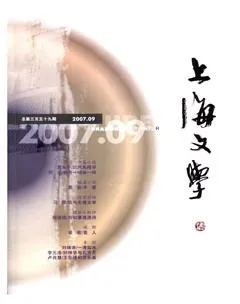陌生人的悲伤
◎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切 著
卢丽安 干贤婧 译
作者简介
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切: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阿南布拉州,在恩苏卡大学城长大,完成了小学、中学教育,在尼日利亚大学学习了两年药学。之后移居美国,在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学习传媒和政治学专业,2001年以最优等第毕业。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硕士学位。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切从大四起开始写小说处女作《紫色木槿》,2003年甫经发表即引来文学界广泛赞誉;获得2004年英国橘子文学奖提名、2005年约翰·卢埃林·莱斯奖提名。在《陌生人的悲伤》中,作者沿续行云流水的优美文风,以批判的眼光聚焦于尼日利亚移民,展现了她对种族、性别问题的深邃思考。
在母亲开车送她去机场的路上,琪娜切伦没怎么说话。她看着窗外的树,有的树叶早已变成了熟透了的香蕉色,有的成了浆果红;还有一些树都掉光了叶子,带着光裸的枝桠直直挺立。这是她喜欢聊的话题——新英格兰的秋天,花儿们是怎样把自己的色彩借给了树叶;她也喜欢说夏天,那时的太阳是怎样地缱绻不舍、逗留不去;或者冬天,在寂静的雪景与刺痛耳垂的冷冽中,那股原始纯粹的感触。“拜托了,”这种时候她母亲就会说,“拜托了,娜,说点现实的事吧。”母亲总用恳求和怜悯的语调说这句话,好像表示她知道得小心应对琪娜切伦,但这话又不得不说。今早她们离家起程去机场之前,母亲就用那样的语调说过:“到了伦敦之后,亲爱的,试着跟奥丁正正常常地说话。”她也想跟母亲说,她已经在电话里同奥丁正正常常地聊过了,不是吗?奥丁好像觉得她说话足够正常,因为他这不是邀请她去见面,不是吗?不过她还是回答:“我会的,妈妈。”
她会试着正正常常地说话,尽管她不确定什么是“正常”。比如说,在最近系里的节日聚会上,大家沉浸在纵容里,争相暴露流言隐私——这就是“正常”?她听到一连串的以自我为主的陈述,比如关于“我”会/已经/希望/打算处理的事;都是“我”。没人会谈论自身以外之事,除非这事与说话的人有关。也许交谈就是这样的吧。也许她逃离生活太久了以至于不习惯交谈了吧。九年的确是一段漫长的时间。那次节日聚会是她这段时间以来参加的第一个聚会,第一个社交活动。也许正是那个活动让她最终屈从于母亲和恩格丽卡姨妈的主意——找个尼日利亚男人来“相亲”。“相亲”——这词当时让她发笑,现在仍是。
车子里暖气太强了;琪娜切伦把车窗摇下一点,不禁回想起早先她“相”过的尼日利亚男士们,她曾经电话交流过的,说一口做作的美式英语、谈话中不时提到宝马和郊区别墅的男士们。奥丁就不同,也许是因为他在电话交谈中没怎么提他自己;他不自夸自恃,这给人一个自信的印象。至少琪娜切伦是这么认为的。奥丁是恩格丽卡姨妈介绍认识的。“美中不足的是他不住在美国,”恩格丽卡姨妈几乎是鬼鬼祟祟地、小声地说,“但你搬家很容易,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琪娜切伦原想问姨妈,为什么那位男士(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他叫奥丁)不能搬过来。但她还是没问,她不想让人觉得她还是原来的琪娜切伦,那个在母亲口中离群独居的人,那个让母亲忧急担心的人。她想做个愿意重新生活下去的,新的琪娜切伦。
她们到达机场后,母亲拥抱了她,用她那双每周在韩资美甲坊里缀新的手捧起她的脸,说:“我衷心祈愿,娜娜,这次能顺利成功。”琪娜切伦看着母亲忧虑的脸庞和修细了的眉毛,点了点头。她真希望自己能有母亲那样的热情和庄重的希望。她希望自己能感觉到些什么,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那围困着她的麻木——已经把她缠封了九年的空虚麻木。
在她登机前,她看到一位妇女正与孩子丈夫相拥道别;那女子有着一头难看的鬈发,哭的时候泪水在化浓妆的脸上划出条条沟纹。她的孩子们哭了;丈夫强装勇敢,望着别处。琪娜切伦注视了他们一会儿,然后也哭了。她发现自己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去感受陌生人的悲伤;就在机场,她感觉到了那个家庭的悲伤,便为他们逼近的分离哭泣起来。
琪娜切伦喜欢伦敦那种幽闭的感觉,一切看起来都相当小巧紧凑。她喜欢阿玛拉表姐狭小的公寓里的那间小房间,喜欢这个没有一棵树的水泥街坊和公寓楼的斑驳砖墙。从她们在希思罗机场见面拥抱起,阿玛拉就一刻不停地和她聊天。而这会儿,阿玛拉九岁的儿子正在电视机前玩电子游戏,边玩边叫喊着。阿玛拉的声音、她儿子的叫喊、电视里的声音都让琪娜切伦觉得烦躁,她感到太阳穴抽痛紧绷。
“那些加勒比海女人老勾引我们的男人,我们的男人也傻得可以,居然听她们的。接下来,她们就会生小孩,也不想让男人娶她们。哦,她们只想找人和她们生孩子。”阿玛拉说这话的时候,乔纳森尖叫出来,两眼死死粘在电视屏幕上。
“把声音关小点儿,乔纳森。”阿玛拉说。
“妈妈!”
“现在马上把声音关小了!”
“我会听不见的!”
他不调低音量,阿玛拉也不再多说什么。她转向琪娜切伦,继续聊天。
“你知道吗,”琪娜切伦抱着双臂,说道,“我们太过于宽容我们的孩子,只因为他们讲话带外国腔。这挺有趣的。”
“什么意思?”
“如果在尼日利亚,乔纳森这么做是会受罚的。”
阿玛拉调开了视线:“我马上就不让他玩游戏了。”
琪娜切伦知道她做不到的;乔纳森来自阿玛拉破碎的婚姻;他生父有钱,每次乔纳森从他那儿度周末回来,总有新玩具。更何况,阿玛拉还幻想着,就靠放任他随心所欲来维持儿子对她的尊敬呢。
阿玛拉又说话了:“最近我遇到的这个男人很善良哦,不过口音太糟了。他在奥尼查长大的,你能想像他口音有多糟。他老把ch和sh弄混。去逛销品茂(shopping mall)说成差品茂,坐椅子上(chair)变成坐席子上。不过,他说他愿意娶我,也愿意收养乔纳森。‘愿意’!好像他在做慈善似的。愿意?你想想。不过这也不是他的错,毕竟我们是在伦敦,要找到门当户对的是不可能的。他这样的,要是在尼日利亚,我连正眼都不会看他一眼,更别说跟他约会。但你知道,在伦敦,人人都变成一样平等的。”
琪娜切伦想着阿玛拉刚说的——在伦敦,人人都是一样的。这让她觉得好笑。散居海外的尼日利亚人抱怨着在国外同胞中,阶层界线模糊不清,无名小卒居然也会一夜发家,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抱怨让她觉得好笑。在伦敦,人人都是平等的。
“你还好吧,切伦?”阿玛拉问,“你看起来无精打采。”
琪娜切伦伸伸腿,双手仍环抱着膀子。她和阿玛拉一起在额努古长大,小时候一起玩洋娃娃,一起在拉各斯的皇后学院上学又在同一年毕业;那是在政变发生、阿玛拉家移居英国和她家移民美国之前的事了。现在,她看着阿玛拉——三十八岁,漂白过的淡棕黄头发,涂得血红的甲爪。“你还好吧,阿玛拉?”她轻声回问,“你看起来就像个粗制滥造的洋娃娃。”
话一出口,她就希望自己没说过这话。这太像过去的琪娜切伦了,那个在她母亲口中已经遗忘了生活中微妙规则的琪娜切伦。但阿玛拉好像也不生气。琪娜切伦也知道那是因为阿玛拉——事实上还有她整个大家庭也是——早已找到了与自己相处的方法,一种琪娜切伦称之为“围堵”的策略。她想起了母亲曾给阿玛拉全家写的信。信是九年前写的,但她最近才读到,那还是在周末她去看望母亲,随手翻她抽屉时看到的。母亲保留了草稿,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记录保存者。“自从伊凯迪的悲剧后,琪娜切伦就不再是她自己了,”母亲用潦草的笔迹写道,“别把她说的话放在心上,别动气回应;时间会让她挺过去的,但她需要我们的耐心。”
现在,她猜测阿玛拉是回想起了那封信才选择不生气的。无论如何,阿玛拉总是出乎意料地心平气和。太滥好人了,她们还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人那么说阿玛拉。也许,这样的人即使处于已离婚、不满足和年近四十的焦虑中,还可以不改本性。
“对不起,阿玛拉,”琪娜切伦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关系,”阿玛拉说,又停顿了一下,“那么伊凯迪怎么样了?有什么好转吗?我是说,他是不是再也不能……呃……变正常了?”
“谁知道呢?”琪娜切伦答道,“奇迹或许会发生,不是吗?谁知道呢?”
“可怜的替罪羊。”阿玛拉咕哝着。但琪娜切伦知道阿玛拉是对着她说的,因为阿玛拉猜想这是她想听的。发生在伊凯迪身上的事情对阿玛拉来说是太遥远了,对每个人都太遥远了吧,除了她。尽管没人愿意承认,但是事实是,她的亲友们的愤怒早已被时间冲淡了。现在阿玛拉眼中流露出的同情,在琪娜切伦看来,是为那些甚至不知自己值得同情的人而保留的。
“我想我得出去一会儿,”她说,“我要去买张交通一日卡,然后逛逛。”
阿玛拉有点不放心,说:“要我陪你去吗?你可以吗?”
“我会没事的。”
“想去购物吗?和奥丁约会你准备穿什么了吗?”
“我还不知道我得特地为约会去买衣服呢。”
“哦,可是,切伦,你以前喜欢购物的呀。你喜欢去伦敦市中心转悠,最后就会说这里的东西都比美国的品牌直销店贵,你还是回去买算了。”阿玛拉说道,她的声音和眼中透露出的渴望都让琪娜切伦觉得想笑。在与伊凯迪在一起的过去,她曾经喜欢淘便宜货。她知道三州交界区的每一家品牌直销店,甚至和经理们也都交了朋友,这样每次大减价的时候他们都会通知她。她的品位也反映出伊凯迪的爱好:有时她会花几个小时寻找带有立场声明的名牌男式衬衫。然而,她并不怀念过去的生活,尤其是在她正走向新生活的现在。
灰蓝的夜幕正漫罩伦敦时,琪娜切伦步入了靠近河堤地铁站的星巴克,坐下来,要了杯穆哈咖啡和一块蓝莓松糕。她的脚底快乐地疼痛着。这里并不很冷——康涅迪格的寒冷可是无出其右的——刚才她穿着羊毛大衣都闷出汗了,现在衣服正挂在她的椅背上。有人落了份《新政治家》在桌子上,于是她开始读了起来。她觉得自在,甚至可说暖和舒适,于是她很快就读到了书摘栏里登的一篇有关拜伦的文章。这时一位巴基斯坦妇女和小男孩上前问她能否合用一张桌子。她没有意识到这么快咖啡厅就客满了。
“当然可以。”她说。虽然她的提包并不是放在他们要坐的桌子那一头,琪娜切伦还是把它拎起来。
那妇女挂着个小巧的鼻环,随着她头的不停转动而闪闪发光。她儿子约八九岁光景,穿着印着米奇鼠的外套,手里抓着个游戏机。琪娜切伦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孩子正和她搭讪。一开始他问她,糖包旁边的细木棒是不是用来搅拌的;她说是的;又问是不是有地方放她的杂志——要不要他移一下椅子?然后,当他母亲正想给他切松糕时,他大声嚷嚷说:“我不是小孩子了!”
他长了张讨喜、肉乎乎的胖脸,说一口优雅的英语——琪娜切伦猜是“巴基斯坦优越上层人”的口音。她想像着这母子在卡拉奇的大房子、车子和仆人们;他那戴鼻环的母亲费劲心思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把他拉扯大,成为一个负责任、不骄宠的人。
“你住在伦敦吗?”他倾身向前问道。琪娜切伦还来不及回答,男孩母亲就用流利的英语插嘴进来,他只能忿忿地瞪着她。
“对不起,”他母亲转身向琪娜切伦道歉,“他话太多了。”
“没关系,”琪娜切伦回答道,她合上《新政治家》,表示自己乐意交谈。
“他父亲去年去世了,”他母亲小声说,“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来伦敦旅游。我们以前每年圣诞节前都来。”那妇人说话的时候不停点头,男孩儿看起来很恼火,好像不想让琪娜切伦知道这事。
“哦,”琪娜切伦答。
“我们去了泰德现代美术馆。”男孩说。
“好玩吗?”她问。
他皱了皱眉头,她知道他以为这样看起来会老成些,说:“太无聊了。”
他母亲站了起来,对琪娜切伦说:“我们该走了,呆会儿我们要去看戏。”然后转身对儿子加了句:“你不能把游戏机带进去,你知道的。”
那男孩儿不理她,对琪娜切伦道了声“再见”,便径直朝门口走去。琪娜切伦知道他本想再留一会儿,所以才没碰松糕。她看着他们离开;琪娜切伦多希望自己问了他的名字,问了他母亲一些她亡夫的事。
她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冰冷的细雨正下得纷纷扬扬。她走向地铁站,感受着细雨滴噼里啪啦打在她的大衣上。走到那儿,琪娜切伦被台阶上繁多的、泛着泡沫的痰迹吸引住了。她觉得这里的某处可能会有一首诗——也许是一首自由诗,诗里闲扯着这片混乱、痰迹和伦敦的风格;就在这时,她的火车来了。不一会儿,琪娜切伦便经过吵闹的车厢,坐在脏兮兮的座位上。拿着《新政治家》,她想起了那位巴基斯坦妇女、小男孩,和他们被旅游观光、松糕和争吵粉饰起来的悲伤。静静地,琪娜切伦哭了起来。
奥丁很英俊。其实从他先前附在邮件里的照片上她就看出来了。但是面对面地看他,她看到了被照片掩盖掉的,粗旷分明的五官肌理,这使他在她眼中显得更迷人了。她从没见过哪个男人像他那么爱笑,每次笑都闪现出他白净的牙齿。她确信这样的牙齿一定漂白过。
他们坐在苏活区一家法国餐馆昏暗的地下室里,都吃着山羊奶酪色拉,桌子中间一根蜡烛光影摇曳。是她先点的菜,然后他要了一份一样的。她很好奇,如果她告诉他,九年来她从未和任何男人在餐馆里同桌吃饭,他会说些什么。他会不会像恩格丽卡姨妈说的那样,觉得她很奇怪?“不要跟他说起伊凯迪,不然他可能会觉得你有些古怪。等到你们亲近些再说吧。”恩格丽卡这样建议过。这让当时的琪娜切伦觉得好笑,因为她从来没打算过要把伊凯迪的事告诉奥丁。
“你那么漂亮,”奥丁说,“我真纳闷竟然没有人能赢得你的芳心?”
琪娜切伦叉起盘子里的一片生菜叶,些微起了警觉。这场游戏没有规则吗?那么快就提到婚姻了吗?“你也不差啊。”她说。母亲会希望她这么说的。这听起来才正常。去年系里的聚会上她听到过这句话。当时,她那个教18世纪文学的女同事——琪娜切伦办公室旁第三间的那个——踉踉跄跄地走到系主任面前,说:“你真他妈的是个有趣的作家。”他回答:“你也不差啊。”说完,他们周围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翻。琪娜切伦一直怀疑,是不是因为他们喝醉了才这样的;现在看来不是,因为奥丁也正大笑呢。
“你真不同寻常,”他说,“你脸上的表情,好像你超然物外似的,其实不是。这很有趣。”
她喝了点水,不确定该说什么。
“那,住在新英格兰怎样?”奥丁问。
琪娜切伦开始诗意地描述新英格兰的秋天景致:羞赧的太阳,大自然不同的金黄色,凉风追逐胡萝卜色的树叶。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最后,奥丁看来有点惊讶地说:“嗯,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每次我听到新英格兰,想到的就是康涅迪格、缅因这些地方,我猜那里都是白人吧。”
“呃,其实还是有多样性的。我几个班的学生中大约百分之十是黑人。”琪娜切伦耸了耸肩,希望看起来自然一些。“食物很好吃。”她又加了一句,低头看着盘子。
在一种她熟悉不过的安静里,他们沉默地吃了一会儿。琪娜切伦突然被她自己手中叉子从盘子到嘴的运动、被奥丁下颚的咀嚼运动,搞得不自在。
“那,”他说着放下叉子,“还好吧?”
琪娜切伦不确定他指的是什么。在一次电话聊天中,她提到过她收到了一笔补助,想利用学术休假时试着完成她的诗集。他是说那本诗吗?还是说他们刚才的晚餐、他们的会面?“什么好不好?”她问。
他笑了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唤回你的注意力,你刚才好像走神了。”
“哦,没有,我一直在听。”她说着又把腰板挺得更直了些。
吃点心的时候——他们分了一块提拉米苏——他谈起了散居海外的尼日利亚男人对妇女的态度。那些男人认为,他们可以四处拈花惹草,但女人不可以;他们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女人该去煮饭烧菜,即使两人的工作时间一样长。他边说边摇头,以示自己认为这些男人该更明理些。琪娜切伦很感动地意识到,他正试图告诉她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也许是他想做怎样的人。
他握着她的手,两手紧靠着桌面。“能和你见面我真太高兴了,”他说。这幅场景的普泛性质突然触动了琪娜切伦。任何一位妇女,任何受过教育、定居海外、三十多岁、正寻觅终生伴侣的尼日利亚妇女都能和他在一起,不一定非她不可。
母亲和恩格丽卡姨妈都打电话来。她听着两个紧绷的声音问她晚饭怎么样;当她说要到星期五才会再见他的时候,两人都倒吸了口冷气:“哦!天呐!那可是三天后!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
当然是琪娜切伦的主意,因为奥丁早就邀她隔天共进午餐;事实上,当晚他就想请她一起回家了。
“是他的主意。他工作很忙。”她说。
“唉,这可不是好兆头。”琪娜切伦忘了这话是谁说的,母亲和姨妈的声音太像了。然后,母亲犹豫了一下,问道:“你正正常常地说话了吗,娜?”琪娜切伦平静地回答:“是的,妈妈,我有。”
她挂了电话后,阿玛拉说,在水湾的一个朋友办晚会,她觉得琪娜切伦应该去参加。
琪娜切伦说她宁愿在家读那本她没读完的《新政治家》,对一本她没有掏钱的杂志,至少她应该坚持看完。阿玛拉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会儿,但什么也没说。阿玛拉走后,琪娜切伦想像着这场晚会的情况。她曾经和伊凯迪去参加过一些晚会;不管是圣诞晚会、订婚宴会还是生日派对,都无所谓,因为它们都一样——到处充斥着家洛富米饭和嫉妒、胡椒汤和东家长西家短:谁在伦敦切尔西买了套房或者在芝加哥郊区买别墅啦,谁家孩子得自闭症啦,谁老婆打包跑啦,谁还没拿到合法居住证或者绿卡啦,谁被卷入了信用卡诈骗案啦,谁的丈夫回尼日利亚包养了更年轻的女孩子啦。这场在水湾的晚会正是母亲认为正常的事情。
第二天,琪娜切伦碰巧遇到内维利·利普顿。他们以前见过,阿玛拉介绍他俩认识的,后来他还低声告诉琪娜切伦,邻居们都叫他“牛津剑桥的八十岁蛮老头”。就像其他街坊邻居一样,阿玛拉也喜欢他,因为他关心、也送礼物给孩子们。乔纳森的书中,有一半是内维利·利普顿给的。在利普顿的资助下,乔纳森已经游览了不少博物馆和陈列馆;乔纳森还老是用“利普顿先生说的”这一句话来强调权威。
“他没有必要窝在这里,”阿玛拉告诉过琪娜切伦,“我想,利普顿先生这么做,是为了申明他的政治态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自恃清高了。”琪娜切伦当时这么说。她说了吗?现在她倒不是很确定当时她回应了什么。她回想起来,利普顿先生对尼日利亚了若指掌;当时,在他们简短的交谈中,利普顿先生总是脱口而出尼日利亚的历史事件和日期;对此,琪娜切伦是又着迷又觉得难以接受。这次,当她在街上撞见他,再一次在游览伦敦的途中相遇,利普顿也记起了琪娜切伦,亲了亲她的双颊,并且注意到,自上次见面后她把头发剪短了。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好吗?跟我来吧。”他说着,早已迈开步子希望琪娜切伦跟上来了。琪娜切伦的确跟了上去。归根结底,这不就是“生活”吗?——屈于冲动,拥抱率性。和她几乎不了解的、阿玛拉的老邻居一起吃午饭,这就是生活。
“我要带你去旅游者俱乐部。你的夹克很可爱,所以我们进去不会有问题。他们有个很恼人的着装规范,你知道的。”
“真的啊。”琪娜切伦答道,惊讶于他会觉得她的旧夹克可爱。一会儿后,他们被领进了旅游者俱乐部的华丽内厅;琪娜切伦环顾四周,看看围桌而坐的男士们都穿了什么。她原以为他们都会戴蝴蝶领结的;但看到的大多数西装,在利普顿剪裁考究、橙绿镶边的条子夹克映衬下,都显得古板保守。显然内维利·利普顿和这里的男士们不同,而他也敢于显示他的不同。她想像着他的另一种生活——在非洲探险,然后带着黝黑的皮肤和新奇生动的土人故事,凯旋而归。
“这里太闷了。”他们入座后,琪娜切伦说了句。她用“闷”的比喻义;他听懂了,于是大笑起来。
“你的嗓音很动人,”他说,又凑近了些,“如果你说话没有美国腔就好了。”他正盯着她看。他的眼睛那么蓝,看起来就像是画上去的;他白得惊人的头发已见秃顶,衬着布满细纹的面容。等上菜时,内维利·利普顿向她介绍了旅游者俱乐部简史,发表了关于君主制必要性的长篇谈话,刻薄地攻击了那些想禁止猎狐、不识好歹的蠢蛋。他称琪娜切伦“亲爱的人儿”、“亲爱的女孩儿”,还用了一个生涩的副词“非法地”。他以一个牛津剑桥出身的八旬英格兰老人的旧式风范说“他妈的”来逗琪娜切伦笑。利普顿似乎决心把琪娜切伦介绍给每个——包括侍者在内——经过他们餐桌的人;他以迅速、几不可辨的低语咕哝出她的名字,然后再加一句:“她是尼日利亚人。”
他们的菜刚上来,一个鼻毛突出的男人就走了过来,瞥了眼琪娜切伦,转问内维利:“这个黑皮肤美女是谁啊?”
内维利介绍了她,告诉那男人琪娜切伦是尼日利亚人,又加了句她在美国是诗人和助理教授。
“你好!”那男人问候道。
琪娜切伦什么也没说。那男人一直微笑着。
“很高兴认识你。”那男人微微抬高了音量,似乎认为琪娜切伦没听到先前那一句话。然而,琪娜切伦还是一言不发。沉默延漫开来;她察觉到了紧张压迫的感觉,也同时享受着这种难堪笨拙。这是过去的琪娜切伦的行径,而她却觉得这样很自在。那男人朝内维利咕哝了几句,便走了。
“亲爱的女孩儿!”内维利夸张地低语:“你为什么那么做?”
“‘黑皮肤美女’。”
“哦。他是在赞美你。”
“不是,他在赞美‘您’。就像赞美某个人有匹出色的赛马一样。”
“那老家伙没有恶意的,事实上,他可恨不得能坐在我现在坐的位子上。”内维利笑了起来;此刻琪娜切伦突然有种冲动,想把她的那杯水泼到他脸上。但她只是单指扶了扶眼镜框,用愉悦的口吻说:“知道吗,利普顿先生,我觉得这里你们所有人都是小心眼儿的老头儿。”
内维利瞪了她好一会儿,然后大笑起来:“老天,琪琪伦……”
“你叫我什么?”
他看着她,好像他不确定她说了什么。
“我的名字叫琪娜切伦,利普顿先生。琪—娜—切—伦。”
他重复了几次她的名字,脸上尽是想念准这名字的急切表情,可是偏偏每次他都念得粗声粗气的。念了几次,利普顿问道:“顺便插一句,你名字是什么意思?”
“‘上帝为我着想’。”
“是吗?我有个津巴布韦来的朋友,叫肖纳,意思是‘上帝之火’。有趣吧。我还真怀疑上帝有火算不算好事。”他抿了口水,“‘上帝为我着想’,这不怎么适合你,不是吗?”
“为什么?”
“为什么?亲爱的,这名字暗示了顺从,而你呢,一点也不顺从。老天,你骨子里压根儿就没有顺服的细胞。”
利普顿听起来很讶异。琪娜切伦审视了他脸上咖啡色的老年斑好一会儿,才说:“听你的意思,好像我应该柔顺一点。”
是她的幻想吗,还是他,这个强硬又老于世故的老人,真的脸红了?“关于种族问题,你真的很敏感,是不是?非洲人对种族问题可没这么敏感,当然喽,除非他们住在美国。”
“你好像对非洲了若指掌、无所不知。”
他伸出手来握住了她的:“别这样说话,亲爱的。”
不知道为什么,琪娜切伦开始讲起伊凯迪来。也许她只是想告诉内维利·利普顿,他无权评论她对待种族问题和其他任何事的态度。也许根本不需理由来辩白;这些话冲口而出,一句接着一句从她嘴里蹦了出来。
首先,描述伊凯迪被枪击的那晚之前,琪娜切伦提到一些伊凯迪曾经说过的,关于他和琪娜切伦的话:什么他俩是缘定的;如果有人抽干了他们祖居村庄的河水,人们会发现他们的名字被刻在河床上,紧紧缠绕,难分难解,等等。伊凯迪被枪击后,琪娜切伦曾想过回尼日利亚,去他的家乡乌玛纳奇和她的家乡阿坝,她想跳进这两个地方的河流,想办法抽干它们,看看那里写了什么,看看伊凯迪的名字会不会以残缺不全的字样显现出来。她告诉内维利·利普顿,伊凯迪的脾气:他生气的时候会砸啤酒瓶;还有伊凯迪的理想主义,他投身抗争活动、游行、组织纠察队;放着他父亲在西哈特福德的空房子不住,搬到东哈特福德的窄小房间里,因为那是他自己付的钱;就在他站在公寓门前准备开锁的时候,警车到了;三个人,三个白人。后来,在审讯中,他们声称以为伊凯迪要拔枪。坐在法庭上的琪娜切伦哭了;公寓前的楼道那么狭窄,伊凯迪根本不可能避开这四十多颗子弹。更后来,琪娜切伦甚至希望伊凯迪是那个一度占据所有新闻版面的海地人,那个被警察用脏扫帚柄鸡奸侵害的海地人。至少那个人,那个海地人,体肤完整。
最后,她告诉内维利·利普顿:“伊凯迪失去身体功能、全部瘫痪时,正是暮秋;两天后天就下雪了,几周后春天到来,春雨绵绵。季节像水般流转,伊凯迪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一直在等待转机;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等。”
琪娜切伦放下叉子,气自己竟然把伊凯迪的事告诉这个不值得她倾诉的男人,气伊凯迪躺在哈特福德的病房里,瘫痪了不说,还沮丧消沉得连她来探视时,眼也不眨一下;或者,是他选择不再眨眼了。
但,同时,琪娜切伦也感到莫名的兴奋;她终于说出了伊凯迪的事,她甚至能告诉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自己并不确定到底是否曾喜欢过这个令她生命消停了九年的男人。
奥丁对第二天要带琪娜切伦去的餐馆赞誉有加,所以琪娜切伦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喜欢它。这餐厅相当摩登高雅:铬制装饰、宽广明亮的空间以及雕刻在金属薄片上的菜单。
“这种装潢可称为艺术,不是吗?只是它与你的、你的诗的艺术不同。”奥丁说。
“我想是的,”琪娜切伦喃喃低语。今天的奥丁有些不同;或者,是上次她看得不够仔细,所以没有注意到——不管这不同是什么?她不想谈论她的艺术;“你的艺术”这种说法已经够烦人的了,于是她说:“‘奥丁’听起来不像是伊布人的名字。”
“是‘奥丁切左’,我把名字缩短了,你知道的,让他们念起来方便些。”
“哦。”她低头看着食物——几条烤鱼如此精心摆放着,弄得她都不忍心吃,以免破坏了图样。恩格丽卡姨妈放着儿子恩耐麦克的名字不用,而叫他“鲍伯”,也是“因为他们”。琪娜切伦记得,她和伊凯迪还因此批评过姨妈。“因为他们”——琪娜切伦想问奥丁,“因为谁?”人犯不着否决从祖宗那儿继承来的传统,然后却为了自己的选择来怪罪某些子虚乌有的人。
“这鱼怎么样?”奥丁问。他看起来有点紧张;原来就是这点不同,紧张。
“它吃起来就像它看起来那么有意思。”琪娜切伦答道。
奥丁放下叉子:“有些事我还没告诉过你,但你得知道。”
“什么事?”
奥丁大声清了清嗓子:“我有个儿子,六岁,监护权判给了他母亲,但我每两周要看他一次。”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甚至其他桌的人也似乎都停止了交谈。“上次我不想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任何会让你太早退缩的事。”奥丁说,他逃避着她的视线:他的眼光越过她的头顶,又迅速收回聚焦于他的食物。琪娜切伦突然觉得他看起来年轻了许多,脆弱了许多。她想告诉他,没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被允许——放下包袱、解开负担。但是,这只能在准备就绪的情况下才行。
“没关系。”她说。
“我就知道脸是不同的,”奥丁弯了弯身,朝琪娜切伦凑近了一些,“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在迷茫,不知我的生活在哪。而你进入我的生活正可以帮助我找回平衡。”
琪娜切伦惊奇地握着叉子。他怎么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能让他快乐的人是她,就一定是她呢?
她觉得有必要跟他讲讲伊凯迪,让他知道,她也有事没告诉他。但她没说。她没必要说。意识到奥丁没必要知道这件事让琪娜切伦松了口气;坐在这儿看着他干净的下巴和深棕色的眼睛,琪娜切伦更如释重负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奥丁最终将与另一个不因追求新生而备受困扰的尼日利亚女子在一起;一个与她不同的女人——不会像琪娜切伦一样崇尚自然偶发、渴望真实无伪,追求一种没有预设的连结,就好像在星巴克遇见陌生人一样的连结。
回到康涅迪格,琪娜切伦从机场打的回家。车里的暖气上得太慢,她冷得在后座缩成一团。空气是凝重的,路的两旁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那刺眼的苍白灼痛了她的眼。从新闻里,她听到在马萨诸塞州有些孩子死了。他们在结冰的湖面上玩闹,冰层破裂,人沉了下去。他们淹死在零下温度的水中:三个年龄在七到九岁的小男孩。
琪娜切伦闭上了眼,但她没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