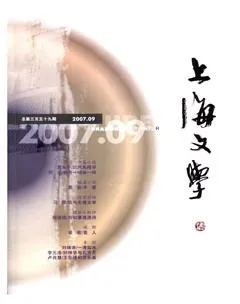瓷人
民国20年前后,保定东大街有了一家店铺,专门烧制瓷人。师傅姓梁,名宝生,三十几岁的样子,自称德州人氏,手艺由祖上几代传承下来。梁师傅的店铺,没有雇用伙计,忙里忙外就他一个人。店铺的字号:瓷人梁。有些街人并不知道梁宝生的名字,干脆喊他“瓷人梁”。梁宝生有一妻一子,从不来店铺抛头露面。有人看到过,梁宝生曾在保定庙会上游玩,妻子小他几岁,儿子刚刚会走,一家人其乐融融,其状陶陶。
梁宝生的店铺后边,用红砖垒了一个窑。不大,五步见方。如果有了生意,凑成一窑,梁师傅才去点火。若是主顾急用,便要另外加钱,当下就可起火点窑。没有主顾上门时,梁师傅便在店中闲坐,沏一壶茉莉花茶,慢慢地细饮,或有滋有味地哼着戏文,或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街上的各种叫卖声。
东大街口的菊花胡同里,住着一位唱戏的先生,名叫张得泉,这一年四十岁出头儿。张先生是唱河北梆子的,是那年间保定的名角儿,他手里有一个戏班子。街人都尊敬,称他张先生,或者张老板。梁宝生听过张先生的戏,爱听,而且上瘾。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梁宝生是张得泉的铁杆“粉丝”。
那天,张得泉进了瓷人梁的店铺。梁宝生抬眼一搭,目光就亮了,忙放下茶壶起身,拱手迎了,笑呵呵地说:“张先生来了,小店生辉了。”张得泉也抱拳寒暄了一句:“梁老板,客气了,客气了!”撒开眼睛在店里货架上闲逛,梁宝生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搭讪:“张先生喜欢这个?”张得泉点头,悠悠地说:“真是喜欢。只是听人讲,今天头一回来,果然不错。”说着,便回过头来,看着梁宝生,笑道:“劳烦梁老板,给我捏一个像如何?”
虽是初冬时节,街上的阳光却很好,无数阳光漫进店里,店里亮亮堂堂,梁宝生很阳光地笑笑:“谢谢张先生照顾,只是价钱很贵。”
张得泉摇头笑笑,略带讥讽地说:“着实贵了些,梁老板岂不知,一分利撑死,九分利饿死?这等价钱,能有几个主顾上门呢?莫非你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梁宝生稳稳地一笑:“张先生说笑了,梁某的店铺,小本经营,能够哄饱全家的肚皮,就算勉强了,岂敢奢望流水般挣钱。再者,梁某也不想把祖上的手艺卖低了。”
张得泉诚恳地说:“我的确喜欢,梁老板,还还价钱如何?”
梁宝生摇头说:“张先生啊,如果您真的喜欢,就不应该在乎这个价钱么。”
张得泉商量的口气:“您开口言价,我就地还钱么。”
梁宝生继续摇头:“真的不让。小店生意言无二价。”
张得泉的目光就涩了:“唉,那您这买卖怎么开啊?”
梁宝生认真地说:“不瞒张先生,梁某就是给那些有钱人开的,并不想赚穷人的钱。”
张得泉笑问:“您看我是有钱的主儿么?”
梁宝生双手一摊:“张先生啊,您这话可就透着不实在了,您是名角啊,唱一出得多少大洋?怎么会没钱呢?您还养着一个戏班儿呢。”
张得泉无奈地摆摆手,笑道:“行了,行了,我不跟您扛嘴了。就按您说的价钱,给我捏一个吧。”
梁宝生便让张得泉坐下,重新沏了一壶茶,给张得泉斟了,去店后边取出了窖泥,在张得泉对面坐了,与张得泉说说笑笑搭着闲话,眼睛却细细瞄着张得泉,手里更是紧忙活着,一支烟的工夫,给张得泉捏好了一个像,放到了桌上,张得泉仔细看过,连声叫好。梁宝生又细细地收拾了一番,就算完成了。二人便说定,三天之后,烧成瓷人,张先生便来取货。张得泉放下定金,便走了。
三天之后,张得泉派跟包儿的小刘来取货。梁宝生把烧制好的瓷人用草纸仔细包裹了,装了盒子,又扯了纸绳儿,十字捆扎了,对小刘说:“转告你们张老板,我今天晚上请他吃涮羊肉。”
小刘回去捎了话。张得泉撇嘴一笑,没有当回事儿。他觉得梁宝生就是一个黑下心挣钱的生意人。涮羊肉的事儿,也就是嘴上说说。谁知道,到了晚上,张得泉散场的时候,梁宝生竟在剧场后台的门口站着,正候着张得泉呢。等到张得泉卸了装,走出来,梁宝生忙迎上去,拱手笑道:“张先生,我答应过您,今天晚上请您吃涮羊肉。东来顺的馆子我已经定下了。”
张得泉愣怔了一下,就笑了:“梁老板啊,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呢?”
梁宝生认真地说:“我说过的,请您吃涮羊肉。我知道您好这一口儿啊。”
张得泉听出梁宝生是真心实意,便随口笑道:“也行啊,您赚了我的钱,自然要请我一顿儿了。”
梁宝生笑道:“那咱们走着?”
张得泉爽快地答应:“走着。”
二人便去了保定东来顺,东来顺的老板已经留好了雅间。老板姓马。张得泉笑道:“马老板啊,您这买卖挣了白天,晚上也不歇着,还有夜宵啊?怪不得您发财呢。”马老板很商业地笑了笑:“这不是梁老板订下的桌么,马某敢不伺候吗?张先生,甭取笑我了,您里边请吧。”
进了雅间,只见桌上的木炭火锅已经点燃,马老板将香菇、虾仁、枸杞子、红枣、姜片等放进锅中,桌上已经摆好几盘上好的羊肉,另有麻酱、辣酱、韭菜花、酱豆腐,葱姜蒜末等小料,一应俱全。还有一坛陈年的山西汾酒。
张得泉拿起汾酒,打量一下,笑道:“马老板,你也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儿?”说着,就启开了酒坛,浓烈的香气就冲撞了出来。
马老板嘿嘿笑道:“哪里哟,这些都是梁老板吩咐的。”
二人相对坐了。梁宝生捉起那一坛酒,斟满了两只杯子,笑道:“张先生今晚只管畅饮,酒钱么,梁某断不会皱眉。”
张得泉笑了,端起酒杯:“好!好!来,干了这杯!”
窗外冬夜沉沉,北风猎猎。屋内二人吃得热火朝天。
一坛酒吃尽,二人放了筷子,梁宝生眯缝着眼睛笑道:“张先生,吃得怎样?”
张得泉抓起桌上的热毛巾,擦了擦脸,大笑:“大块朵颐,痛快淋漓啊。”
梁宝生接上一句:“那明天我还请您,如何?”
张得泉哈哈笑道:“当然最好,张某吃得上瘾了。”张得泉认为梁宝生客气一下就是了,谁知道,第二天晚上,他刚刚卸了装,正端着小茶壶喝茶呢,小刘就跑来告诉他:“张先生,瓷人梁在外边等着呢。说今晚还是请您去吃涮羊肉。”张得泉怔了一下,忙放下茶壶,起身出来。果然,梁宝生正在门口站着呢。张得泉连连摆手道:“梁老板啊,您也太客气了。我不能再吃您了。”
梁宝生笑了:“您昨天可是答应了,您可不能爽约啊。”
张得泉苦脸说:“哎呀,我只是一句玩笑,您怎么当真了?”
梁宝生认真地说:“我可没听出您是玩笑。”
张得泉只好点头:“好,咱们走着。”
于是,梁宝生就又请张得泉去了东来顺。吃过之后,梁宝生笑道:“明天我还得请您。”张得泉笑道:“您不会有什么事情求我吧?梁老板,我张泉人可就是个唱戏的,大家捧我,我就算是个角儿,大家不捧我,我就是臭狗屎。我无职无权,什么事情也办不了的。您如果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梁宝生笑道:“张先生啊,您放心,我并无事情求告于您。您就放心吃。”
张得泉呆呆地看着梁宝生,突然也来了兴趣,他真不明白梁宝生为什么总请他吃饭。就笑道:“您的意思是……咱们明天……继续吃?”
梁宝生认真说道:“当然要吃!吃!”
张得泉击掌笑道:“吃就吃!”
第三天晚上吃过,梁宝生又要定下第四天,张得泉却是高低不肯了:“您为什么总请我吃饭?否则,明天开始,我一连请您三天,这三顿涮羊肉,我一定得让您吃回去。要不然,我睡觉都不安稳了。”说到这里,张得泉目光狡黠地盯着梁宝生。
梁宝生噗嗤笑了:“张先生啊,您一定想多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那瓷人么,本是个手艺活儿,卖高卖低,只由我说了算。那天我不还价,只是我不愿意降低价格。您一再要求,我看出您的意思了,您是真想买,可是我既然说了,就不能降价了,您的面子就伤了。我这心里就不好意思了,只好请您吃几顿饭,这饭钱么,就抵了那瓷人的价钱了,就算是我退给您钱了。我还落一个陪吃。这么算来算去的,还是我占您的便宜了。”
张得泉听得直摇头:“哎呀,梁老板啊,这就不对了么,您讲的这不是道理么。您做的是生意,您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您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这样一来,张某倒不好意思了哟。”
梁宝生认真地说:“还有一句,我还没说呢。您有所不知,我是您的戏迷啊。您想啊,这天底下,哪有戏迷不捧角儿的呢?”
张得泉听得点头:“如此说,我也真应该请您吃一顿了,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您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您如果不吃,那也行,我得请您白看三天戏。”
梁宝生摇头:“不行,我知道,您的戏票贵,前排坐是十块大洋一张票。我不能占您这个便宜。”
张得泉坚决地说:“不成,我都依了您三回了,您总得依我一回,我一定得请您看戏。”
梁宝生无奈地说:“如果这样,我就再白送您三个瓷人。”
张得泉怔了一下,哈哈笑了:“戏换瓷人?一言为定!”
“瓷人换戏,一言为定!”
由此,张得泉与瓷人梁交上了朋友,二人便是来往走动了。张得泉没戏的时候,便来“瓷人梁”闲坐,找梁宝生喝茶聊天儿。满条街都知道瓷人梁结交了名角儿张得泉。
那天,张得泉的表弟曹正文来张得泉家串门儿,曹正文是保定府的秘书长,此人处世有些霸道,官声不大好。张得泉心中看不起他,面子上却也不好得罪。张得泉近些年在保定唱戏,也依仗了曹正文的保护,都知道他是曹秘书长的表哥,白看戏的很少。城里的地痞无赖,轻易也不敢找张得泉的麻烦。张得泉常常自嘲,说这个表弟只是他餐桌上的一块臭豆腐。气味不好,下酒佐餐却是可口得很。
曹正文看到了张得泉书架上摆放的几个瓷人,曹正文喜欢收藏,年头儿久了,颇是长了些眼力,他欣赏了一番,叹道:“表哥啊,都说‘瓷人梁’的东西好,我只道是个虚名儿,今日一看,倒是叫我青眼相看了。这几个瓷人,不仅捏制得妙,烧得火候也妙,颜色变化得也妙。可说是妙趣横生,妙不可言啊。”
张得泉笑道:“表弟啊,不必如此夸奖了,您要是喜欢,您就挑拣两个拿走。”
曹正文摆手笑道:“君子不夺人之美,我明天去买几个就是。”
第二天,曹正文便去了“瓷人梁”,一问价钱,却皱了眉头。他对梁宝生道:“梁老板,且不说曹某是政府秘书长,我也是张得泉先生的表弟啊,您总要给我些面子吧?价钱上您一定得让一让。”
梁宝生笑道:“曹先生啊,梁某怎么能不知道您是大名鼎鼎的秘书长呢,我当然也知道您是张先生的表弟。可这与您买瓷人是两回事啊。这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闲情逸致,如果您有这份儿闲钱,您就没有必要跟我讲价钱。如果您没有这份闲情,您何苦花这个钱呢?情知,我开得是买卖,我得指望着它吃饭呢。曹先生啊,真是对不住您了,小店不还价钱。”
曹正文无话可讲了,便来找张得泉,让他去找梁宝生去讲价钱。
张得泉摇头说:“表弟啊,莫怪梁老板不给你面子,人家指着这玩意儿吃饭呢,我怎么好去跟他压价呢。”
曹正文不高兴了:“我也就是看着‘瓷人梁’是表哥你的朋友,才不好为难他的,我若是耍起蛮来,白拿他几件,他有何话讲?我来求你,也是给你的面子,更是给他的面子。”说到这里,曹正文的脸色就阴沉了。
张得泉没词儿了,摆手苦笑道:“行了,行了,表弟啊,如果你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得了,我就破一回规矩,去跟梁老板说说。”
转天,张得泉对曹正文说:“得了,我说好了,你就去吧。梁老板低价钱给你做十件货。”
曹正文非常高兴,就到了瓷人梁的铺子,说明了情况,就订做了十件货。
取货那天,曹正文笑道:“梁老板,我真的有些不明白了,我那天跟您还价,您咬定不让,如何我表哥来说了,您就低价做了这十件呢?莫非我这秘书长的身份,真赶不上我表哥的名声么?”
梁宝生淡淡地说:“曹先生啊,您如果不问,我也就不说了,因为张先生不让我讲。您一定要问,我就告诉您了,您还下的价钱,张先生已经替您付过了。我这生意,也不怕您笑话,梁某只认顾客,只认价钱,从来不认朋友,比如张先生;也不认长官,比如您曹秘书长。为什么?如果都认下来,梁某这买卖就开不下去了,一家大小就要喝西北风了。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呢?”说到这里,梁宝生抱拳道:“梁某小器,让您见笑了。”
曹正文的脸就涨红了,尴尬地笑笑:“说的是了,是了。”
张得泉后来知道了,就叹道:“梁师傅啊,我这位表弟你不好得罪啊!”
梁宝生笑道:“张先生啊,有您这位表哥,那曹秘书长怎么好破脸来找我的麻烦呢?他或许成了我的老主顾呢。”
张得泉一怔,哈哈笑了:“宝生啊,你真是……哈哈!”
真让梁宝生说中了,曹正文果然就常常来“瓷人梁”,定制瓷人,再不还价。
春雨蒙蒙的一个下午,街上稀少了行人,张得泉来到了“瓷人梁”,进门就说:“宝生啊,有人送了一包‘雨前’,咱们品品味道。”梁宝生也笑道:“好极了。”就把店门关了,烧了一壶水,二人把茶沏了,细听着满街的雨声,对坐着聊天儿,正聊得兴致浓厚,店门一推,进来了一个青年男子,高个头儿,粗眉毛,大眼睛,他收了手里的油纸伞,伸到店门,抖擞了一下雨水,再把伞立在了墙角,拱手问:“我找梁宝生师傅。”
梁宝生急忙起身迎了:“我就是梁宝生,不知先生?……”
青年连忙自报家门:“梁师傅,我是您的同乡,名叫丁也成。我是德州深县李县长的亲戚,是他介绍来的。”然后就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了梁宝生。
梁宝生细细地看罢了信,眉头皱紧了,眯缝着目光,认真打量了一番丁也成,旋即,他的脸上又非常热情起来,请丁也成坐下喝茶,又把张得泉引见了,然后笑问道:“是啊,李县长是梁某的表亲。既然您是李县长亲戚,自然也就是梁某的亲戚了。他推荐您来,您就不用客气了。不知丁先生找梁某何事?”
丁也成说:“梁师傅,晚生此来,是要跟您学手艺的。”
梁宝生对张得泉呵呵笑道:“张先生啊,您看,梁某还真是有了些薄名。”又问丁也成:“丁先生在保定可有亲朋好友?食宿如何打理?”
丁也成脸微微地红了,不好意思地说道:“除了您之外,保定并无亲戚了。我也是初来保定,一路打问才找到这里。昨天夜里,在车站的客栈里住了。”
梁宝生哦了一声,点头笑了:“既然是李县长介绍您来的,我便同意了。您若是没有住处,就搬到店里来住吧。夜里,也好替我看看店。”
丁也成高兴地连连鞠躬:“本以为梁师傅不肯收徒,如此一看,梁师傅果然大度。我这就回客栈收拾行李,就搬到店里来吧。”
梁宝生笑道:“丁先生去吧。”
丁也成答应了一声,撑起油纸伞,匆匆地出门走了。梁宝生并未起身,只是虚着目光,送丁也成出了店门。张得泉疑惑地问:“宝生啊,我可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有李县长这么一门亲戚啊?再者,我看你刚刚的言谈话语之间,似有些夸张,用我们的行话讲,您的戏演得过了。这其中莫非有诈……?”
梁宝生笑了:“张先生啊,您果然神目如电,我哪里有什么李县长的这门亲戚,我只有过一位姓李的表哥,在县里做过几天的师爷,也已经去世多年了。想必这位丁也成不知道此事,他只是望风捕影,冒名来的。”
张得泉惊了脸:“如此说,这封信是伪造的?难道你看出了?”
梁宝生苦笑道:“我如何看不出,当然是假的了。”
张得泉拍案而起:“宝生啊,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诈骗,你何不将他送到局子里去呢?我这就去找警察来,捉他就是了。”
梁宝生忙拦住张得泉,摇头笑道:“且慢!且慢啊!张先生啊,且听我说,即使您把警察喊来了,警察又能如何处置?他丁也成诈骗我什么了?不就是一封假信么,我若不认,他便说找错人了,我还有何话说?”
张得泉口吃了:“这……”却又怒道:“至少你也不应该收留他啊。”
梁宝生摆摆手:“张先生,莫急,实话实说,我委实有些投鼠忌器啊。我刚刚仔细看过这封假信,语句通顺,字迹灵秀,他有这种手段,造假肯定是一流水平,即使送到局子里,关上些日子,放也就放了,他还要到别处招摇撞骗。我思想了一下,莫不如让他跟我学习这个烧瓷的手艺,我也认真教他,捎带着也教授他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免得他出去造假,危害市井啊。张先生啊,您岂不知小人有才,祸国殃民啊。或许我教他一段时间,他也能改了些心性,那世上便是多了一个手巧的工匠,少了一个有才的小人啊!”
这一席话,讲得张得泉呆住了,好一刻,他感慨地长叹一声:“宝生啊,你果然是一个有心的人啊,张某自愧不如了!”
丁也成就留在了“瓷人梁”,跟着梁宝生学烧瓷的手艺。
日子像水一样流着,一年过去了,梁宝生悉心教授,丁也成努力学习,捏出人像来,竟然也是惟妙惟肖了。
那一天,梁宝生说:“也成啊,你已经跟了我一年,你是一个聪慧敏捷之人,我这手艺,你已经学得青出于蓝,你可以出去自立门户了。”
丁也成听了,脸上便流露出依依的表情:“师傅啊,可是……我并不想走啊。”
梁宝生笑道:“天高任鸟飞么,你怎么能一辈子留在我这小店里呢。走吧!大丈夫志在四海,怎可拘泥一隅呢。”
梁宝生的话讲得决绝,丁也成不好再坚持,便在保定饭庄摆了一桌酒席,答谢梁宝生一年来的教授之恩,并请求师母并师弟都来赴宴,却被梁宝生推辞了:“也成啊,你师母从不出头露面,你师弟年纪尚小。若是过来,便要搅了酒兴。”丁也成便要求请张得泉先生过来坐陪。梁宝生点头笑道:“如此最好!”
保定饭庄坐落在莲池东岸,饭庄四周,杨柳依依,春色非常可人。三人进了饭店,便在雅间坐了。三杯酒过后,张得泉笑道:“日子真似打了飞脚啊。去年似乎也是这个时节,也成来‘瓷人梁’拜师学艺,转眼竟是一年过去喽!”
丁也成羞涩地一笑:“其实,我瞒过了师傅,今天徒儿要走,便要实话实说了,我并不是李县长的什么亲戚。也并不认识什么李县长。李县长的那封信,其实是我仿写的。”
梁宝生哦了一声,木木地看着丁也成,神色茫然不知就里。
丁也成叹道:“师傅啊,您为人纯朴仁厚,君子品行,我真不应该欺以其方啊。今天想来,也成还是羞惭的很啊!”
张得泉忍不住了,哈哈笑起来:“也成啊,你以为你师傅呆么?他本来就知道你是假冒的。只是他看你心灵手巧,敏捷聪慧,他才收下你的。这一年来,你师徒二人朝夕相处也有了情谊,你这番话但说出来,也就无妨了。”
丁也成惊异地看着梁宝生:“师傅啊……”
梁宝生笑道:“一个手艺上的事儿,你学了就是。不说这个了,喝酒!喝酒!”
丁也成惊讶了一下。脸就腾腾地红了。
梁宝生喝了一口酒,笑道:“也成啊,世间的手艺么,都是磨心性的事儿。我也希望你学了这一年,便是改了性格。人生在世,还是要诚实为本啊。”
丁也成长叹不已,他说:“师傅啊,也成自当铭记了。”
张得泉举杯笑道:“说的是,说的是啊!来,都过去了,喝酒!”
谈兴浓厚,酒就吃得多了,一直吃到太阳西斜。丁也成饮罢了最后一杯酒,神情庄重,起身说道:“青山不倒,绿水常流,日后也成发达了,再来看望师傅与张先生。”
梁宝生拱手笑道:“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也成啊,我观你气色不俗,将来必定有一番人生造化,你就安心做事,不要将梁某挂记在心上了。”
三人走出酒店,丁也成跪下,向梁宝生磕了三个头,拾起身,又朝张得泉抱拳拱手:“张先生保重!”便踩着满街的夕阳大步走了。
张得泉望着丁也成的背影,笑道:“宝生啊,此人将来定有一番结果。”
梁宝生望了望渐渐涌上来的层层暮霭,摇头一叹:“张先生啊,我也愿意这样设想,可是,这茫茫世间,从来都是九分人算,一分天算。两者之间,谁又能说得确凿呢?”
又一年,日本人举着膏药旗,牛哄哄地开进了保定,梁宝生就不再做瓷人的生意,把店铺关了,每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瓷盆瓷碗的生意了。张得泉也不唱戏了,戏班子也解散了,就靠着典当家底过活了。曹正文也不知去向了。日子变得蔫蔫的一片死色。
花开了,花落了,下雨了,下雪了……又过了八年,日本人匆匆地卷了膏药旗,灰灰地走了。“瓷人梁”的店铺丁丁当当地放了一通鞭炮,又开张了;张得泉的戏班子锣鼓喧天,又重新唱戏了。曹正文也回来了,八年不曾露脸,他竟然加官晋爵,做了保定的副市长。他上任第二天,就请张得泉与梁宝生吃了一顿酒。三人嘻嘻哈哈,喝得大醉而归。
日子似乎又变得明朗快活了。可是,人间的日子总是像天气一般,阴晴不定。再一转眼,就到了1948年春节。国共两党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保定的街面上,也显得乱哄哄起来了。有人私下说,国民党支撑不了多久。街面上的物价,涨成了孙悟空,一天就能有七十二般变化。梁宝生的生意就做得潦潦草草,张得泉的剧团也唱得半死不活。二人常常在“瓷人梁”坐着闲聊,或感慨,或感伤,或感叹。那一番灰凉情绪,直是冷到了骨头里了。
那一天,曹正文突然派人到“瓷人梁”,请梁宝生到市政府去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商量。梁宝生本想推辞,可是看到来的人都是横眉立目的士兵,便知道不去是不行了。此时的曹正文,已经升任了保定市长。梁宝生便到了曹市长的办公室。曹市长寒暄了两句,便开门见山,要梁宝生做三个与真人高低相似的瓷人:福禄寿三星。曹正文解释说,这象征着国泰民安。
梁宝生苦笑了:“国民党都这样了,还能国泰民安么?曹市长啊,您真是讲笑话了。”
曹正文干笑道:“梁师傅,您是一个买卖人,只管做你的生意即是。莫谈什么国事了。这单生意是政府出资,放心,亏不了您的。”
梁宝生摇头:“曹市长啊,这乱哄哄的世道,梁某也无心挣钱了。”
曹市长怔了一下:“听梁师傅的话音儿,是不肯做这单生意了?”
梁宝生郑重地点头:“不瞒曹市长,梁某是这个意思。”
曹正文嘿嘿冷笑了:“梁师傅啊,如果您不做,全市的瓷匠们都要受您的连累,都要以通匪论处。”
梁宝生皱眉问:“通匪?怎么处置?”
曹市长冷笑:“枪毙!”
梁宝生惊讶道:“枪毙?”
曹正文点头:“枪毙!”
梁宝生一下子仰靠在椅子上了,正值干旱天气,窗外万里无云,连风也没有一丝,梁宝生能听得到自己乱乱的心跳声。良久,他长叹一声:“唉,曹市长啊,如你这般说辞,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呢?”
曹正文嘿嘿笑了:“梁师傅,您不明白啊,我就是公理啊。”
梁宝生脸白白地,悠悠地叹了口气:“您说的是啊!您就是公理啊!行了,行了,我答应您了,您还是把抓来的工匠都放了吧。”
曹正文摇头笑道:“这可不行,您想啊,我若放了他们,您食言了,我怎么办?再者,他们也能给您搭搭下手啊。什么活泥啊,熟料啊,垒窑啊,等等,这些事儿总得有人干么。行了,您就上手吧。完工之后,我立刻放人。”
梁宝生就带着二十几个烧瓷的工匠,在保定西关垒起了一座瓷窑。
工匠们就运来了保定完县的黄土,梁宝生亲自验过,点了点头,工匠们便开始搅拌泥坯,三天过后,泥坯做成了,梁宝生看罢,用鼻子嗅了嗅,摇了摇头,让工匠们再加工。于是,工匠们再奋力搅拌。又三天过去,梁宝生看罢,说:“行了!”就开始捏制瓷人,一直捏造了七天,期间不断修修补补,三个瓷人便是捏作好了。又晾了十天,梁宝生便开始彩绘。
曹市长那天亲自来督促,站在一旁看梁宝生彩绘,苦笑道:“梁师傅,您好可是要快一些了,解放军就要打到保定市了。”
梁宝生指了指三个正在着色的泥胎,苦笑道:“曹市长啊,您急,可是它们却偷不得工夫啊。”
一共彩绘了五天,烧窑点火了,梁宝生就坐在窑旁指点工匠们料理火候。时而文火,时而武火。半个月过去,梁宝生就在窑旁枯坐,他的胡须已成灰白的颜色了。那天,他耳朵附近了窑,细细地听了一刻,便让工匠熄火。他又在窑旁守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伸手拍了拍窑壁,用早已经涩枯的嗓子喊了一声工匠们:“起窑吧。”
众目睽睽之下,三个瓷人出炉了,入窑前的彩绘完全变了颜色,三个瓷人栩栩如生,神采奕奕地站在了众人面前。阳光之下,三个瓷人微笑得十分灿烂,似乎要拔步就走的样子。众工匠看得眼呆,好一刻,有人带头喝出一声彩:“好品相!”
曹正文市长也来了,他就在一旁直直的目光看着,嘴张着,一句话也讲不出了。终于,他涩涩地说了一句:“果然是瓷人梁,神品啊……”
梁宝生近乎迷离的目光,呆呆地看着那三个瓷人,终于,他如释重负,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这一个多月,似乎用尽了他一生的力气,好一刻,他摇了摇头,长叹一声:“浑然天成,似有鬼神造化,可惜了,你们却不得其时啊!”
曹市长满意地笑了,摆了摆手,放了全城的瓷匠。三个瓷人被小心地装了箱子运走了。
全城的瓷匠摆下宴席,答谢梁宝生的出手相救之恩,张得泉也被请过来坐陪。
梁宝生闷闷地喝过了几杯酒,长叹道:“这三件东西,怕是回不来了。”
张得泉苦脸说:“宝生啊,我也不瞒你,正文已经举家迁到了香港,他要在香港做生意,这三件东西,他一定要弄到香港去的。我这个表弟哟……唉!宝生啊,可惜了你的手艺,竟被正文中饱私囊了。”张得泉一劲儿摇头叹息。
梁宝生苦笑:“张先生莫要自责了,曹市长的心思,我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全城瓷匠的性命,我也只好如此了。”
张得泉问:“宝生啊,难为你了啊。”
梁宝生苍凉一笑:“张先生,我一生捏造烧制瓷人无数,唯有这三件瓷人是我的得意之作,眼见得它们离我而去,心中便是一种悲凉的滋味啊。我自看天命,也不过再有十五年的光阴,我死之前,仍然见不到这三件东西归来,那三件东西便有缝隙之虞啊。”
张得泉一怔:“宝生啊,你这话中似乎有话啊?莫非藏有什么机关?”
梁宝生叹道:“不提也罢了……”泪就落下来了。
宴席间的气氛压抑,酒吃得沉闷,梁宝生喝得泪流满面。
众人摇头叹息不已。
又过了几个月,保定城外的枪炮声急骤了。一夜起来,保定城里已经全是解放军了。曹市长早已经不知去向了。由此,保定解放了。梁宝生仍然做他的生意,张得泉仍然唱他的河北梆子。日子匆匆忙忙地过着,1954年春天,保定市的工商界大张旗鼓地开展公私合营的运动。先是张得泉的剧团,合并进了保定国营河北梆子剧团,张得泉任副团长,当年,张得泉被评为保定市劳动模范。1959年,张得泉已经七十岁,便谢绝了剧团的挽留,退休了。梁宝生的店铺,也于1954年合并进了保定市第一国营瓷厂。梁宝生在厂里做技术指导,并被评为高级技师。如此匆匆又过了十年,就到了1964年春天,梁宝生感觉身体不好,就写了份申请,光荣退休了。退休之前,瓷厂鉴于梁宝生这些年的贡献,评选他当了保定市劳动模范。
1964年的秋天,已经退休的梁宝生接到了从新加坡寄来的一封信,信是由市委统战部转来的,打开一看,竟然是丁也成写来的,丁也成竟然成了东南亚一带著名的收藏家,现在新加坡居住。他写信来,是邀请梁宝生师傅参加他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瓷器收藏展。双程机票及食宿等等费用,都由丁也成承担。市里的同志问梁宝生是否有意去一趟。梁宝生愣怔了一下,凄然一笑:“谢谢丁先生的好意了,我已经是近古稀之年了,就不想动了。”
这年的冬天来得早,风吹得紧,梁宝生先是得了一场感冒,总不见好,就住进了医院,检查了一番,竟然是绝症。张得泉去看望他,二人执手无语,泪眼相对。挨到最后,张得泉涩涩地问梁宝生:“宝生啊,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梁宝生叹道:“张先生啊,您还记得那三个瓷人么?”
张得泉点头:“怎么不记得,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三件瓷人的下落呢?”
梁宝生道:“是啊,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烧品了。”
张得泉长叹一声:“是啊,你当年说过的。可惜了,被我那无良的表弟饱了私囊。唉,宝生啊,是我累及了你啊……”
梁宝生摆手:“张先生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还记得我说过,十五年后,那三个瓷人会有裂隙吗?”
张得泉点头:“是啊,你当年没有细说,我也不好打问。你怎么知道它们会在十五年之后出现裂隙呢?”
梁宝生苦笑道:“当年我做那活儿时,心存愤怒,便是偷减了工料,我已经料定,这三件瓷人,不得久长啊。”说着便从枕头下边取出一个小盒子,打开之后,取出一个纸包,那纸包年深月久,已经泛出黄斑,梁宝生打开,里边有三块墨色的东西。梁宝生递给了张得泉,张得泉接过捏了捏,感觉坚硬如铁,仔细去看,竟是三块泥丸。
张得泉惊讶:“宝生啊,这是……?”
梁宝生道:“这便是我当年偷工减料下来的三块熟泥啊。”
张得泉惊得呆住了:“你的意思是……”
梁宝生淡薄一笑:“十五年已经过去了。既然管不了身前,怎么顾及得身后?张先生啊,您好自为之。”说罢,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张得泉慨叹一声,呆坐了一刻,就起身告辞。又过了五天,梁宝生在医院去世。这一年,梁宝生六十八岁,距离他讲过的十五年的话,刚刚过去一年。
再一年,保定河北梆子剧团应观众的热烈请求,邀请张得泉在保定迎五一文艺晚会上,登台演出河北梆子现代戏《节振国》。张得泉痛快地答应了,粉墨登场,却在台上突发脑溢血,送至医院,不治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出殡那天,几千名戏迷闻讯赶来,洒泪送别,张得泉先生身后如此殊荣,若是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
再一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梁宝生的儿子梁向明女儿梁小红被戴了高帽子游街,其中有一个罪名,便是其老子梁宝生是反动权威,为国民党反动派曹正文捏造烧制封资修的人物,罪该万死。梁宝生的劳动模范称号被剥夺。张得泉的两个儿子张可飞张可扬也被揪出去批斗,其中一个罪名,便是其老子张得泉为国民党反动派曹正文唱戏,罪该万死。张得泉劳动模范的称号也被剥夺。两家的孩子,都充当了父债子还的角色。
……
话说曹正文去了香港之后,市长自然做不成了,他在香港开了两处古董店铺,买卖还算兴隆。他由内地运去的几百件瓷器,很快都以高价出手,曹正文很是挣了一笔。只是那三个瓷人,他割舍不得,摆在家里欣赏。有人知道了,便来观赏,看过之后,便说出高价买走。曹正文坚决不卖。却也真是应验了梁宝生的话,果然在十五年之后,即1963年春天,那三个瓷人的眼睛突然有了裂隙,曹正文着急,眼见得裂隙有漫延的趋势,他便请来香港的一些古董专家,想求教一些补救措施,可是众人看过之后,都表示无能为力。曹正文叹道:“这三件宝物如何是好呢?”于是,他就把这三件瓷人放进了内室。不再让人参观了。
转眼,又过了十几年,香港回归的消息越传越烈了。曹正文便有了回乡之心。
又有一天,一个名叫丁也成的收藏家来香港,找到曹氏开的古董商店。经理是曹正文的大儿子曹柏青,丁也成要求拜访曹正文先生。曹柏青与父亲联系了一下,曹正文答应了。
曹正文在自己的别墅接待了丁也成,曹柏青就在父亲身旁侍立。丁也成与曹正文寒暄了几句,便说:“丁某此次来府上,是想参观一下曹先生收藏的三件瓷人。不知方便否?”
曹正文怔了一下,就笑了:“丁先生如何知道这三件瓷人?”
丁也成笑道:“我是搞收藏的,当年保定大名鼎鼎的‘瓷人梁’,给曹先生烧制了三个人高的瓷人,也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曹正文的脸微微一红,摇头笑道:“不瞒丁先生,当年曹某年轻,一时把持不住贪婪之心,也就起了夺人之美的念头,便做下了这件恶事。现在思想起来,也确实对不住梁老板了。”便带丁也成去内室观看。
灯光之下,三件瓷人鲜活如初,仍似刚刚出窑的样子,丁也成细细地看罢,叹道:“果然是梁师傅的上品啊,只是……如何……三件瓷人的眼睛都裂了呢?”
曹正文摇头:“或许是当年梁先生对曹某的情绪恶劣,便影响了手艺,工序上便是做得不精当了。”
丁也成苦苦一笑:“梁宝生师傅乃一代高人,手艺上断不会出此低等错误,怕是另有所故了。”
曹正文哦了一声:“丁先生或许看出什么了?”
丁也成细细打量了一番三个瓷人,点头道:“据我看来,这三件瓷人烧制之前,也就是捏造之时,用料不均,一代能工巧匠,何以偷工减料?或许如曹先生所说,是梁师傅对您心有不满所致啊!”
曹正文点头叹道:“丁先生说的有理啊。”沉吟了一下,又问道:“如何办呢?”
丁也成叹道:“我也不知办法,只是听说,如果有好的锔匠,便可补救。”
曹正文再问:“哪里有这样的好锔匠呢?”
丁也成摇头说:“香港弹丸之地,断无此高人啊。如果锔好此活,曹先生还得回内地啊。再者,这三件宝物也应该落叶归根了啊。”
丁也成叹息着走了。
曹正文送丁也成出来,望着丁也成远去的背影,他对曹柏青说:“柏青啊,香港回归之时,我们便将这三件东西运回去,找能工巧匠锔上。是啊,丁先生说得对啊,它们也应该落叶归根了哟。”
曹柏青连忙点头答应。
曹正文怔了一刻,又仰头望天,天空一片阴霾,似有大雨将至。曹正文叹息道:“只是,内地能有如此手段的锔匠吗?”
曹柏青张张嘴,不知道如何作答。
这一年秋天,曹正文突发心梗,在寓所去世。终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