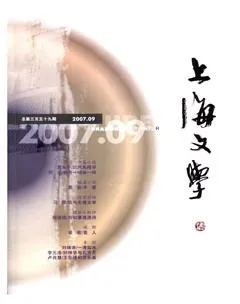王尔德和莎乐美
一年前一个午夜,记得是深秋初冬,纽约街上无人无车,雨在路灯底下,大得像把纽约浸在了水里。那天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奥斯卡·王尔德书店。书店自是打了烊,昏黄的灯光从木格的门和排列了书的窗户背后慵懒而散漫地透出。
奥斯卡·王尔德纪念书店,世界上最早的同性恋书店,于1967年开始营业。
那书店传递着某种神秘,这于我是雨夜的神秘,还是王尔德的神秘,我不甚明了。很小的时候看过翻译的《道连·葛雷的画像》,在记忆中只留下一幅承恶而变丑的画像,而那张施恶的脸永远那么年轻漂亮。葛雷说,“如果我能够永远年轻,而让这幅画像变老,要什么我都给!……我愿意拿我的灵魂去交换!”
那个总在衣领上别一枚鲜花的爱尔兰作家在一百年前这么写。而我则在2004年12月的深夜想起这些零星的片段,走出克里斯多弗街,走过6大道,去坐地铁回家。我的皮鞋饱吸雨水,一路吱咕吱咕地响。
这是夜里了;现在一切喷泉高声絮语。而我的灵魂也是一道喷泉。
这是夜里了;现在一切爱者的歌声醒起。而我的灵魂也是一位爱者的歌曲。
克里斯多弗街是一条有意思的街,每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同性恋、凑热闹的异性恋,还有警察轰轰烈烈从5大道游走到此,然后聚于那条小街上,聚于王尔德书店门前,又唱又跳又喝又闹。1882年王尔德赴美巡回演讲后,写了一段美国印象的文字。他说这个国家没有盛大壮观的游行。他只见过两次,一次是警察走在消防队前面,一次是消防队走在警察前面。他万没有想到现在纽约六月的游行如此壮观,警察和消防队当中夹了许多同性恋。去年克林顿夫人也一起游了过来。这条小街在那个盛日,像要爆炸了似的。我也凑了几回热闹,想着的却是写《莎乐美》的王尔德。
黑夜看一个人同白天看,是不相同的。在那个午夜我撞见的王尔德让我神迷。我开始读这位颓废的唯美大师留下的文字。书信,剧本和小说。他才情恣肆,妙语横生,他的机智轻易得就好像口袋里摸硬币一样。我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把读到的珠玑写在电子信里散发给朋友共享。好东西是要共享的。好酒好菜好文字。
偶尔,下了班我会去克里斯多弗街的书店玩。店堂很小,十几个人一同挤进去,便背肩相擦了。柜台后面总有两个苍白的瘦女子坐着看店,像是鲁迅的豆腐西施。我没有在那里找到王尔德的书,但却总觉得找到了那人,他衣领别着鲜花,支一柄手杖,倚靠门柱,以一种英国人的懒洋洋道,“I can resist anything except temptation.”
去年夏天我在史传德旧书店,花了十块钱,淘到一本DOVER出的插图版《莎乐美》。我记得开始读《莎乐美》是在格林威治街的一个新潮三明治店里,一边看剧本,一边等朋友。那是一位差不多一辈子以法律的严谨一丝不苟地做游戏的纽约人。他见我在读这百年老书,于是说,“颓废。”他在指书,指王尔德,或指这个令王尔德流连忘返的纽约,我不得而知。八月底的时候,傍晚渐长,就像街灯被落日拉得孤零零的影。窗外,恰是纽约流金的黄昏,有生命燃尽之前悲哀而颓废的辉煌。我恍恍然想这或许便是《莎乐美》,是王尔德了。而剧本的奇谲就在那片暮色里向我慢慢展开。
《莎乐美》取材于《圣经·马可福音》:希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施洗约翰在民众中责备希律,希律便拿了施洗约翰,锁在监里。希律在他的生日宴会上要莎乐美为他舞蹈,答应给她任何东西。希罗底挑唆女儿,要了约翰的头。这本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古典报复故事。王尔德则把它写成一个爱欲横流的尘俗爱情故事,而且用大量色彩浓丽的笔墨于爱欲的铺陈(莎乐美对约翰),对缠绵的同性恋情结的细述(侍童对卫队长)。如此玩世地篡改《圣经》当然有犯于英国文坛,他因此招来四方围攻,剧本不得上演。
更让我嗟叹的是作书四君子生命之光怪陆离。
剧作者奥斯卡·王尔德,享年四十五岁,天才而叛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同性恋被监禁,以至英年早逝。该书作序者罗伯特·罗斯,多才多艺,享年四十八岁,是王尔德第一位同性恋朋友,他的生死之交,他们长眠于同一墓穴,鼾息相闻,同一片鲜花在他们的身体上生长。该书插图画家、同性恋者奥伯拉瑞·毕亚兹莱,二十六死于肺病;他才华横溢,他黑白线条的画被鲁迅称誉为“无匹”。该书英文版译者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是王尔德的最爱恨缠绵的同性恋朋友,王尔德为热烈的爱而把《莎乐美》题献于他,也为他下狱继而丧生。
“我什么都能抵御,除了诱惑。”而这无法抵御的诱惑,乃是爱情,莎乐美式的,拿了死神做抵押,换得一吻。爱比死更为神秘难解。莎乐美在死之前如是说。何尝不是王尔德!
而我在新潮三明治店里,看着行色匆匆的人从黄昏里无声走过: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为诱惑所困的,不为诱惑所困的,痛苦的欢乐的,等等。过了一百年,这些热闹难道不是照样又都沉寂了?克里斯多弗街,街上的那爿书店,还有六月里的热闹游行,到那时还会存在么?如果幸运,说不定会有一册《“新”莎乐美》记录眼前的辉煌。
历史会使石头哭泣。我在小说Gilead里读到这句话,仅仅几字,却石头般重。生命,死亡和爱情,一个古老而简单,但永远探讨不出究竟的哲学主题。我想我能够听见石头的哭泣,是因为我自己的存在。而证明自己的存在,那十分简单,只要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块哭泣的石头。
四月份我回上海,与编辑曹元勇先生谈妥了翻译计划。七月底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包括请朋友冰青和晓丹校读。这本书与其他的翻译比较起来,就篇幅而言,自是短得多;但就文字背后给予我的震撼却是巨大的。我无法漠然。译完此书,把辞书,圣经和王尔德的其他参考书一册册插回书架,我希望能把与翻译此书同时走进我生活的沉重一起还给书架上去。其实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2006年7月30日
题图摄影/瑞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