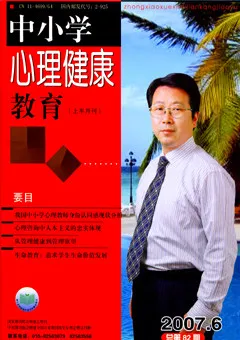从管理健康到管理欲望
关键词:管理;健康;欲望
记得印度有一则寓言,说一个人临死前,上帝会问他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爱过吗?第二是你有过快乐体验吗?第三个是你心平气和地失去过吗?如果这些问题都回答是,上帝则允许这个人进入天堂。我们总是认为人生是加法,快乐和爱等正性的体验越多便越幸福,其实,人生的意义也在于减法,有时学会正确地面对失去才决定了幸福。确切地说,人生是加减法的合理组合。
陈逸飞、高秀敏、傅彪等人的突然离去,使我想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健康管理问题。健康是需要管理的,你爱护自己的身体,它才爱护你。健康管理不能从其字面意义上理解,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防止疾病。在现代社会,健康管理是一种主动的生活态度,是旨在增加生命质量、防止猝死的有效途径,是勇敢地承认人生的衰老、为生命负责任的生活态度。管理健康首先意味着尊重身体的需要,疲劳时,及时休息,听从身体的召唤。其次是要善于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增加对身体状态的敏感性。有些人过于注意身体的疾病的信息,经常感觉自己得病,经常往医院跑,这固然不好,但有些人过于乐观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当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时,仍然不加以注意,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第三是主动选择锻炼身体。有些人认为,经常锻炼身体的人,贪生怕死,贪图长寿。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观念,现代人的锻炼不是为了追求单一的长寿,而是为了防止早死,防止猝死,主动锻炼的目的是为了健康地长寿,而不是简单地为了长久地活着。有些人虽然长寿,但整日病恹恹,失去了生命的质量,这种长寿不是我们所倡导的。
既然健康管理如此重要,为什么有些人、甚至是明智的人不重视它呢?这里就有一个欲望管理的问题。管理健康的前提是管理自己的欲望。在现代社会,欲望的过度满足是健康的敌人。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欲望和需要经常处于匮乏状态,人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发展更多的物质条件,来尽量多地满足需要。传统社会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鼓励人们控制需要、压抑欲望。但现代社会提供了物质需要极大满足的一切条件,人们便忘记了对需要满足的控制和管理,有些人认为欲望必须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可有些欲望最大化的满足就可能给健康带来灾难,如食物的摄取、酒精的过多摄取等。人们观念中仍然不重视对需要的管理,把对欲望管理当作是禁欲。其实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管理是理性引导和合理满足需要,为了身体的健康适时、适当地满足需要;而控制和禁欲则是出于现实条件的无奈而压抑欲望。管理了欲望,就等于管理了健康。
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为了身体健康应当管理较为低级的需要,但对于高级需要的管理则有所忽视。像陈逸飞、高秀敏这种有成就的人,生活在高峰体验中,其自我实现的欲望远远高于一般人。由于在现实世界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相对较少,所以它经常成为人们鼓励的对象。我们常说某某人为科学和艺术献身,是多么高尚的事情,是多么伟大,令人羡慕。自我实现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但是对于知识分子中过于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需要管理的。陈逸飞自我实现的高级需要就缺少有效的管理,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曾写到:“平时大家也知道我做的挺杂的,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各种想法。一是说你在干吗?二是说你犯得着吗?我就说,陈逸飞这个名字后面没有‘画家’两个字,我父母在取名字的时候也没有在后面画一个括号,指明陈逸飞是个画家。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私人的。”这种有才华的人方方面面比别人看到的更多,做得更为出色,但也需要管理一下这些才华和精力。有些自我实现的东西还是要舍弃,舍弃和失去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再说积极的心态。是的,像陈逸飞这种大师级人物,生命质量很高,每天都生活在积极的情绪中,他写到:“我一直乐观,一直兴奋,遇到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就像旅游,晴天固然好,突然下雨了也别有一番风味。一下雨就抱怨,一路玩不好,何苦呢?”这种积极的心态和乐观也需要管理,一个人不能整日都生活在兴奋之中,我们倡导弹性的乐观,不是事事都去兴奋,都去积极投入。该休息时就要休息,一个晒太阳的猫是在浪费时间吗?一个在春风中摇曳的树是在浪费时间吗?管理过度的兴奋,抑制兴奋,有更加广泛而灵活的兴趣,忙里偷闲的人,才是会生活的人。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成功,也不在于一直做事。即使是高级的需要,对自己和人类都是有意义的,也需要管理和引导,合理地满足它们,否则就会透支健康,透支生命。陈逸飞写到:“我没有那么沉重的包袱要做‘大师’,否则我得天天画‘大师’级的作品。我不是用这种心态过日子的。我觉得我很轻松,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问题在于他想做的事情无休无止,而无休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终就不那么轻松了。
我们无权对陈逸飞大师的生活态度和积极的品质加以非议,我们只是在惋惜中提醒人们,有些欲求虽然很美丽、很高尚、很高级,但为了健康的考虑,还是要合理地加以管理。管理欲望就等于管理了健康。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编辑/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