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担负政治使命?
沈 岿
任何公民和组织皆可推动司法解释立项之后,最高院以往悄悄地隐在“法律解释”面纱下的政治使命,被一下子推到了聚光灯之下。
200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史无前例地确立了任何公民和组织皆可推动司法解释立项的制度。
2007年4月2日,也就是《规定》正式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市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熊伟向最高法院提交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就村委会成员被非法撤换、停职、诫免等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做出司法解释》。
2007年8月16日,《法制日报》报道,最高法院已经制定出2007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其中,熊伟的上述建议被采纳、列入计划中。
当像笔者这样一些自诩从法律院系接受正宗法学教育、有着科班出身背景的人,带着“法院的角色就是司法,就是在有人起诉的情况下,独立地、凭着良知和对法律的恰当理解,审理和裁判案件”的知识烙印,去看待最高法院的这—大胆创举时,可能不免会惊讶不已、疑窦频生。
的确,最高法院鼓励任何组织和公民个人“动议”司法解释,以及在起草司法解释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做法,偏离了典型的司法样式——法官正襟危坐、聆听并引导纠纷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依据法律和良知作出裁判。然而,如果我们稍微清醒就能警觉到,关于典型司法样式的映像,可能会产生先入为主的误导作用。超越概念禁锢才能进入更加贴近实际的、关注制度功能的探问。
这一新措施会给最高法院、给中国的农村制度变革、乃至给中国的法治和政治架构,悄悄地捎去怎样的后果?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笔者初步的看法是谨慎乐观的。
中国式司法解释
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无论是个案批复的形式还是制定抽象规则的形式,都或多或少地与典型司法样式错位,并因此受到少数学者的诟病。但是,不可否认,最高法院通过此类解释工作,丰富和扩大了法律的意义空间,在中国的法治甚至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扮演着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个别的解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应该被看作是难以避免的“试错”,而不能整体抹煞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积极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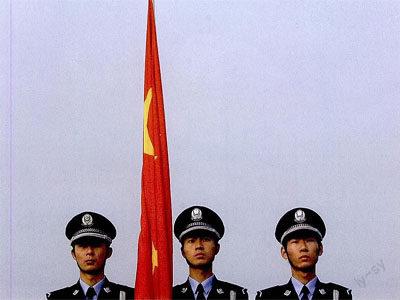
这一积极功能的存在,是有其原因的。现代法学已经揭示,任何国家的立法机关都不可能制定百分之百周详的、覆盖所有问题的、又能紧跟时势变化的、在实务中只需法官照搬适用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只能出自“上帝”或“神灵”之手。在中国,立法机关自身的立法功能尚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而社会仍然在继续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法律的不周延和欠缺更为凸显。在此制度格局中,必须要有那么一些机构,勇敢地拉起“法律解释”的大旗,通过富有智慧的、表面上看起来是逻辑推演的工作,使法律在立法机关未来得及予以补充或修改之前,得以不断地展现其可能具有的意义,机变地解决各式各样的新问题,从而借助法律推动社会变革。
如果说民主制国家中立法是一种多数公民意志的表达、是一种政治活动的话,那么,给法律注入更多血肉、让其更富适用性和实效性、使其更具生命力、为诸多新问题的解决“发现”法律依据的解释工作,也可称得上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使命。只是,这样的政治使命经常躲在“法律解释”的面纱之下,起着“静悄悄的革命”之作用。任何经常运用法律的机构,其实都承担着这样的使命。但是,相较而言,法院是碰到法律问题最多、运用各种法律规则最全面的机构,也是当代法治架构的设计者赋予最终解决各种法律纠纷(包括在对法律理解上的纠纷)的权限的机构。因此,法院的解释无疑是最具广泛影响力的。
在适用判例法制度的国家中,司法解释是在法院裁判文书中显现出来的,并通过判例发挥拘束效力;即使地方法院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裁判不一,最高层级的法院也会通过提审等方式就具体案件作出裁判,并由此确立最权威的判例,借此推行最权威的解释。这样的司法解释,确实与典型司法样式一致。不过,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既然司法解释在许多时候是具有很强政治意义的,是需要法官像立法者那样考虑各方面应当考虑的因素的,那么,以典型司法样式完成的司法解释,就会使法官只能局限地观察特定案情、聆听或阅读特定当事人的意见陈述。当然,法官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广泛汲取案件以外的信息和知识,以最大可能地缓和这一局限,但局限很难彻底克服。
在中国,判例法欠缺,地方法院乃至最高法院,即便作出具有创新意义的司法解释的裁判,也不会构成“强拘束力”(以后碰到类似案件的法院,可能会参考这一裁判但不一定完全遵循,可谓具有“弱拘束力”)。真正有效的、在各级法院审判实务中得到普遍适用的司法解释,出自最高法院的个案批复或抽象规则。虽然最高法院并非以“坐堂审案”的方式作出司法解释,但经验表明,最高法院的批复或规则,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审判实务中的事实和问题而产生的。其中,抽象规则形式的司法解释,既是来源于实际个案的,又是超越实际个案的。因为,最高法院可以不拘泥于特定案情或特定当事人的意见陈述,可以像立法机关那样听取相关利益主体的意见或召开专家咨询会。中国的最高法院,就是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履行着各国法院都要负担的政治使命。
“公民动议司法解释”的机制,实际上也并不仅仅在于扩大司法解释的信息渠道——最高法院可能对需要解释的问题早有了解,更在于增强司法解释——相当意义上是一项政治使命——在民众中的认同和接受程度。不过,中国式司法解释并非没有潜在的危险。
时机的选择
熊伟在建议中提及:非法撤换、停职、诫免村委会成员是对村民自治权的侵犯,也侵犯了按法定程序当选的村委会成员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即可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并不局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现实中已有法院拒绝在行政诉讼中受理此类案件,因此,最高法院应依照《行政诉讼法》的精神作出解释,将对村委会成员的非法撤换、停职、诫免等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若果如此,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1条规定,村委会成员基本上能胜诉,中国的村民自治将向前迈进一大步。
最高法院采纳此建议,显然已经暗示其对上述理由的认可;至少,足以让人相信,最高法院默认了其面临的推动村民自治的政治使命。于是,以往悄悄地隐在“法律解释”面纱下的政治使命,被一下子推到了聚光灯之下,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自我暴露,是一个大胆的、勇敢的坦白。然而,也有可能使最高法院以及各地方法院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通过的。可见,村民自治的改革计划,早在9年以前,就已经由最高权力机关宣示了。然而,直到现在,基层政府非法撤换、停职、诫免村委会成员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恐怕不能简单地说一句“基层政府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滥用权力”就可打发掉的。除了出于裙带、寻租等因素以外,还可能出于“完成国家治理任务”、“对村民自治的不信任”等因素。假如村委会成员被村民告发存在违法乱纪的问题,或者存在滥用权力侵犯村民正当权益或公共利益的问题,或者存在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或复兴宗族势力的问题,基层政府也有可能按传统管理方式,对村委会成员进行撤换、停职等。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村民自治计划,不是朝夕之间即可实现的,它牵涉整个农村治理的改革。当前,农业税的取消,至少在理论上使基层政府失去了70%左右需要借助村委会的治理任务。这就为村委会成员的任免受基层政府干预,扫除了重大的障碍。但是,这显然不是由司法解释加以推动的。假设最高法院在9年前就作出允许村委会成员对非法撤换、停职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司法解释,虽然符合《行政诉讼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神,村委会成员的胜诉率也会很高,但国家治理任务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会成为诉讼之后的重大问题。
此例充分显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一个“是否合乎时宜”的问题。在引入“公民动议司法解释”机制之后,最高法院就必须经受得住一个考验:当公民动议显得十分的人情、人理、人法的时候,最高法院是不顾时宜地采纳还是慎重考虑时机。若是前者,或可得到普通民众直觉上的认同,但不见得对制度改革有利;若是后者,或许对制度改革有利,但可能会使最高法院直面普通民众的质疑。
此外,若最高法院作出允许村委会成员起诉的司法解释,的确会使村民自治迈前一大步,但是,最高法院也需考虑在未来如何应对村民自治(集体治理)与村民(个体权益)之间的纠纷。如果说基层政府以往还是对此类纠纷进行处理的“先头军”,那么,农村治理改革很有可能使基层政府失去担纲“先头军”的积极性,许多纠纷可能会直接摆到法院面前,让法院来厘定村民自治与个体村民之间的正当关系。这是最高法院可能面临的另一挑战。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