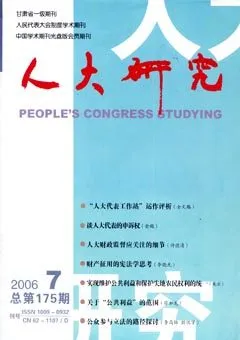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失地农民权利的统一
世界各国经验证明,每一轮“圈地风”刮来,受到最大损害的便是农民和耕地。中国的“圈地风”近年来也呈愈演愈烈之势。“公共利益不明”,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清,是导致乱占耕地现象泛滥的一个原因。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所谓征用,只是暂时的使用,使用后将返还原物,不能返还原物或对原物有损害时,应予以赔偿或补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立法规定的土地征用均指国家以强制有偿的方式取得建设用地所有权。现行法所规定的征用,实质上为征收。征用(收)(包括土地征收)应当具有公共利益目的,这已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个基本规则。虽然按照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集体公有,但是土地仍然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尽管被征收土地的农民的就业和安置以市场为导向而有多种途径有其可行性,但并不能否认土地是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农村的失业保险功能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目前,征地方对农民的补偿太少,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难以维持日后生计,这样容易形成社会问题,造成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一、征地失控的原因——公共利益模糊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用地主体的多元化,国家调整了供地政策,对一些经营性用地项目改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无论公益性用地还是经营性用地,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强制征地办法。这样,在征地与供地之间制造了一个利益空间,从而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创造了条件。虽然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都规定了土地征用(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由于原《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一条及原《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都规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可以征用(收)。因此,实践中仍以经济建设作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征收土地,使原土地所有人(农村集体组织)的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农民不满意政府从农民手里征地后,卖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再转手赚巨额钱财。
我国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依法”征用,本无不妥。但是法律未对“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明确的阐释和界定,而对公益性(及其合理限度)的判定权力主要集中于领导人员,人民的意见实际得不到注意。许多被冠以公益之名的项目,其公益因素十分有限,例如,一些单位用于商业性经营的楼堂馆所,以财政拨款为建设资金,以国家建设名义征用土地。这种状况表明,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要件实际上已经非常模糊了。有学者以为,对公益的范围需要适当限制[2]。必须明确,经营性项目用地,不能启动国家的征地权,必须通过市场与农民集体和承包农户平等谈判协商取得土地使用权。同时,应允许农民集体土地以使用权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合作开发或自行开发经营。当然,所有土地的利用,都必须符合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二、政府是否是当然的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任何权力从它产生起就是公共的或者说是用来管理和服务于人类群体和社会的,个人掌握的权力不过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其性质仍然是公共权力。与社会上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相比,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最弱、最不明显,或者说,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公共利益的化身,是利益中立者。但是,历史上手握权力者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从而造成对公众和公共利益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因为,面对社会成员不同的偏好和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机构的组成人员和企业人士一样,都是具有利己心的,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政府自然要把个人利益带进政府行动和政府决策中去。地方政府把征地和地方经济、政绩联系起来时,政府官员把征地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时,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自然失灵了。
而且中国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均平化整体性利益格局,出现了利益观念多元化、利益单元个体化、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的状况。产权关系变更产生了大批具有独立利益的法人实体,同时形成了所有者阶层、企业经营者阶层和劳动者阶层等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带来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此情况下,行政价值观应该体现出整合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新的能力和目标。但是行政机关往往成为强势利益的代表,弱势利益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因此,整合社会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服务于社会进步,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如何防止政府代表的利益和真正的公共利益发生偏离,如何使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成为学者必须要研究的课题。多数学者认为,必须对政府权力施加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