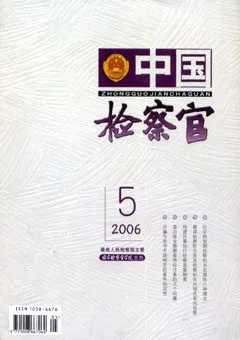职务侵占罪司法认定若干难点探析
内容摘要:司法实践中,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区别主要是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村基层组织人员侵占财产的,要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来定性;对于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各共同犯罪人的定罪量刑数额采“参与数额说”。
关键词:职务侵占罪 村基层组织 共同犯罪
一、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界限
两罪在客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即:职务侵占罪在主观上要求非法占有目的,而挪用资金罪在主观上则没有。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更从下面几点把握:
(一)看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手段
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人一般是通过实施侵吞、盗窃、骗取或其他手段来达到犯罪目的的。根据这点,可以将职务侵占罪的具体侵占行为分为四种类型:
1.侵吞型非法占有。“侵吞”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管理、经手、使用的本单位财物直接据为己有。侵吞型非法占有行为以行为人事先合法占有本单位财物为前提,是指行为人基于一定的合法事由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本单位的财物具有事实上的控制权、支配权。变合法持有为非法占有,是侵吞型非法占有的最本质特征。例如非法截留自己管理、使用的财产,将自己管理的罚没款或罚没物占为己有,将自己保管、使用的车辆等擅自出售、转让或赠与等。
2.窃取型非法占有。窃取型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一般来说,窃取型非法占有也以行为人合法管理本单位财物为前提。监守自盗是窃取型非法占有中最典型的一种。如公司的库房保管员将库房内的产品偷盗外卖,银行运钞车押运员在押运中偷窃押运的人民币。有的学者认为,所有的侵占行为都不是公开的,也是秘密实施的,监守自盗只是侵吞的一种方式而已。从广义上说,侵吞型非法占有是可以包括窃取型非法占有的。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窃取型非法占有中的合法管理本单位财物与侵吞型非法占有中的合法持有本单位财物还是有所区别的,合法持有人直接持有财物本身,甚至在一定时间内还可以有权支配该财物。而合法管理行为人一般不直接持有保管物,也无支配权。
3.骗取型非法占有。骗取型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骗取型非法占有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所骗取的对象是他人合法管理之下的本单位财物,行为人本人对该财物事先并未合法持有。例如购销人员伪造涂改单据冒领财物,出差人员虚报差旅费等。如果被骗财物是行为人合法持有,行为人为了掩盖其非法占有的事实而采用欺骗手段的,则其行为仍属于侵吞型非法占有行为,因为行为人在虚构事实之前已经非法占有了该财物。
4.其他类型的非法占有。其他类型的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除侵吞、盗窃、骗取以外的其他方法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如公司、企业下属部门巧立名目,私分公司、企业财物。对于其他类型,法律并未具体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绝大部分的职务侵占行为也已为侵吞、盗窃、诈骗所包容。应当说这属于立法的原则性规定,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立法空白。就目前情况看,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领导集体私分单位财产应属此列。
(二)看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客观态度
在司法实践中,有人这样认为:犯罪行为人在作出侵害单位资金的行为时是否对其行为进行掩盖,是区分其主观方面是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具有暂时挪用为目的的重要标志。如,单位的财务人员为侵占单位财物,使人们从帐面上无法直接发现其行为,而做假帐来掩盖;或者行为人在帐面上对资金的去向进行虚假记载以达到其挪用的目的。但笔者认为在行为人掩盖其侵占行为的过程中还应存在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况。作为的行为应该是其积极的掩盖,不作为的行为则属于消极的掩盖其侵占的行为。像行为人通过做假帐或将帐做平就是作为的侵占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人积极地掩盖其侵占的犯罪行为;而在有的案件中,由于行为人掌握了其所在单位的财务制度的漏洞,所以在其侵占单位财物期间,根本就没有做过帐,所以我们也无法通过行为人是否将帐做平或做假帐来认定其行为。但其行为仍是以非法占有这部分资金为目的的,笔者认为这应属于对其掩盖行为的消极方面。
(三)看行为人对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挪用资金罪的犯罪行为人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主要有四种:第一,供自己使用;第二,借贷给他人使用;第三,用于非法活动;第四,用于营利性活动。并且对时间上的要求是达到三个月。通过对“挪用”资金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其使用的目的是为解决一时之需来弥补自己资金的暂时短缺,或是为了通过挪用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而要转嫁风险进行的。如,由于自已没有资金或想转嫁风险使自己避免损失而挪用单位资金进行炒股、投资的行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初衷是想“借钱生钱”,待盈利后再归还其挪用的部分,这表明其主观上只有挪用的故意。但“侵占”的情况则不同,侵占的目的是完全是为了非法占有那部分资金(这里为了与挪用资金进行比较只讨论侵财部分),达到私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侵占行为的后果是造成了单位资金所有权的变化。应该说这种行为的实施人考虑的是“如何非法占有单位的资金”,而不是“如何使用单位的资金”或“如何通过单位的资金进行收益”。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行为人为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大量侵吞单位的财物,得手后便大肆进行挥霍,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所以也可以通过对资金的使用方法、挥霍程度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对资金的非法“占有”目的。
(四)看行为人是否有能力偿还所侵占的资金
这里的“有能力”,笔者认为并不单单是指在案发后的积极退赃,而应该是指行为人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指多次挪用或侵占的过程)是否有能力偿还和案发之后是否有能力偿还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多次侵害资金的行为发生了一段时间后(这种行为可以是以“挪用”为初衷而进行的侵害行为),行为人发现由于自已先前的行为而导致不具备偿还所侵害资金的能力,但是却仍继续实施侵害本单位资金的行为,这种情况应认定犯罪行为人具有职务侵占的犯罪目;第二种情况主要是指,在犯罪行为的事实败露后,犯罪行为人在具有偿还被其侵害的资金的能力的情况下仍继续掩盖其犯罪行为,或是以携款逃匿的方式来逃避法律的惩罚,这种情况当然也就该属于职务侵占罪了。
二、村基层组织人员范围及其行为法律性质的司法认定
2000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哪些公务行为属于“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做出了规定。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的管理村公共事务工作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村集体财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解释》中所说的“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主要是指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经联社、经济合作社、农工商联合企业等掌管村经济活动的组织的人员。因为,他们是农村中掌握权力、可能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以外的人员如村民小组长,不能适用《解释》。199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规定,“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271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三、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数额的认定问题
财产犯罪的共同犯罪中,对于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数额如何认定处罚,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有分赃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参与数额说之分。
笔者认为,分脏数额说忽略了职务侵占犯罪案件主犯的刑事责任,实践中难以施行,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人,可能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分赃数额较少或没有分赃,在共同犯罪既遂、但尚未分赃的情况下,以及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分赃数额说都无法贯彻执行。
而犯罪总额说的缺陷,一是对各共同犯罪人的作用和地位不加区别,特别是对多次共同犯罪,行为人参加次数有多有少,一律按照犯罪总额计算,有违罪责自负原则之嫌;二是与刑法总则规定相抵触。《刑法》第26条第四款规定:对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这里采取的显然是参与说而不是总额说。
笔者赞同参与数额说。即对于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应只对自己参与的犯罪数额,并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也与《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相一致。
责任编辑: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