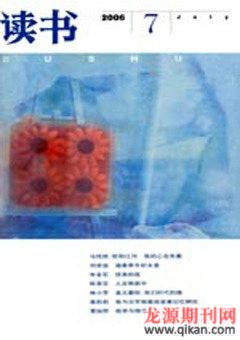田中正俊与日本人的“战争体验”
陈才俊
历史学家田中正俊(一九二二——二○○二)一九四三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是年,他作为“学徒出阵”(学生兵)应征编入福井县敦贺步兵连队,后转入航空兵地勤服役,曾前往菲律宾、台北等地值勤。一九四六年退伍,次年复学,并于一九五○年毕业。自一九五四年始,先后在横滨市立大学、东京大学、信州大学、神田外国语大学任教,并长期兼任东洋文库研究员。他既是亲历“二战”的老兵,又是颇具良知的学者,他一生著述颇多,尤以《战中战后(增订版)》和《东亚近代史的(研究)方法》最具影响。中译本《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以下简称《战中战后》),正是精选翻译此二书中之若干经典篇章而成。
“战争体验”是《战中战后》的理论主体与作者表达的思想主旨。首先,在究竟怎样的“战争体验”才是实质性的、具典型意义的问题上,田中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立场与对自己的“体验”所做的反省作为媒介,谦虚地向更多的、广义上的“战争体验”学习。其次,在如何辨别何者为实质性的、典型意义的“战争体验”命题上,田中又指出,不能仅限于表面的实际感受与“感动”,而应该从中获得并提高对“战争与和平”本质的、普遍性的理性认识。否则,就只能停滞在感性认识阶段,不仅不能获得正确公允的认知,而且有可能连悲惨的“战争体验”,或由此而得到的感性认识,也会与好战的、反动的“悲壮感”混为一谈。日本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经历与教训。而且,决定这种理性认识及理论实质的,就是“战争体验”之后直至战后的今天,与我们“争取和平实践”中各个方面紧密相关的东西。最后,田中还强调,作为上述普遍性的、理性认识上的“战争与和平”理论,绝不应该是简单的、抽象的甚至空洞的“理论”,而应是由各自的、不同人的体验和广泛的史实作为具体内容构成的理论,必须是作为“历史认识”的理论。只有以这种“历史认识”为媒介,反思者才有可能把“战争体验”作为真正的近代日本的“历史的经验”。基于以上透彻认识,田中将“战争体验”分为四个方面予以考察:一是后方军人在战争中的情状;二是前线军人特别是牺牲者在战争中的处境;三是未参战一般平民在战争中的境遇;四是被侵略国家人民在战争中的遭遇。
田中的“战争体验”理论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亦关涉到诸多的文本阐释,本文仅就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可能是一个被大多数日本国民都忽略了的问题——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究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典型意义的”“战争体验”——予以讨论。
毋庸置疑,任何战争都是非常惨烈的,这一点只有置身于战场前线者最刻骨铭心。田中本人“具有四年的战争经历”,亲历过许多的悲恸场面。他说,“这中间,我自身目睹的惨状,饱尝的痛苦和侮辱,至今连我的家属都不知晓”。入伍之初,田中在参加发放军装和举行出征仪式时,突然痛切地想起一首曾偶然接触到的无名氏创作的歌:“军装还散发着新的气味,这就出发了。可怜的生命啊,尚能有几时?”军官对新兵们训示道:“你们中间将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沉没,你们要做好这样的精神准备。”这句话可以说是当时新入伍者对战争未来及自己命运的唯一确切的判断,而且完全被后来残酷的现实证明了。据田中回忆,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亚洲太平洋战争失败止,仅与他同班的二百五十名“学徒出阵”者,就有将近三成战死。
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装载着包括田中在内数万名士兵的由十七艘运输船只组成的队伍,自大阪出航开赴战场。在运输船上,田中就开始感觉到死神随时都可能降临。他们被置于渗水的像蚕室一样的船舱底部,几乎每天都见到用白布裹着的尸体从船尾被抛入海中。田中目睹身边的一个中年补充兵,只能靠从战友口中喷出的水雾维持着生命——那已经看不清任何东西的痴滞的眼神,一辈子都深印于田中的脑海之中。恶劣的自然气候,污浊的生活环境,简陋的食物补给,军官的殴打奴役,都有可能导致死亡。更为可怕的是,他们随时可能受到美军的鱼雷、炮舰和飞机的袭击。田中他们这支十七艘船只的队伍,在美军鱼雷的攻击下,最后只有三艘到达了目的地马尼拉。十二月二十二日,田中又乘坐由十二艘运输船只组成的队伍离开被他们视若“已化为人间地狱”的马尼拉,可他们于一九四四年底最后一天的黎明时分逃进台湾高雄港时,又仅存三艘了。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国家征用而沉没的商船,共有两千五百艘,总吨位八百万吨。牺牲的船员共六万余人,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三。而且这些死者及其死亡时的详细情况至今仍是个模糊概念。曾亲面战争死神、被美军俘获、战后成为著名文学家的大冈升平在《礼智战记》中,对日本士兵临死前的绝望心情有如下描述:“哪里都找不到活路。也许可以活到七十岁或者更长的生命,却只有二十五岁就完结了,一种痛彻肺腑的必死的预感,压倒了年轻的士兵。在雨和火的后面,美国兵走过来并从身旁经过。但是由于日本士兵已没有了去路,只好成为狙击兵蜷缩在蛸壶之中,结果全都成了美国兵挥动着的火焰喷射器的牺牲品。”
田中还记得,当他们这些带着疲劳与困惫的士兵们侥幸爬上吕宋岛时,却又被立即抛向缺乏武器和粮食补给的第一线——日本军队的基本战争方针向来是“粮食来自敌方”。所以,当战斗出现僵持时,士兵首先面临的就是饥饿,随之而至的则是疾病之苦和精神错乱。一九四四年秋,田中因冲心性脚气病、重伤寒和赤痢等疾病住进了位于马尼拉郊外奎松(Quozon)的第十二陆军医院。该医院最盛时拥有两千多名工作人员,上万名伤员,每个房间要住一百多病号。只有一块白薯的菜粥和飘着野草叶的盐汤,就是伤员的“营养”餐。田中刚入院时,左邻的床上,躺着一个不知病因、皮肤与肌肉都僵硬了的人。此人与许多伤者一样,由于营养失调,很快便倒下去了。田中右邻床上躺着一个从礼智(Leyte)岛运来的士兵,来时已经昏迷不醒,连姓名还没弄清楚就死了。这个士兵整整经过一天一夜剧烈的喘息才断气。军医说,直到死时他都像是在继续跑着马拉松。另有一个伤兵,他死时好像是在战场上用肩托着炮身一样,不停地喊着“嗨哟、嗨哟”而气绝。还有个伤员拒绝进食医院的任何饮食,终日凝然地伫立在窗前,一发现院子里有蜥蜴,就突然跑去捉来吃。这显然是由于过分痛苦而招致精神错乱的结果。逐渐地,医院伤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摆放在走廊上的担架,也就成了他们临终的地方。只有从病房运走的死者,却没有康复出院的人。田中每天晚上都听到那些被送进医院伤者的凄惨叫喊,一种绝望的气氛包围着那些迎接死亡的人们,他们最后的话大多是“我有孩子,我不能死啊……”之类牵挂家属的话语。
曾经驻守于马尼拉近郊克拉克空军基地的西原敬氏,在描述日本军队惨败的凄情痛状时写道:美军在吕宋岛登陆。日军守备的克拉克基地和马尼拉陷落了。……在热带丛林中辗转了三个月,人人干瘦得不像样子,身体衰弱到拿不动一点重的东西。铁帽子扔了,手枪扔了,军刀扔了,最后连手提饭盒也扔了,只把铁水壶、布袋、罐头盒和准备自决用的手榴弹系在腰间。军靴的底子掉了,只有脱下死去战友脚上的靴子替代;食品没有了,只有从死去战友的布袋中寻找。丛林的低洼处、水边零乱堆放着尸体,散发着腥臭味。穿过密林到了丘陵地带,肮脏得皱皱巴巴的只遮着兜裆布的尸体,一望无边地堆放着。……人在临死时,先从内脏开始腐烂,随着呼吸吐出腐臭。苍蝇聚集着,动弹不得的伤员们的鼻子和嘴角都生了蛆。当蛆爬上眼睛时,他们的呼吸便停止了。
与田中同年出生的学生兵、战后曾任日本法政大学校长的阿利莫二氏,在其《吕宋之战——死亡谷》中的描述则更为凄惨:前线官兵吃野鼠、小鸟、蝌蚪、地虫、百足虫,甚至同胞的尸肉;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予以就地“处置”(“处置”是当时日本军队中的特定用语,指“杀死患者”);强迫随军妇女“自决”(即“集体自杀”);因被仇恨而背后遭遇同胞的“黑枪”等等。阿利莫二氏感叹道:“有这样的战争吗?在吕宋岛的战场上,有多少人都嘟囔着这句话啊!大家对国家领导人是多么憎恨啊!我没有勇气说同胞是在白白送死,但我不能不告诉大家,多数人根本不是喊着什么‘万岁而牺牲的,他们是含恨而死的。这里所说的‘万岁,自然是说‘天皇陛下万岁,可我在战场上,也亲眼送别过许多死者,却从未见到有哪一个人是喊着‘天皇陛下万岁死去的。”据统计,自一九三一年九月“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爆发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军死亡人数达二百三十多万。而且,这些死者还牵涉到妻子、父母、兄弟、姊妹等许许多多的人。全国各地无法忘却这种悲痛的遗属的总数,远远多于战死者。面对这种无奈的结局,田中指出,战争要求牺牲,然而即便是把战争作为前提,那么牺牲也只能是作为其结果而带来的战争的必然罪恶。
一九四五年的四月,本来身处战事相对平稳的台湾岛的田中,又亲历了一次无法忘怀的与战友的生离死别。由于美日在冲绳的战火恶化到绝望的程度,某日,田中所在的空军部队突然接到命令,正在待飞的少年飞行兵和学生兵立刻登上“特攻机”相继出击——为了轻装,他们不准带回程的燃料,而且起飞后马上甩掉机轮——不折不扣的飞向死亡。这样的惨状日复一日,田中彻底悲观了。显然,这种成功率极低的自我“牺牲”,对盲目投入其中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人们,是多么的不公平和不值得!作为幸存者,田中当时唯一能想到的是:不管怎样,我们跟着也要死的。他们把这种互相舔着伤口的悲壮感化成了通常的饯别。田中不禁质问,这种非理性的“牺牲的工具化”,是什么人发明出来?实在令人愤慨。
现代战争毫无疑问具有国家总体性质,所以交战国任何一方的平民都是受害者。毫无疑问,日本的野蛮侵略盗行也给自己的民族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报告,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本土各城市一般平民死于空袭者达三十三万人,伤者达四十七点三万人。仅广岛、长崎市民直接死于美军原子弹轰炸的就达三十万人以上。整个该国本土战灾死亡者的实数超过了五十万人。有关死亡的实际数字,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至今仍在日益增加,但也仅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数字,且其间必然包含许多无法确定姓名者。
作为对日本的惩罚,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美国空军对东京发动了以杀伤全部平民为目标的无区别地毯式轰炸。美国空军第二十一轰炸队司令官鲁梅少将以“日本的军事生产多来自家庭工业”为由,经过周密计划,三月九日夜,将载有总重量达两千吨燃烧弹的三百三十四架B29型飞机调往东京的“下町”。美军此次大空袭,事先选定在约一点六平方公里范围内,平均每平方公里约有人口十万零三千人。死者的人数也是美军事先预测好的。美军首先以后来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常用的凝固汽油弹,在目标地区周围燃起火墙加以封锁,然后向其中投入十九万个普通燃烧弹,计划极其周全而残酷。两个半小时的大空袭,造成东京四十平方公里内约二十五万户居民房屋被焚毁,约百万人失去家园,十万余人撒手人寰,十万余人肢体残废。在火海中逃难的人们,身上的衣服由于高热而燃烧,背上蹿着火苗,跑着跑着就倒下了,接着马上就变成了木炭似的焦黑的尸体。这天夜里,遭到轰炸的一些地区,直到燃起熊熊烈火之后,日本军方才迟迟发出警报,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之所以如此,据当时担任警报工作的陆军东部军参谋藤井恒男中尉的记录,是因为当时正值午夜零时,“顾虑深夜惊动天皇,让他起来到皇宫地下防空壕去是否妥当。犹豫和踌躇的结果,使警报未能及时发出”。
日本政府这种草菅人命的办事“国策”后来还酿成更大的惨剧。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发表。由于日本政府固守坚持“保护与维护国体”(即天皇制继续存在)的投降条件,拖延对宣言接受的时间,结果导致美军于八月六日和八月九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造成日本平民数十万人死伤。
田中对日本平民战争受害者做了细致的研究与深刻的剖析,并道出了他们的“战争体验”:“一般平民乃至市民在战争中的苦难,不仅直接来自于敌国的空袭等等,更为严重和具有日常持续性的是,来自本国统治者的侵略战争政策对个人生活的破坏,对自由的侵害和对生命的摧残。由于实行战时统制经济,造成了国民生活的贫困和营养失调,还有依据那臭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防谍法)》、《预防拘禁》等,当时的政权对思想、信念自由的蹂躏、拷问和虐杀;一九四四—— 一九四五年在塞班、冲绳、中国东北(满洲)的‘弃民与民众的集体自杀;中国遗留孤儿;还有在久米岛上日本军人对冲绳县民和朝鲜人的屠杀;等等。这都是战时统治者对人民权利的犯罪的结果。在作为‘为防卫日本本土而牺牲的冲绳,日本军将士战死者约六万六千人,与此同时这里平民的死亡却达到了十五万人。”日本一般平民的悲惨遭遇,随着大规模的亚洲太平洋侵略战争而延续到大范围的占领区。日本国内在战时统制经济下生活艰难的多数民众,受到“国策”宣传的诱骗,一度纷纷向所谓占领地移民。但随着日本军队的战败和撤退,这些平民或者为求保护而成为本国军队的人质,或者遭到遗弃。
据一八六四年《日内瓦条约》(日本未签字)和一八九九年第一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宣言,国际上应该严正地保障战争中的伤员、野战医院以及为其服务的医务工作者、红十字随军女护士等在交战中的中立性。可田中在《战中战后》里揭露,日本政府和军队的统治者们,一贯表面佯装威严,在国民面前卖弄道义言辞,但实际上却干着阳奉阴违的勾当,特别是在人类堕落到极点的太平洋战争中,竟敢冒犯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利用红十字标志的医疗船只装运武器;对红十字随军女护士,则命令她们绝对服从军人,不顾男女差别,强迫她们从事粗重的劳动,并最后把她们逼到死亡的绝路——强制集体自杀。田中曾疗伤过的马尼拉郊外奎松第十二陆军医院的女护士们,据说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转移”(退却),并被命令“在陷入敌人手中之前,自己收拾自己”,其结果是许多人都在战败后自杀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十二陆军医院的一千多名伤员在徒步撤退的过程中,被用空气注射或用“青酸加里”做了“处置”。田中由于此前执意出院而幸免于难。后来在他逃亡的路途中,又在一个兵站目睹大规模“处分”曾落为俘虏的同胞:让那些骨瘦如柴的俘虏替自己挖掘墓穴,然后再把他们用枪刺死。
然而,战后日本政府又为本国的平民战争受害者施以了哪些人道援助呢?面对当权者惨无人道、倒行逆施的国民政策,田中发出了义愤填膺的怒吼:“日本的为政者对战争的死难者,一面赞颂‘靖国神社的英灵,另一面对军人的抚恤金、遗族年金,仍旧沿着旧军队的等级差别。对于因空袭和战时义务劳动而牺牲的一般平民及其遗族,不要说年金,就连其他的社会保障也冷酷地不予以照顾。这样说来,他们对所谓‘英灵、牺牲的平民及其遗族的赎罪,到今天也没有完。必须指出,这不是军国主义政治又是什么?”
田中一以贯之地认为,讨论历史不只是把它作为过去来谈论,真正的“历史认识”是通过现代产生而且在现代重新建立起来的。具有“战争体验”的人,在战后的生活中,还要通过战后的人生感悟,对国内外的、亚洲的乃至全球的战争牺牲者承担起“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负有为他们“安魂”的义务和使命。只有视“战终”为自身主体战败体验而活下来的人们,以其生活方式作为媒介,和平才可能在战后的现代重苏。也只有基于此种“历史认识”,我们才能对未来的“历史的创造”充满积极、真切的希望。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于暨南大学新明湖苑
(《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日]田中正俊著,罗福惠、刘大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二○○五年五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