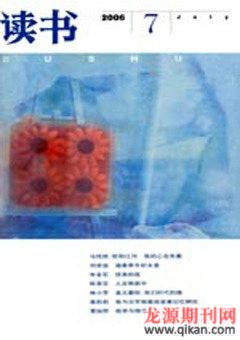饕餮盛宴与茶泡饭的滋味
张承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电影视觉的“饕餮盛宴”,从引进大片开始,到《英雄》、而后的《十面埋伏》、不久前的《无极》,好莱坞当年与电视抗衡的大片主义演变至今天,人类对技术的无限信任和贪婪的“饕餮”心态,终于使“盛宴”味同嚼蜡,正如王世襄老先生作为资深的“吃主儿”,对今天的吃却以“绝望”形容之。巧的是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也曾以吃喻自己的电影——“我这豆腐匠只能做炸豆腐和油方,炸猪排之类的恕不能为。”他所厌的尚是寻常油腻,还不是远离本真的人造食物。他也曾以《茶泡饭的滋味》描摹夫妇的恩爱境界,所谓“人间有味是清欢”,此类风味于今风头正劲的电影中久不见矣。
海德格尔称近代社会将是一个“技术时代”、“世界图像的时代”,循此,依从物质、技术至上时代的电影“现代化”已然登场。就电影言,它更容易体现技术的两面性。其与生俱来的商业性和技术性同时也是伤害艺术的因子。商业性使电影常常成为颇让人沮丧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高昂的成本经常拒绝优秀的创造者,著名者如格里菲斯、奥逊·威尔斯。技术则一方面是催生电影诞生的母体,却也是电影取得商业成功的一种手段。的确,人类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使技术不断完善着电影的魔力,在电影的童年时期,梅里爱就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影史也证明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全是佳音,甚至有声片替代无声片、彩色片替代黑白片这些看来纯属历史必然的改变也使电影在表演、色彩方面反而失去了某些丰厚的表现力和较为纯粹的艺术性。
其实,一向在电影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最擅烹制此等饕餮盛宴的美国电影人对一味偏重技术的无益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新式摄影和特殊效果一直在鞭打着观众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出现往往需要整体上巨大的能量去平衡……往往缺乏艺术所需的统一和深度。”“令人吃惊的技术足以刺激观众和评论家的眼睛……用新技术在电影领域寻找道路并不是那么富有成效。虽然新技术对摄影技术的发展也许有帮助,但是对引起深刻共鸣的电影艺术却没有什么益处。”([美]埃里克·舍曼:《导演电影》,7页)这些一九七六年的忠告,并没有阻止三十年后有些电影会选择除了视觉只有视觉的极端道路。但是,在文化反思中登场的“第五代”却纷纷改弦更张以技术为尚,恐怕不仅仅是取悦观众或谋求票房之罪。对中国来说,百多年来,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曾长久以来使我们慑服,其技术神力尤在“科学”的旗号下令人心驰神往。甚至“现代化”早年以烟囱吐出滚滚黑烟的形式进入国人视野时,也成了郭沫若新诗里讴歌的工业文明的“黑牡丹”。尽管现代化对人类的恩威并施已被认识,但在一波一波图强和求富的愿望下,它仍诱惑着许多中国人,并畸变成一种忽略自身传统的特殊模式。对本土文化及艺术这一层面的影响,只需看大拆大建后千篇一律高楼林立的城市新貌便可知一二。
好莱坞倾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电影市场,多被归功于《侏罗纪公园》一片,表面看来是影片的技术强势,背后则是蔓延向全球的美式文化。电影的“现代化”在全球化以前尚不明显,不嗜牛排黄油的还可以端起自己的茶泡饭,除了爱其简单,更重要的是有亲切的本色。但在今天,本土风味的电影日见凋零,尤其东方电影,不仅中国电影如是,日本作为东方世界中电影最发达的国度,现在似乎也失掉了自信力。后发达国家不仅为发达国家提供经济原料,也同样奉上自己的文化原料,期待西方世界的首肯,而被首肯的东方电影大多符合西方预设——通常带着某种陌生神秘的文化特质,如果期待落空,就会出现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特吕弗称再也不要看见印度电影大师雷伊的“印度农民电影”的恶评。为了呈现这种趣味,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走上极致与边缘化的道路,这种一致又使西方眼光不停地喜新厌旧,以东亚电影为例,在西方电影节上就呈现出明显的风水轮流转现象。首先进入西方视野的是日本电影,上世纪曾深得戛纳、威尼斯、柏林等电影节的芳心,经过五十年代的黑泽明和沟口健二、六十年代的新浪潮、七十年代的道德批判导演,日本开始被西方疏远,硕果仅存的也许只有宫崎骏。下一个新面孔是中国电影,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大陆、台湾莫不如是,连一向听命于商业的香港电影也有个王家卫。越南、韩国电影则是最迟的新贵。上述曾被不屑的“农民电影”也盼来出头之日,近年被西方电影人力赞的阿巴斯何尝没有一点农民气?
说到现在的中日电影该如何表现本国文化之色,看传统艺术样式在电影里如何被表现就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曾借助西方舶来的电影保存了许多传统戏曲,虽然遇到表现手法上的一些矛盾,但仍不乏杰作。但最近的《千里走单骑》,电影既由傩戏得名,也以忠义为尚,那么描述中国民间敬仰的忠义之神关公的这一傩戏就该在影片中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描绘与戏呼应的戏外人生,莫若用戏里悲欢来映衬最为贴切。遗憾的是,关公、傩戏又成了张艺谋一向喜好展示的某种猎奇意味的文化符码,最后大戏甫一开锣,现代音乐马上响起,比起从前的灯笼、染坊漫不经心多了。而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这部未能在西方电影节折桂的电影,在我看来,并不逊色于《悲情城市》。影片讲述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半生传奇,且不谈电影中大段大段李天禄本人冷眼看生死的自我陈述,其中大量布袋戏演出实况的片段,借由耳熟能详的旧戏、古朴的唱词也即太半传达出电影所着重的人世沧桑之感。它不仅尊重主人公敬天事人、达观任侠的古中国之风,更爱重孕育出这种个性的文化传统。
同样的,日本老电影中对能、净琉璃、歌舞伎也常有不吝的手笔。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如小津《晚春》中的能、市川昆《雪之丞变化》中的歌舞伎、稻垣浩《无法松的一生》中的园大鼓,沟口健二的电影中,更是有大段类似原始记录的传统戏曲表演。日本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武士电影,“世界的”三船敏郎曾是与西部牛仔相颉颃的硬汉形象,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武士电影日渐式微。日本电影人反思的结果是推出武士电影的解构之作,二○○二年山田洋次的《黄昏清兵卫》获得日本国内许多好评,但真田广富所饰演的黄昏清兵卫与其说是个有着至高智慧的逃世武士,莫若说更像现代社会中无力疲惫的男性,甚至比不得浪迹飘零、屡屡碰壁的寅次郎。长期在日本民众中家喻户诵的仗剑四游、求取功名的宫本武藏式英雄被抛弃了,而美国的个人英雄却仍在现代都市中继续他的救世传奇。如果说武士电影需要破灭神话的解构之作,那么早在一九三五年,日本早夭的天才导演山中贞雄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他当时与稻垣浩、三村伸太郎等人所组建的“鸣泷组”,其创作目的即是拍摄“带发髻的现代剧”,吸收美国电影和好友小津安二郎的小市民影片,用现代人的情感、语言去塑造低层武士,自成一格为“历史剧的小市民影片”。存世的三部作品中,其中《丹下左膳余话·百万两之壶》就一改须眉怒张的武士片为淡淡喜剧,只手只眼的怪侠丹下左膳变成被妇孺缚住手脚的气短英雄,但他依然是日本民众熟悉热爱的武士,人性的、平民的情感固然是现代人的,却保留着骁勇好义的古风。电影的古意流传,只从丹下左膳造型强烈的浮世绘风格即可知之,从服饰、化妆乃至带着怒气下垂的嘴角,都肖似浮世绘名家东洲斋写乐那幅著名的《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更勿提电影中江户时代市井风情生机勃勃的再现,日本传统审美倾向中最突出的两面——物哀与滑稽在影片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而二○○四版的《丹下左膳余话·百万两之壶》情节与旧版相仿,但俊美的丹下左膳身着写有汉字的和服(无独有偶,不久前我们的武侠连续剧里也有个满脸匪气的武人穿着写满汉字的一袭白衣,尤以一个大大的“禅”字最为醒目,大概寓意出世,可惜效果却颇为滑稽),躺在纤尘不染的雅室中,怎么看也不像市井中的风尘英雄了。
我在想,电影发展到今日这样的光景,不知是否和现在的电影从业人员过于经院化、精英化有关?现行的电影教育体制无疑是一种“现代”的教育体制。中国人从前的艺术启蒙似乎相当一部分来自乡野戏台、瓜棚豆架之间,有着强烈的“散仙”气息,和中国传统艺术中推崇的佛道气质最相契合。中国的旧电影人,也多有不曾先上电影学院,甚至没有经历系统正规的艺术教育,而是从最不起眼的角色起步,道具、场记、美术、剪辑……杂学旁收,最后成就了名山事业。武侠电影大师胡金铨可为代表,首先是个旧式中国文人,然后才是个导演,浸淫于中国文化,嗜藏书,尤精通明史,好京剧,有这些渊源,方能一开武侠片的新局面。如没有胡金铨式的学养深厚,很多电影人至少也在沈从文先生所说的“社会大学”里阅尽人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中浓厚的人文关怀,即来自与里弄亭子间的朝夕相处。日本老一代电影大师中也多有中学毕业投身此行者。规整的学院教育当然并非一无是处,但其精英心态使大众艺术与大众远离也是不争的事实。电影人固然无须回到从前仰视劳工的诚惶诚恐,但也无须执拗于狭窄的个人经验或边缘人生,第六代导演的许多作品即因之而应者寥寥。
今天的中国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性与现代性如何取舍的困境之后,又面对全球化语境,学界对民族电影身份是否会丧失曾有过热烈争论。东方电影,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如何既保存自身的文化特质,又与现代化进程同步,也许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比我们先行一步的日本,在承诺无痛变革的“明治维新”之后,还是渐渐丧失了许多传统,小津安二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是竭力抓住一个逐渐失去自我风格的日本,那时的日本正一意在现代化的征程上孜孜以求。到七十年代,日本影评人只能哀叹——“小津坚持拍摄的家庭剧,在今天的日本电影院可以说几乎绝迹。随着电影产业的衰退,影院放映的影片以刺激强烈的暴力片和黄色片为主流。……然而家庭剧在今天的电视中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家庭题材的电视剧也已不是小津、成濑他们制作的那种风格恬淡的作品了,多数都是演员东奔西跑、吵吵嚷嚷、尖声喊叫的。”([日]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艺术》,11页)待到倾慕小津的德国导演文德斯八十年代再去日本拍摄《寻找小津》这部纪录片时,东京街头早已不见小津所讴歌的一切。中国电影近年来的历程似乎亦相仿佛。
或者,若持了悲观的心态看,在这个越来越趋同的时代,将来的某一天,也许只有在不断增加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才能看见民族电影的身影。如同不久前,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奔波日久后重新发现费穆的《小城之春》、胡金铨的《侠女》,对原本属于自己的文化血脉充满的竟是陌生与欣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