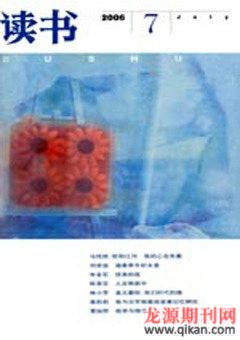优美的弦
朱金石
中国前卫艺术的起始源于何处似乎一直不是争论而是定论,研究这段历史的批评家们普遍认为一九七九年的“星星画展”开启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先河,而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接续“星星画展”的新的旗帜。在这样的批评声音中我们是否认真思考和对比西方早期前卫艺术的发生现象?是否详细地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现象的具体事件?还是匆忙地遮盖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几个原因:首先,直到今天前卫艺术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合法性,所以研究者很难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批评观点拿到公共论坛中去讨论,于是一家之言因其批评者的权威性成为了历史定论。其二,批评者在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脉络时只是更多的从某一层面的视角去诠释艺术现象,而忽略了更为细微与关键的艺术与本体、传统,包括艺术与特殊场景的具体关系。第三,七十年代是中国前卫艺术的摇篮,在这一时期艺术正处于社会封闭状态,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监控,艺术群体只能以“游击队”的方式松散地在朋友小圈子里活跃,难得与艺术批评群体构成同盟。因其相互了解甚少,批评的视野只能从具有社会影响的“星星画展”跳跃到之后由学院引发的“八五新潮”,而把一个时代的重要的环节一带而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与欧洲的六十年代的激浪派、贫穷艺术在语言方式上大相径庭,保留着传统的架上绘画方式,也与同时代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持不同政见艺术没有根本联系。研究这个问题线索复杂,只有耐心地把纠缠的问题梳理清晰,中国现代艺术的区域特征才能凸现,并且串联出中国历史及西方现代艺术对它的影响主线,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独立性是在何种自由状况下引导出来的?而且这种独立性是否将会对我们今天的困惑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性正如中国学者的看法,它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土壤,西方的影响催化和引导了中国的现代性,但在本质上却是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这样的历史观点不仅有效于政治经济,而且也适用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国内外的艺术评论家或许也会大致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在论证上,却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异军突起的海外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寻其实据。但实际上,恰恰是七十年代中期,一些至今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已经提前二十年实践了这样的现代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出现,和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有着必然联系。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终止了艺术学院教育,力挫了老一代艺术家如林风眠、董希文、刘海粟等在五十年代政治体制中缓慢的现代艺术探索,文化一下成为真空,而年轻艺术家在此时应运而生,成为承接这一重任的后来者,由此出现了中外艺术史上的奇观:一个庞大的学院艺术体制之外的艺术群体,以自学的方式进入艺术领域,创造了一场改变艺术史的地下艺术运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被这些无畏的年轻艺术家挪用于对正统艺术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与欧洲六十年代前卫艺术遥相呼应,后者把美国文化霸权作为挑战对象,也就是说,他们艺术的对立面都是权力,但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及生存环境迥异,导致了他们艺术风格及语言的根本区别。中国七十年代的前卫艺术的早期摹本基本来自俄罗斯及苏联画派、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因为现代主义的“摹本”在当时被官方所禁止,反倒使年轻的艺术家们产生了好奇与亲近,并从这样的方法里获得了产生不同见解的独立态度。这些艺术群体小圈子只能以散漫的方式形成凝集,而在家中作画与郊外写生则成为躲避政治监视的“自由据点”,因此,在那时艺术圈子少则三三两两,多则十几个人,相聚为友,长者为师,年轻者互学。
任何一个艺术现象,起源往往来自某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群体,然后再慢慢滚成雪球,中国现代艺术现象也是如此,所以赵文量这个传奇的代表人物和他的群体就必然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赵文量,生于一九三七年,五十年代开始习画,最初受俄罗斯画派影响,六十年代初,赵文量在北京结识了杨雨树、石振宇、张达安等艺术家一起画画,开启了艺术学院体制之外在野艺术的初端。他们与十年后结识的年轻艺术家身份一样,在某一家单位或工厂上班,业余时间用来画画。据赵文量回忆,最开始的风景写生大部分都在钓鱼台附近,开始并不是去画,而是去看,面对变化的光线、时间、天气去适应自己的感觉。一次他为了克服自己面对风景时的困惑,随意地把托在手里的小画箱倒置地画了一幅画,画时的感觉很轻松,慢慢地就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当然不是再继续地倒置画箱去画画,而是用随意轻松的方式去画画,但他强调,这不是主观地去画画,而是通过主动地去画而感受到自然。在七十年代之前,赵文量和他的朋友们不能看到西方艺术原作,只是偶然在展览中见到苏联艺术,大部分艺术信息都来自在中国发行的苏联《星火杂志》,在这里几乎只有微少的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介绍。他们的老师是自然,在对景写生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理解。赵文量画画无拘无束,在毫无借鉴的情况下,反而更加放任了自己,看他七十年代中期的小写生,往往会以为他受了哪位名师的指点,其实指点者就是他的感觉,他称自己为感觉主义,实为恰当地形容了他无师自通的绘画艺术天性。什么是赵文量的艺术风格呢?他说没风格就是他的风格,换句话说什么景物适应了他的感觉,他就会即情所至,或非常写实,这在头像写生中常会见到;或非常写意,在充分感受了对象之后,或突然纵笔畅流,或画中突然收笔。一些批评家认为,他是一个追求艺术形式的画家。他当然讲究形式,但看他的一九六七年的静物《凋零》、一九八九年的“风景系列”就会明白,他也是一个对社会非常敏感的艺术家,历史情节在他的艺术中总是被深深地暗示在某一风景或某一静物之中。
由赵文量为首、始于六十年代作画的北京画家群体,大多是三四十年代生人,最初人员数量在七八人之间,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张伟、马可鲁、韦海、史习习、刘是,女艺术家郑子燕、李珊、王蔼和、小田等开始增聚在这个群体,人数在二三十人之间。这个时候也是这个群体艺术风格的高峰,赵文量因其年长且画风成熟,自然成为了中心人物,他们常常十几个人手持画箱(他们自制的画箱轻小可手持作画)聚于北京市内的八一湖公园、紫竹院公园、郊外的香山,更远则至北戴河写生作画。其群体中最小的艺术家李珊,当时只有十八岁,正在上高中,为能全力画画,她常常一个星期里自己给自己开四五天病假。李珊的画风雅致清新,直用薄且明亮的色彩描绘目中所见的风景。她对赵文量的教学记忆尤深,她讲,赵文量让她明白画画到什么时候应该停是最关键的。画面的整体气氛决定了画的饱满,一次,她画画时旁边有一个学院的画家也在画,面对相同的风景,学院画家在树上“和泥”,而她的画面却异常透明,这使对方百思不得其解。李珊画的一幅《荷花》写生堪称杰作,这幅画简单奇异的画法,大概只有中国人能掌握,准确的颜色渲染出一顷荷塘气氛,但视线却凝结在几片荷叶上,概括的笔法描绘出了荷花的形状,对荷叶与荷叶之间的衔接采用了细微的疏离方法(即空白),一笔淡淡的黄绿色托靠住更淡的荷花的底部,既有野兽派色彩处理的方法,又融进了金农画梅的单纯质朴。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个艺术群体举办了第一次公开展览,参展者有二十多名画家,但随着展览结束这个群体也逐渐解体。八十年代初之后,商业化开始在中国登陆,但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机会,这使一些艺术家分流到社会其他领域寻找发展,而剩下不多的固守原位的艺术家也因艺术的趋向出现歧异分道扬镳。一颗划过七十年代的闪亮流星就此消陨,但它的精神却以间接的方式得以流传,譬如在德国生活工作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秦玉芬就是一个例子,她的装置作品的双重文化身份不仅是身在异乡的结果,最初的基因则早在七十年代就在北京获得了催发。这样的例子在王鲁炎、顾德新、黄锐、艾未未等活跃在中国艺坛的艺术家身上同样得以充分体现,在他们艺术的背后都隐含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同艺术小圈子的印痕。
北京在野艺术作为七十年代艺术小圈子的典范,不是证明现代性在中国同步的与西方共进,恰恰相反,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它是以一种形式滞后的方式,但从精神性、自由度、个人人格的独立状态闯进了我们今天的视线,从广义的社会雕塑观念出发。假若我们不是以切断历史的关联性与延续性作为艺术的批评角度,那么,七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自有其提示性,这不仅表现在应该对某些艺术群体、艺术家的重新关注,而是通过它横视那个时代,在只有政治的特殊年代,艺术顽强的抗争却超越了社会强制给个人的压迫。由这个角度来考量,艺术家写生艺术的“优美”就不仅意味着艺术美学,而且意味着社会民主,意味着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现代性的灵魂。这样的现代性不是试与西方一争高低,而是与两千年传统的古老文化形成生动的关联;以绵绵之力,缓缓功夫,从更长远的志向构成与自身文化身份的连接及和西方艺术对话的强劲张力。
令人反思的是,一九七九年“星星画展”的社会民主化诉求对彼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挑战构成了一次现代艺术的先例,但可疑的是,自此以后中国现代艺术一路演化,到今天却完全固定在艺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社会化的艺术社会美学脉络之中,无法从更为开阔的视野中把当代艺术置放在不同空间中给予充分展开。倒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艺术家的动漫艺术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与七十年代创作的艺术获得了某种脱离艺术政治美学的一致性。这种偶然的巧遇与亲和不是以文化载道的儒家正统文化作为根基,而是与在野于山林之间的闲云野鹤的隐士文化有着不可分离的、有意识的(七十年代艺术)或无意识的(七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艺术)关系,从这个角度,它们一方面是我们追踪中国现代艺术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从偏见中觉悟出来,重新定位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条隐蔽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回首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艺术不仅是为了进一步开拓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为了丰富艺术多元应做的不可缺失的功课。
二○○五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