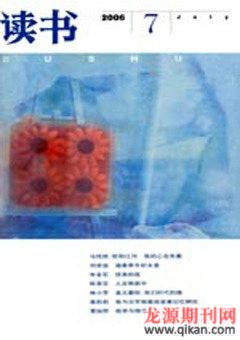“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
顾 彬
请允许我以鲁迅的气派开讲吧:其实我没什么要讲的,我将要讲的,无论如何,在别处已经有人讲过了;实际上,别人已经说得更好。关于“理解”的看法,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十年,这个论题得到了反复而精彩的讨论。我试图进一步阐述这个论题,或许会显得肤浅而笨拙。我研究这问题的路子的新意,仅仅在于试图继续别人的深思熟虑,以便建立起一条联结中国或东方的纽带;然而,即便从这一方面讲,我无论如何也不是开山的人物。
我决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划定我讨论的范围,先从李白开始。关于中国文学的这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在近期的研究中,一位美国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在一些叙事诗中,李白以她们的名字讲话的那些女人,果真是她们在那样讲话呢,还是她们仅仅是李白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话的代言人?(Chan,Shelly W.,《如何讲故事以及谁来讲故事:读李白的〈长干行〉和〈江夏行〉》in:Tang Studies,12/1994,esp.)当然,你可以轻易遇到这么个事实:男人不仅以女人的名义说话,而且女人也以男人的名义说话。比方说,你可以想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其中的叙述者是一个男人。我不知道文学领域有任何男人,会反对女人采取男人的声音这样一种权力,他们也不会禁止女人以消极的眼光来描绘男人。
然而,我们的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它将迫使我们返回到中国文化的黎明时分。你或许还记得庄子和惠施的对话,他们争论的那个问题,关系到人类对在快乐经验中的鱼有没有认知力和理解力。这迫使我们要对付好几个问题。如果李白被禁止以女人的声音讲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一种不可能之物了。另外一些问题于是就跳了出来:你不是鱼,你怎么可能谈论鱼呢?你不是天,你怎么可能谈论天呢?以及:你不是中国人,你怎么能获得关于中国人的知识呢?
自从我开始和中国打交道以来,我必得不厌其烦地听到一个口头语。起先,这说法使我呆若木鸡,接着这说法把我逗乐了,最后它只能使我怒不可遏。(我必须万分诚实地补充一句:这说法,我只是在大陆才听到,或者是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的嘴里听到;但在台湾和香港,从来没听到。)那个口头语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有中国人能了解中国。(当然,这样的说话方式不能一刀切地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我所知,韩国也有这样的说法;在阿拉伯世界,这样的说法也有案可查。参考Hanimann,Joseph,《镜子大厅:返回东方研究》),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1.08 1994.)设若这是真的,那我们就真的不得不对我们的思维来一番严肃的重新估计。以同样的口气,别人一定得允许我们下这么一个结论:只有日本人了解日本,只有美国人了解美国。你还可以相当符合逻辑地进一步推论:中国人不了解日本或者美国;中国人既不了解东方,也不了解西方。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如下这些句子的正确性呢:“只有女人了解女人”、“只有鱼了解鱼”、“只有天理解天”,以及“只有我了解我自己”?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习惯说法包含着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只能导致另外一些谬论。以类比的方式构造的一些命题,如“只有谋杀者了解谋杀者”或者“只有纳粹了解纳粹”,就把这个荒谬论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说这种话的那群人缺乏安全感,其心理学因素,就暗藏在这些命题当中。如果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那自然就可以由此说,外国人不可批评中国人。外国人将必然是错误的,方便得很,中国人必然是正确的。
我们的实际经验很难和这种见解相符合,并不令人惊讶。作为一个外国人,尽管我不自认为我就能了解中国,但有人却仍然要我对中国学生进行考试。双方都为这种安排忐忑,因为双方都不想丢脸。这位“外国人”不想问那些送人情的简单问题,中国学生希望没有太大的困难就能通过考试。然而,甚至在基本问题上,就起了误解。来自汉语地区的一个学生,却难能用拼音(创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为国际所通用)写出自己的名字。这个“外国人”简直服气了,他模模糊糊地怀疑,这个中国学生对自己母语的语音形式好像是不怎么熟悉。更有甚者,一个中国学生,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题目译成“The Lyrical Notes of Mr.Ren Jian”,或者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大名错误地写成“Si Maqian”,并且把他的《史记》搬到了唐朝,但这不见得耽误他的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在北京,你能得到一种更荒唐的经历,你被从出租车上撵了下来,因为司机不知道北京大学在哪儿,而且也忍受不了一个外国人告诉他这大学的方位。
你多半会纳闷,我干吗要念念不忘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尽管理解不见得和专业知识有关,但要理解,必须先和被理解的东西之间有距离。只是在某事向我客观地显示的时候,我才能对它进行反思。这意思是说,你要反思一个地方,你当然不必是那个地方的人。身为德国人,我可以使用“德国”这个词,而不必知道这词的本义。与此相似,冷不丁地要一个中国人解释“中国”这名称的意思,他就有困难,这没人觉得惊讶。我说距离,是什么意思?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在波恩告诉我说,“你们外国人”不能理解“文革”后遍及中国的诸多变化;可是,我的台湾讲师,由于她的出生地就在大陆近旁,就更可能理解那些变化。台北所处的位置,不仅比波恩更靠近大陆,而且也比许多中国北方的城市更靠近经济特区。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哈尔滨人理解汕头的事情,要比一个台北人理解得好呢?另外:为什么一个北京市民,仅仅因为他在地理上的靠近,就必定能理解一个广东人?语言、文化甚至气质上的差异,难道不会造成障碍吗?空间上的靠近,似乎并不是理解的可能性的一个主要的判断标准。我提到的距离,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距离。那是一种内在的距离,不仅中国人或许(而非必然)具有这种距离感,而且非中国人也肯定能学得会这种距离感。
怎么解释这种“内在距离”说?设想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即中国,全部时代的全部的人,都能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之,这大错特错。如果有那么一个中国,中国将会多么贫乏无聊,汉学领域也会极度单调乏味。然而,“中国”仅仅是表示某个东西的一个符号,我们是想把这某个东西理解为这世界的一个清晰而独特的部分。这个部分永远不曾客观地存在,而只是我们的诸多解释方式当中的一个游移的参照点。
这样一来,结果当然就是:否认西方人有权根据西方的材料以形成他们自己关于这个“中央帝国”的理解,却坚持要他们使用中国术语和思想倾向,就是完全荒谬的。(Weber-Sch奻er,Peter,《理解东亚:可能性和局限性》,in: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Bochum东亚研究年鉴》),19/1995,再次以非常新颖的方式讨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参考pp.11—12。)首先,我们得牢记在心的是,自王国维以来,大陆就开始以西方眼光来解释自己;其次,自一九四九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成了大陆压倒一切的世界观;第三,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回到唐朝,去细致地考察李白的言语模式,去考虑关于他的叙事诗中的女性声音的那些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到末了,我们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移情,我们只是要拟就关于某一事物的一个观念,而这个某一事物是我们根据一种有名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我愿意把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西方发明了东方,这就是东方这个对象),纳入一种更加相对的眼光中。西方汉学家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否则,他必得噤口不言。由于他本人就是在他的感知方式下的那个对象的始作俑者,他就应该以他对中国的思考来反思这个对象。与此相似,从事德国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创造了他自己的“德国”,这就导致了目前这么一种状况;德国文学享受的那种特别的赞誉,在波恩和北京之间形成了一道鲜亮的光谱。我必须补充一句:在中国,德国研究领域从未受到帝国主义利益考虑的左右;但在德国,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德国研究常常被工具化了。
一言以蔽之,我们讨论的主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关于“中国”的那个形象的性质,而不是我们理解不理解中国这个问题。
使这个形象或对象变得可以理解的那些解释方式,首先就是开放的。那些解释方式或许会变,否则,就是解释者和他解释的对象有了什么差错。然而,或许不变的东西,是互相交流着的解释者之间的对话的存在。照哲学家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的说法,真相是“双人游戏”。在我们的讨论中,这意味着:在我独处的时候,关于中国,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一旦我和别人交谈,小心谨慎就变得重要了,因为别人或许要我出证据,或许会对我提出批评。在对话的框架中,可允许的说法的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些限制之内,关于中国的每一个形象都是可能的,但并非每一个这样的形象都必得为人所接受。这种对话,仅仅是一个媒介,一个我们如何和中国角力(wrestle)的媒介;我们之所以和中国角力,是因为我们关心中国。
我们为什么关心中国?我只能以一个非中国人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关心中国是重要的,那是加强我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手段:以自我为参照,我是不可能理解我自己的,我只能参照那个不同的东西。只有借助于知道我确实不是什么的那个东西,我才能确定我潜在地可能是什么。这种立场,以距离为先决条件;然而,当这种立场是由一个西方人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暗示着一种批评的态度,这种批评态度就被错当成对中国缺乏善意。
可是,理解和友谊,或者甚至和敌意有什么牵扯?西方汉学家,尤其是那些研究现代中国的汉学家,难得有人能够对殖民主义的陷阱有免疫力。有人就不可避免地做如下推理:中国过去不得不在西方列强的重轭之下备受苦难,因此,身为一个西方的汉学家,你感觉到你有一种责任,你得对往昔非常敏感,你得自我约束,不要发那些太过苛刻的评断。你经常走得太远了;你在国内一听就会立刻反驳一些说法,你在国外却默然接受了。然而,中国在五十多年前已经重新获得了完全的主权;在这里,没有人想要为以往的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辩护。然而,许多颇有声望的东方发言人,已经指出:“帝国主义统治的历史经历[……],是一种大家都有的经历”(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西方和东方都有这种经历,因此,西方和东方可以互相批评,但不要做往常那种老生常谈式的责难。话说到这里,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Wagner)的“小生境文化”(niche-culture)论,应该得到重新考虑:他猜想,日薄西山的清朝,不仅是西方列强招致的一个衰落阶段,而且也是一个为在通商口岸和特许权这样的小生境当中的现代纪元的开始和旧政体的垮台做准备的阶段。
简而言之,由于我总是公开抨击他们,我就觉得我不必为我的老祖父们的恶行而嗫嚅不安;同时,我也不想仅仅因为德国人在中国的德性曾经野蛮,而怵于批评。
以我个人为例子,我想展示一下,“殖民主义陷阱”能导致些什么事情。在“文革”期间,我曾经努力取悦于那些关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令人张狂的思想。我不是总是非常成功,但我的努力却为人欣赏。事情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继续发展。要求总是这样:“请以我们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或者更精确地说:“按照我们政府的观点来理解它。”任是谁把理解和友谊同时拥抱在怀里,他都把自己弄成了个傻瓜。在某个节骨眼上,他是一个革命派,接着他成了一个改革派、一个资本主义者、一个消费者,到末了,他是政府的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儿。而且,这种蠢劲儿,难得有什么好处。即便在今天,在跟中国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之后,我还是被拒绝进入某些我想参观的地方;我想参观那些地方,既是出于对我的职业的热爱,也是出于我对中国持久不变的喜爱。我说的不是什么禁区,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在经过一番操作之后,有人通过旅游活动能从那些地点收取商业利益,公众都可以去参观那些地方。更有甚者,在我干这些蠢事的时候,许多中国人却对我侧目而视,而且一本正经地训导我必须保护他们的政府免遭苛刻的批评。
在诠释学领域,有一个关于理解的观念,可是这个观念能够别有意味地和我已经摒弃的那些友谊和敌意的口号挂起钩来。按照这个观念,当一种理解方式是直率的时候,它就是友好的;当一种理解方式是以陈词滥调为基础的时候,它就是敌意的。因此,把中国人说成蓝色的蚂蚁,就是敌意的,因为这说法是照搬老套路。相反,把西方一概而论地指为在道德上颓废,却不允许以开放的态度,就是说,不允许以好眼光来看西方的那些自觉地遵循传统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的人,这也是敌意的。
你或许会问我,在中国背景下,我为什么也断然摒弃绝对真实一说。“真实”只能存在于传统和宗教领域之中。然而,现代人却任性而无可挽回地毁灭了这些领域。因此,再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了,有的只是孤立起来的“真实”(参见Josef Simon在Zeichen und Iterpretation,《理解中的距离:符号与解释》,Frankfurt:Suhrkamp,1994中的前言)。有一项任务落在了我们头上,即把真实限定在我们自己这里;这项任务,我们能够、也必须不武断地来完成。我们只能以对话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提出一些假说,不同的主体通过各各不同的个人途径上下求索以互相影响(参考Jauβ,Hans Robert,《理解之路》,Munich:Fink,1994。该书关于理解和非理解的一些话题的若干重要思想,我借重不少)。搞得好了,我们或可相信我们理解,但是我们的理解不可能到达一种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最终有效的契合;这样的理解永远不会停止产生新问题和新答案(参考Watzlawick,Paul,《现实有多么现实?疯狂,欺骗与理解》,Munichl Piper,1992)。对那些解释,我们或许会一般地同意,或许不会一般地同意,因为这些解释,易于受到时代的阵痛和妄想的影响,永远不是盖棺定论或一成不变的。有些事情,例如“本质”这个能够发生持续影响的东西,是靠得住的解释也罢,是靠不住的解释也罢,都得指望未来的世代,都得指望他们的需要和问题,而不指望我们。
当有人谈论处于诠释学思想边缘上的理解问题的时候,他同时说的也是非理解,有时那甚至是一种故意的非理解,因为,在这里,在理解过程的背景下,不同之处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那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意见相同,那又能干什么?”回答起来是很容易的:你应该“发起一场语言学上的讨论,就是说,[……]把一致意见丢掉”。(Steinfeld,Thomas,《一位具有西方思想倾向的学者:纪念H.R.Jauss逝世》,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03.03.1997.)当所有的人都意见相同的时候,那就既没有教师,也没有学生;既没有“知道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人”;既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甚至也没有对话,因为那样一来,我们会走得太远了,我们可以设想自己在天国般的和谐一致的境界里。
互相之间不能完全地理解,无论如何不是个灾难;忘记了我们习惯性地缺乏理解,这才是灾难。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冲突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因为那就不会有什么事情能够缓解我们自我膨胀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加强我们对别人的尊重。我因此就是我自己的镜子。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事实牢记在心的话,我们就起码能够在对话中沟通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怎么办成此事?我们得允许别人有权利犯错误,得允许他们不同。有的时候,那是很痛苦的。但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无愧于我们人类存在的基本使命(马丁·海德格尔)。在谈话中,我们不仅创造了他们讨论的话题,而且也创造了我们自身以及我们与别人的联系。对于自我发现而言,别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既听不到别人听到的声音,也看不到我们自己的脸(若不借助于镜子)。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能否定别人对我们的声音或者我们的脸的那些说法的。成千上万的人对我们都有说法,在他们面前,我们孑然孤立,守着我们对自己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只有别人能理解我,只有非中国人能够理解中国;相反,只有中国人不理解中国。
我在开篇的时候,借鲁迅的声音说话。现在允许我以伽达默尔的声音收尾。在我开始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还没有对我发生影响。在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九六六年,我读了他的书《真理与方法》,到现在我仍然相信,该书呈现的这种诠释学哲学,不仅是两个个体的存在性相遇的事情,而且也关乎不同文化、不同人民之间的相遇。和不同的世界(可等同于国家)无关,一个“好为人师的文化”一变而为一个“勤学好问的社会”,是一种常见的情形。我从伽达默尔那里学来的东西,在我看来,一而再地适合于中国的友谊概念(即“知音”或“知己”)。为团结打下基础的,是语言。两国人民的相遇,是在语言当中。思维超越于那个他们不知道说什么的领域,他们却在语言出现的时候相遇了。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说到底,诠释学是一种艺术,它将把我们前意识的相似性扩展到我们的科学文明的特殊狭隘性之外,因而也将把我们的哲学研究转移到这种狭隘性之外。这样一来,诠释学或许能为人类创造这样一种未来:我们又能把一种声音送给其他的文化、其他的语言、其他的人民,或许(最重要的)也能把这声音送给动物和我们的环境,如此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世界。(我借重了Rüduger Safranski的一个电视节目:《今日哲学:哲学家伽达默尔》WDR 1996,这里的引文即采自该节目,前文的思想也与该节目有关。)
有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说,我落后于时代三十年,这不仅归因于这种理想主义观点,也和这整个的诠释学研究路子有关,因为,诠释学如今已经到了危机的时候。身为一个在理解和非理解之间的边界地带徘徊的汉学流浪者,承认我自己在哲学家们的后尘中瞠乎其后,何其快哉。还得继续用鲁迅那种讥讽的口吻说话:误解是骗人的,一如理解也是骗人的。
(王祖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