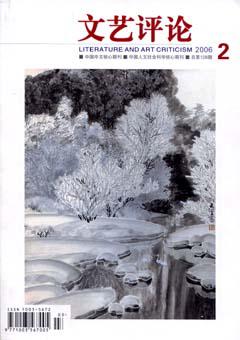论文艺接受中无睹效应
杨健平
文艺接受是审美主体对于文艺作品进行感知、体味、解读的复杂审美心理过程。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文艺接受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接受。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被接受的信息,又有被排斥和遗漏的信息,接受始终是和排斥相伴而行的。而审美信息的这种被忽略、遗漏的过程,就是一种无睹效应。这一过程又常常在无形中影响和左右着总体审美效应质量。所以我们在研究文艺接受规律时,就不能不探讨无睹效应的特点和规律。
一、无睹效应的发生
所谓无睹效应,是指在文艺接受过程中,作品中的某些审美信息被主体忽略、排斥、放弃、遗漏,所形成的一种消极性审美效果。也就是说,对于作品所传达的某些审美信息,审美主体将处在一种心不在焉和熟视无睹状态。无睹,并不是说接受者没有“睹”,而是说,在这些信息面前,他貌似接受,而实际并没能理解和体味之,或未能深入体味之。故而未能获其味。这时往往表现在主体对于审美信息的无兴趣、不关注或不体会等方面。
无睹效应在文艺接受中是相当普遍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接受者看起来是在接受艺术作品,实际上却没能获得多少审美信息。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艺术感受。这种效应出现在各种文艺接受活动中。无论你是读小说、看电影、听音乐、看绘画等等,总会有那么多审美信息没有引起你的兴趣和关注,没有被你理解,而被你拒收、遗弃和漏睹了。
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作者描写过克利斯朵夫在演奏钢琴时,莱哈脱太太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的窘态,她看起来似乎是在欣赏,而实际上却是似听非听,听而未闻,把许多重要的审美信息遗漏和排斥掉了。鲁迅说:“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体耐着性子接受下去,所得到的感受也是相当淡薄的,因此,这是一种消极、被动、丧失了主体性的文艺接受。无睹效应在整个文艺接受中所呈现的态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常常表现为时隐时现,时弱时强,它的出现,给审美过程留下了一块消极空白,出现了审美的搁浅。可以说,这种接受还没能进入到真正意义的文艺接受层面。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对审美信息的排斥和忽略,已超出了审美的范畴,似乎不能构成什么审美效应。但是,这毕竟是文艺接受活动中经常出现的审美现象,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和参与,又明显地影响着审美总效应的走向。因此,本文仍把它视为一种审美效应加以研究。
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全部接受文艺作品中的审美信息,而一定要排斥、放弃、遗漏掉一些内容呢?这原因还是要从审美主客体两方面来找。就主体来说,其审美心理结构对于审美信息有一个接纳和拒收的特殊机制。他只能接受其结构可以容纳的部分;就客体而言,它又必须符合主体的心理结构。在这方面,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已经给文艺接受理论一个重要启示。皮亚杰认为,人的认识的获得,是一个认识结构形成以及不断建构的过程。他说:“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须有反应刺激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由认识结构体现的。“结构”具有同化和调节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机制。同化就是将外界刺激有选择地纳入原有结构中进行改变、消化和吸收。主体只有通过结构的同化作用,才能了解、觉察这些刺激所包含的客观属性,才能产生认识。
当然,对于客体刺激仅有同化作用还不够,由于结构本身的限制,客体刺激中必然有许多原有结构所无法纳入的部分。为能接受新内容,主体还须改变原有结构,建立新结构,使之更好地适应客体,以期达到相对平衡。这就是结构的调节作用。这种旧结构不断被新结构所取代的过程,皮亚杰称之为建构。
文艺接受虽然不等于一般的认识活动,但仍是接受主客体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的审美感受便是建立在对审美对象认识的基础上的。在文艺接受中,接受主体正是凭借其原有审美感受心理结构去接受文艺作品的。接受的过程既包含同化,也包含建构。同化是对客体刺激的一种积极改变、调整,使之能够符合主体结构。但是,并非一切信息都能够被主体同化,主体只能吸纳适合于其框架(格局)的刺激,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新的整体。而那些不符合主体格局的信息则明显地被拒收和排斥了。所以,同化的同时,必然又有排斥的参与。也就是说,主体同化了他能够纳入和改造的部分信息,而摒弃了“异己”的或不理解的部分。
接受美学同样认为,文艺接受不仅有顺利接受,也有抵制的接受。这抵制的过程,当然也就是一种摒弃的过程。由此可见,所谓“直接接受”或“全部接受”是根本不可能的。文艺接受只能是主体依凭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心理结构对客体信息进行改造和摒弃过程中的接受。
无睹效应的产生,恰恰是来自于主体在同化进程中对于难以同化、同时又暂时不能实现建构的那部分信息的摒弃。对于审美信息的同化和接受程度以及无睹效应的发生及其强弱程度,既受制于接受者个体诸方面因素,也受制于接受者所处的文化场、时代场、社会场等客观因素:无睹效应又体现在不同的表现层面上。本文主要从民族性角度上,分析人们在接受异域作品时和接受本族作品时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无睹效应表现形态。
二、接受异域艺术的无睹效应
随着跨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文艺接受的视野也越加趋于全球化,即充满了对异域文化艺术的接受。我们知道,无论接受主体还是客体,都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当人们接受本民族作品时,由于在民族性等方面是一致的(“同形同构”),因此,很容易形成主客体之间的自然对应。达到“顺畅接受”,但是在接受异域作品时,由于接受主客体在民族性方面是非同一性的“异质交流”、“异质对应”,所以就会出现主客体的“对应错位”现象。也就是说,异域作品中有许多裹挟着异质文化的审美信息是主体所陌生的,不易理解的,或是与本土文化相悖离的。这就会使接受主客体难以契合,出现了暂时的审美“搁浅”。
在文艺接受中,主体又总是以本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去解读异域艺术,“以自己的‘文化眼镜去看待外来文化,即以自己种族作为标准,并且喜欢从本民族的观点,根据它的某种偏好去感知一切生活现象”。①这样一来,在异域作品中,那些与主体民族文化心理不相符的,难以理解的审美信息,有的受到主体的忽略、遗弃、拒收,有的则被否定和批评。前者产生了无睹效应,后者则产生了证异效应——对于异域作品加以批评和否定(关于证异效应,已在另文论及)。即便是那些已经被接纳的审美信息,大多也是在被误读、改造后同化过来的。它们早已经过了文化本土化处理。
例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上演时,场上西方听众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但中国人听起来却表现得无动于衷;中国的水墨画在本土很受欢迎,但拿到西方就曾受到冷遇而不被理解。这就是说,作品中的那些重要的审美信息,被外族接受后常常被遗漏、误读、忽略、排斥掉了。对于那些难以看懂,引不起兴趣的异域作品中的某些内容,接受者既“莫能知其味”,又不能引起“感官的狂欢”(波特莱尔语),所以也就常常处在心不在焉的状态。荀子说:“心不在焉则黑白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在这种接受状态下,即便审美主体反复受到审美信息的刺激,也难以产生审美兴趣,不能投入应有的审美关注。这时,主体所能触及的主要是作品的表层结构,而那些深层内容则往往被拒之于审美隔阂的墙壁之外。这些内容恰恰又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并在本民族内最能引起强烈审美心理反应的。
对异域作品的接受所产生的无睹效应一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主体对作品大部分审美信息的忽略和遗漏。多表现在对不理解的异族的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视听艺术的接受方面。因为这些艺术样式的外在形式感很强,且在艺术接受中占有重要意义,接受者如不能理解这些外在形式,就难以深入作品的深层结构,体验更丰富的审美内涵,所以很容易将作品的大量审美信息排斥掉。比如在今天的中国,“以形传神”、“情为物动”的传统欣赏习惯仍在民族审美心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许多人不理解或无法解读与中国传统艺术法则相悖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法则,不明白那些抽象形体究为何意。于是,在接受中也就往往得不到什么艺术感受;而西方人在接受中国的一些古代戏曲时同样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
第二种表现在主体对异域作品一部分审美信息的忽略和遗漏方面。它主要体现在接受异域的文学、电影、戏剧等艺术样式上。因为这类艺术作品的审美信息容量较大,特别是文学作品,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生图景,因此接受者如能冲破外在形式结构的民族障碍,进入到作品情感内容层面,就很容易对一些内容产生认同和共鸣;还有一些内容也可以通过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改造而被接受过来。即便如此,这种接受也总是与排斥交替进行的。接受的是可以理解并能引为共鸣的部分,排斥和遗漏的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令主体感到陌生的难以理解的部分。在接受过程中,能够被理解的部分,不断在主体心中得到强化,而不被理解的部分则愈加被淡化和忽略。无睹与接受此起彼伏,各自呈现出自己特有的流程,从而制约着总体审美效应的走向。
无睹效应往往使接受者产生一种接受困惑,为冲破这种审美隔阂,实现文化上的通约,避免无睹效应,许多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在把异域作品介绍给本国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作品进行民族性化的处理,而删改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1985年前苏联与英国联合摄制了一部传记片《巴甫洛娃——一个女人的一生》。然而,当该片在伦敦盛大的首映式上演时,苏联人发现,原有三个小时的译文拷贝已被缩短到两小时十二分。于是苏方指责英方不该如此“剪删”和“歪曲”原作;而英方则认为由于西方观众不习惯苏联人所欣赏的长篇叙述和详细描写,所以只得把它剪辑成一部能够吸引观众的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电影。其它方面姑且不论,从民族审美习惯角度来看,英方的这种删改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各民族“有权利要求按照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自己”。②歌德就曾肯定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将异族人“都变成了英国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③
其实,类似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莎士比亚的戏剧1914年登上我国舞台以来,几乎每次演出都经过或大或小的改动。1980年在北京上演《威尼斯商人》时,导演不仅把剧本处理成抒情喜剧,而且还将原作中犹太人夏洛克与威尼斯基督徒之间的异常突出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冲突情节砍得干干净净;我国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上世纪30年代曾赴美国演出,但首场演出未获成功。原因是所选剧目《晴雯撕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而在西方是没有这个节日的,他们不懂得中国人的这一民俗,所以由此发生的故事情节也就没有被西方人看懂。当时的观众反应木然,大部分审美信息都被遗漏掉了,出现了无睹效应。这一情况被梅兰芳察觉了,首场演出后,梅兰芳立刻做一番调查和了解,总结教训,不得不根据美国人的文化习俗和审美习惯重新编排剧目,而且删改了许多不易被理解的容易产生无睹效应的内容,最终使演出获得了成功。
正是因为在接受异域艺术时由于文化上的障碍容易产生无睹效应,所以一些本可以读懂外国原著的接受者常常宁可阅读本族译者的译著,而不愿去直接读原著。钱钟书就曾说:“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其实,这所谓的“高明”,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林纾的译文对于那些不易被本族理解、容易引起无睹效应的内容做了民族化处理。
以上诸例不仅表明了无睹效应的大量存在,也显示出人类在跨文化艺术交流中为征服它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努力。
三、接受本族艺术的无睹效应
无睹效应不仅表现在对异域艺术的接受,也表现在对本族艺术的接受,这里主要探讨的是接受本民族过去时代作品时所产生的无睹效应。
我们知道,文艺欣赏既有历时性接受(作品在历史发展中被人们的接受,接受美学称之为“垂直接受”),也有共时性接受(人们对同时代作品的接受,即“水平接受”),在共时性接受时,由于艺术家与接受者是同时代人,所以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其作品通常能给人一种亲近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睹效应的不存在)。然而当人们接受过去时代作品时,作品所反映的那一时代的生活和艺术家的情思却往往不易顺畅地被理解和认同,作品难免给主体带来一些疏远乃至陌生的感觉,这时常常出现主体对作品一些审美信息的无睹和忽略乃至排斥。它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对表现特定情感的审美信息的无睹和忽略。众所周知,人类的情感既有共同性,又有个别性。前者是产生共鸣的基础,后者是导致误读的原因。就个别性而言,人与人在诸多感受上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即便同时代人也不可能对同一审美对象有完全一致的感受。那么对于过去时代作品所表现的特定情感和感受,我们就更难以准确理解了。因此,那些表现特殊情感和反映个人境遇的一些审美信息,很容易被我们漏睹和忽略掉。
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固然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然而,人们所能引为共鸣的只是一般意义的触景伤怀情感。接受者可以以此为媒介,推彼及己,抒发和宣泄自己的某种怀旧情思。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先得我心”。事实上,《虞美人》所抒写的主要是一个被俘后的封建没落皇帝对失去的昔日富贵风流生活的哀怨和愁苦之情。即使他所抒写的亡国之恨,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些属于李煜个人的那一份情思和幽怨当然不会被后人真正读懂,后人决不会以此为审美切入点去寻求共鸣、觅求知音。恰恰相反,只有排斥了那些特殊的完全属于李煜个人的东西,而抓住能够引起共鸣的那些带有普遍性东西,人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和接受它。也正是由于这一排斥和无睹过程的参与,才使得《虞美人》赢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假如人人在欣赏该作品时总是去想着一个封建皇帝的狭小个人哀怨,那么就失去了审美共鸣,欣赏者也会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在文艺接受中,无睹效应并非总是起着消极作用。有时作者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与众不同的某些特殊情思和感受,常常是接受者产生共鸣的障碍,只有在它们被排斥和忽略后,人们才会在作品中重新寻找到情感的相符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个人情思都不会被他人所接受所理解。有些艺术家虽然境遇和感受独特,但仍能被别人读懂并形成共识,那是因为其作品所反映的情思往往通过另外一种渠道最终与人类的共同情思联接在一起。
其二、对特定时代审美趣味的排斥和遗漏。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都会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生成特定的审美思潮,形成该时代的社会审美趣味圈,它折射出人们在该时期的价值取向、审美需求。此时的文艺作品一旦准确生动地反映了该时代的审美思潮以及人们的意愿和心声,进入了人们的期待视野和社会审美趣味圈内,就会得到大多数接受者的关注和青睐,甚至容易产生出全社会瞩目的轰动效应。
不过,任何时代的审美趣味也不可能永霸文坛。一旦时过境迁,新的社会审美趣味必将取而代之。这时的人们又会有新的审美追求,正所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所以在文艺接受中,过去时代的社会审美趣味要么就不能引起人们兴趣,要么就不易被理解,因此很容易被人们排斥和忽略。
例如,西欧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和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在当时是很受宠的,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它们均被新的文艺思潮所取代,后来的读者再接触这类作品时,很难产生当时读者的那种浓厚兴趣,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后在文坛上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这些作品曾感染了当时的许多读者,引起社会共振,并产生了特殊社会审美效应。如今的人们再去接受它们时,特别是如今的年轻人接受这些作品时,显然难以出现当时人们那种激动、那种强烈感受和反响,因为有许多内容,许多审美追求是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只能把它们忽略、排斥掉,他们甚至会放弃对这类作品的接受。在文学史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可见,过去许多作品离开了当时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进入下一个时代时,它们往往不是人们所关注的主要目标。它们在上一时代所生成的,曾经使人如醉如痴、玩味不已甚至激动不已的那些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审美趣味,常常会使后来的接受者无动于衷,感受平平。这样看来,我们也就不该奇怪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为什么常常昙花一现。
当然,对于那些优秀作品来说,它们的艺术魅力是永恒的,永远会被不同时代所欣赏,但它们却不能保持永久的轰动效应。其间许多重要审美信息仍然要受到后人的忽略和排斥。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因,如今的影视剧的编导们在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对容易引起无睹效应的某些审美内容给予了删改,进行时代的处理。无论编导们怎样声称他们如何忠实原著,但原著依然逃脱不掉被他们多次加工和改编的命运。这不仅仅是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也是编导们自身的社会审美趣味对旧时代审美趣味的无睹使然。在此方面,有的西方学者曾主张寻找“文本”,客观解读和诠释原作的真正含义,试图追求和寻找文本的原汁原味。其实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所谓原汁原味的“文本”,早已被后来任何一个解读者重新进行了时代的、民族的、个人的过滤后的诠释,其间不乏许多对原作内容的改造和无睹。总是有那么多的信息被排斥、被忽略,总是有那么多的内容被误读、被创造,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总之,在文艺接受中,接受者总是要凭借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时代审美趣味,去接受与之相容的信息,排斥不相容的或暂不能同化的信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接受美学指出:对于一部作品意义的解读永远也不会完结,只要历史不断,文学的生命就不会终结。每一时代和民族都将对同一部作品做出不同的解读和诠释,一部作品将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
不过,并不是所有过去时代作品的审美趣味都受到排斥和无睹,在下列两情况中,它们不仅不会被排斥,反而会被积极接受:
第一种情况,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相近之处,一旦某一时代出现了与过去某时代相近似的历史经历,就很容易产生与之相似的社会情感、审美思潮和审美趣味。这时,那些过去时代的作品也就比较容易满足与之相近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屈原、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诗人的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抒发人们的激愤情感;抗战时期的人们常常通过这些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这时对于这类作品的接受常常能产生较强的审美效应。
第二种情况,有些文艺作品在刚刚问世之时,并没能受到当时人们的欣赏,反而倍受冷遇,而到了以后的某一时代,它们却受到人们特殊的喜爱和青睐。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受宠的时代不是在当时,而是在以后的年代。
例如,《白鲸》这部名著1850年出版时,丝毫没能被重视,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法国著名荒诞剧作家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最初上演时仅有三个观众,看完后还大呼上当,但十年后该剧竟风靡了整个欧洲。司汤达的《红与黑》刚问世时只印行750册,几乎无人问津,直至作者死后,作品才受人赏识。雨果的《欧也尼》初上演时,甚至被人嘲笑,八年后才意外“走红”。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优秀的文艺作品所反映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往往有一种时代的超前性。它们在刚刚问世之时,社会上尚未形成这种审美理想,还没有产生对该审美趣味的渴望和需求,而到了以后的某一时代,该审美趣味才酝酿成熟,这时,此类作品恰好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审美趣味就不仅不会被排斥和忽略,反而很容易受到人们的特殊宠爱。由此看来,优秀的艺术作品要有勇气、有能力穿越时间隧道,度过寂寞期,接受时间的考验。
四、结语
毫无疑问,文艺接受中的无睹效应决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方面。其实,任何一种形式的文艺接受都可能出现无睹效应,而且其表现形态也是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除上述表现形态外,由接受个体因素所引起的个体性无睹效应同样是极为普遍的。也就是说,接受主体所具有的文化艺术修养、个人爱好、生活阅历、年龄、职业等多种因素,都会对无睹效应的发生以及发生程度产生重要影响。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如韦勒克所说“头脑最简单的人可以看到情节,较有思想的人可以看到性格和性格冲突,文学知识较丰富的人可以看到词语的表达方法,对音乐敏感的人可以看到节奏,那些具有更多理解力和敏感性的听众则可以发现某种逐渐揭示出来的内容意义。”④显然,愈是文化艺术修养低,生活阅历等方面浅的人就愈容易排斥和遗漏掉大量的审美信息,难以触摸到作品的审美底蕴。同时,即使是同一接受者,在不同条件下对作品审美信息的遗漏和排斥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审美主客体之间在文化观念、审美理想等方面的矛盾和对立所导致的主体对作品一些内容、形式的否定、反感和批评,并不能称为无睹效应,而是属于证异效应。无睹效应主要表现为接受主体对于作品审美信息的忽略和遗漏,对作品某些信息的熟视无睹;而证异效应则表现为主体对作品的直接否定和批评,表现为主体与作品在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对立;前者表现为主体在审美关注和审美体验方面的缺失,而后者体现的则是主体对于作品的一种否定性情感态度。
另外,无睹效应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转化、常常要发生嬗变的。这是因为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被丰富和建构的开放系统。只要主体不断得到多元、丰富的审美信息的刺激、其审美心理结构就会随之得到建构,这时,过去一度被排斥的不被关注的审美信息就将成为被关注和体验的对象,审美效应也就随之发生嬗变。比如过去西方人不理解中国画,说它“不合透视”;同时,我国清代、近代一些画家也曾指责过西方的绘画“笔法全无”,但是到了后来,西方的许多艺术都渐渐被我国接受和理解了,而西方人同样开始重新解读和接受中国艺术。
事实证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越是不断被丰富、建构,就越是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丰富的异质审美信息,无睹效应也会越来减少;反之,主体越是长期自我封闭,不去接受多元文化艺术,其审美趣味就越是趋于保守,就越是容易产生无睹效应。因此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是极为重要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①北晨编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53-54页。
②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l卷第314页。
③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页。
④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