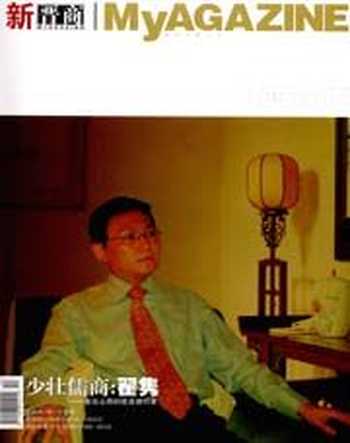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
张正明
晋商与徽商,兴衰各不同
晋商、徽商在兴起原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在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朝廷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勃兴。徽商则是明弘治五年(1492),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靠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由此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在清王朝道光十二年(1832)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商对盐业的垄断之后,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他们均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诚信仁义与君仁臣忠的文化影响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公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熹(南宋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熹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去人欲,存天理”等,朱熹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熹。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朱熹的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 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 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5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
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反映了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在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山西历来多战争,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在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过程之中,出现了许多镖行、镖师,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也发祥于山西太谷县。
避亲用乡与宗族维系的用人原则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侄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船至千艘,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也。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也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孤身闯荡与举家外出的经营现象
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指出:黔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初年第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豫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是把家眷留在原籍。正是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
严谨封闭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相对人少土地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高3丈余,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十余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主院前建有戏台院。当年在此组班唱戏,终日笙歌悦耳,热闹非凡。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组成,现存 “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
徽商居民则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落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也仅2800平方米。其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总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
此外,晋商“俭”而徽商“奢”,以及晋商、徽商在饮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晋商与徽商一样的功名,一样的缺憾
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赋税折银的结果,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了明代,水陆驿站干道也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徽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 开创了一种“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如以义制利、崇尚信义、经商爱国及敬业精神、进取精神、群体精神、修身正己等。
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结托关系,商业实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一统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晋商、徽商对封建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而封建政治势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晋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松对晋商、徽商的敲诈勒索。他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斗争。晋商、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的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
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晋商、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突破区域性界限,进行长距离贩运,从而加强了各地区面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多伦诺尔、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兴起,而徽商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晋商不仅在商业、金融的经营管理方面形成了经营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火活动的开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叶文化和珠算、会计、医药文化的兴起,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徽商则对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徽剧、徽菜、徽俗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总之,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是互有异同,各有千秋,这一现象也是当时时代背景、地缘、人文因素的具体反映。有异有同,通过互相交流、互相促进,进而产生了新的因素。但是由于处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无论晋商、徽商都尚难突破社会的拘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