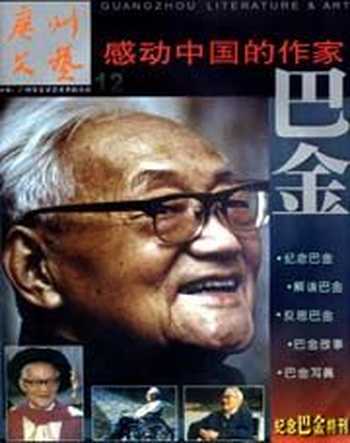还巴金以历史的公正
陈琼芝
毛泽东握着巴金的手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巴金曾说:“我有一个信仰,我愿意人知道它;我有一颗心,我愿意人了解它。我写文章,就为着想把自己的一切放在那里面给人看个仔细。然而写了那么多的字以后,到今天,我还在绝望地努力,找话语,找机会来表白我自己,好像我从前就没有写过一个字似的。”这段话写于1936年,却写尽了巴金一生的无奈。他寻求读者对他的了解和理解,而得到的常常是误解、非议甚至是残酷迫害,那主要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苏联的政治辞典中,无政府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已被马克思主义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也是接受了这个说法的,巴金怎么和它发生关联了呢?一些研究者就极力想为巴金摘除这层关系。有人说他是基于反帝反封建的愿望才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他事实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的承认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认为他更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世界观的“反动落后”并没有影响他“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也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正是他世界观的局限所在。总之,谈虎色变,都忌讳“无政府主义”这个字眼。为什么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从正面肯定“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理想?肯定他那颗赤子之心,他那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如果我们尊重客观事实,如果我们能将多元主义从哲学移过来也观照政治,如果我们不仅仅让胜利者写历史,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还巴金一份历史的公正。
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客观事实。
“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这是巴金常说的话。那么,什么是“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呢?
首先,他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
早年他是从反对社会不公,从改换政治制度的政治革命的理想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在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之后,在各派无政府主义中,他信奉克鲁泡特金所阐明出来的安那其主义的原理。克氏认为要有崇高的道德理想才能创造出一种基础于自由与正义的原理上面的新社会制度。他在国外流亡大半生,晚年回国后在莫斯科郊外写的最后一本书就是讲道德规范和它的目标的《伦理学》。什么是道德?他认为构成道德的三要素是互助、正义、自己牺牲。他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快乐的奋斗中得来的。巴金对此是完全认同的。
巴金对能够体现出这种精神的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们充满敬仰。他在写《灭亡》之前已经读了大量的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和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克鲁泡特金的自传、俄国十二月党人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及其他革命者的书,如《地下的俄罗斯》、妃格念尔的《回忆录》以及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等。“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例如克鲁泡特金,安那其主义最伟大的理论家,出身贵族,当过沙皇近侍和军官。但他舍弃了特权和巨大家产去当工人,去革命乃至成为囚徒。流亡中喝白开水吃干面包却甘之若饴。他的《我的自传》是巴金最喜欢的一本书:“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成长与发展的记录。”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同志和朋友也多是巴金敬佩的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的人,有的甚至是苦行主义者。当年刘师复发起成立“心社”时就有十二条社约:不吸烟、不喝酒、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不坐轿、不婚姻、不当官等。刘去世多年,杭州西湖烟霞洞旁有用世界语刻的他的墓碑。30年代几乎每年清明巴金都去给他扫墓,说他给了自己一面人生的镜子。
卢剑波是巴金早年的朋友,“五四”时期他们先通信后见面。他体弱多病,但精神力量极强,过清苦生活却超负荷工作。受打击也不改其志,不失赤子之心。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心里却充满了爱:“为着爱——如果必得有一个人献身于祭坛之上的时候,便让我来。”巴金说“我喜欢我有这样一个朋友”。
与叶非英是30年代在泉州相识的。叶没有成家,没有子女。他用无私的苦行度过了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巴金曾比他为耶稣。
巴金忘不了立达学园创办人匡互生公而忘私的精神,“我把他当做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
钟时是在旧金山打工的华侨。巴金和他1924年开始通信。巴金需要的书以及收藏的一些绝版书大多是他寄的;1928年巴金从马赛乘船回国的路费也是他送的。他已经去世了,但他们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的人物常常出现在巴金的笔下。他的不少作品写事业和爱情和家庭的冲突,主人公往往舍弃个人幸福献身事业。
巴金本人也恪守从克鲁泡特金学说中获得的道德理想,毕生不渝。他忘我工作,几乎成了个苦行主义者。
“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第二个特点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拘泥于洋教条。
“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样东西……这理由很简单: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巴金的这个态度是经过中国两次大的社会变动的考验证实了的。
最早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这时他刚刚去了法国,他在和朋友合著的《无政府主义和实际问题》中,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深入民众、了解实际了,就不会拘泥于原理。他指出“为人类谋幸福”提法不确切。因为人类是分成两个对抗的阶级的,而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统治阶级的理想。又比如一般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巴金则认为只应反对军阀政客争夺权力的战争,他不反对被压迫者为自卫、为自由而战。国内的大革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他认为不应国民党一党包办。无政府主义也应积极参加这民众的革命运动。“四一二”大屠杀发生后,他发表《无政府党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听了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被捕后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从容地走上绞架为主义献身的消息,他极其钦佩。写《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称他是“近代的伟大的殉道者”。
巴金经历的第二次社会动荡的考验是抗日战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即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中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为反对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有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当战争进行到艰苦的相持阶段,有的人对抗战前景动摇时,巴金1942年6月4日在一封给沈从文的信中却说:“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这胜利不是空等可得来的,他说:“在目前,每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巴金自己就是坚守岗位,日以继夜苦干的。
巴金不仅对战争的态度不同于一般无政府主义的教义,而且他还不断修正自己接受的观点。比如在革命手段上,外国无政府主义是主张暗杀的。中国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赞同。20年代李太一在《无政府党精神》中就说:“无论用什么手段,如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都可以使得。”他并且认为直接行动影响更大,手枪炸弹就是直接行动,一枚炸弹等于十万份传单。巴金也一度接受过这种观点。他在《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中称赞“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史是世界革命中最动人最光荣的一页”;此前写的《无政府主义与暴行》也说“刺杀一两个食人者总可以减少贫民的痛苦”。在对社会实际有了更多考察与了解之后,他承认自己错了:“并不是人生来就是坏的,而是现社会的制度使他们变坏的。假若现在的社会制度一天不推翻,那我们一面在杀坏人,它便一面在造坏人;那么我们虽以杀坏人为义务,一生也杀不尽的。”
像这样的“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革命事业有什么冲突呢?
“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误读”现象。
第一种“误读”反映在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取舍上。他对西欧的“无政府主义”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样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直接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字眼。”在西方众多的无政府主义派别中巴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他撰写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序言》中他说:“如果有人读了这书觉得我的安那其主义是和大部分中国安那其主义书报所说的不相同或者还相冲突的话,那么请他们原谅我,因为我只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又说:“在中国安那其主义的宣传虽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然而至今能够明确地懂得安那其主义的理论体系的人,可说是很少,无论是赞成者或者反对者。所以在中国就出现了关于安那其主义的各种奇怪的误解。”巴金此文写于1930年,其实至今“各种奇怪的误解”也未消除,这就是第二种“文化误读”,即对无政府主义知之甚少的以及对它充满成见的读者对“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的“误读”。
无政府主义又称安那其主义,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被后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的是法国的蒲鲁东。在他之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中国无政府主义最活跃的时期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和理论家是刘师复(1881~1920),他曾说无政府主义者以推翻政府和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发起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在全国设分会,当时颇具声势。作为社会思潮的一种,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早期也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蔡和森、吴玉章、周恩来,还有陈延年等都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也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和文章。他们曾以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就是无政府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陈延年还曾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骨干,翻译过巴枯宁全集,还将各地无政府共产主义刊物《民声社纪事录》、《实社自由录》、《人群》、《太平》等合并,统一为《进化》月刊,由他主编。1919年1月出的第一期印两千册,一个月内即售完。可见当时无政府主义影响之大。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社会主义同盟”在北京、广州也有分盟,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他们还共同成立印刷所,合办过《劳动者》周刊。一次在广州的联合罢工游行中共产主义者系红领带,举马克思画像;无政府主义者系黑领带,举克鲁泡特金的画像。后来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不少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如陈延年、吴玉章;有的脱离了政治运动,当教员、职员甚至和尚、隐士;也有的成了国民党的要员,如吴稚晖、李石曾。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传人中国后,确实起过反帝反封建的作用。“五四”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其影响明显减少,以至于有人不承认中国有过无政府运动。
因为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误解情有可原。遗憾的是长久以来我们被“成见”蒙住了双眼。1979年版《辞海》上权威地引了列宁的话:“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然而,拿这顶帽子戴在巴金头上是太不合适了。巴金不是个人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为崇高的理想无私奉献厂自己的—切。他从克鲁泡特金那里获得的道德理想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传说毛泽东对巴金也有公正看法。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会谈间隙会见文化界人士,他握着巴金的手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从巴金高昂的爱国热情,一贯的政治态度,毛认为他不像通常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感到奇怪。“文革”后期据说毛泽东也对巴金给予了关照。巴金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上说:“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想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
巴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那些从无政府主义走过来的人。1987年,他的女儿女婿到南方出差,去看了仍留在原地的父亲昔日的朋友。回来说很少见到这样真诚、纯朴、不自私的人,称赞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巴金好像顿悟了:对,理想主义者!“他们忠于理想,不停地追求理想。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这也正是巴金自己的写照。
回顾巴金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可不可以这样说:“无政府主义”只是他理想的外壳,无政府主义曾经是一个梦,早年是一个美丽的梦,后来是一个飘渺的梦,“文革”中则是一场摆不脱的噩梦。巴金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他撷取了克鲁泡特金学说中最美丽的花朵,他的无政府主义是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集中,其中也包含了他的爱国主义。他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他的“局限”,而是助他走向完美人格的阶梯。
(本文最初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5期,本书以《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转载稿刊印)
(责任编辑:王绍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