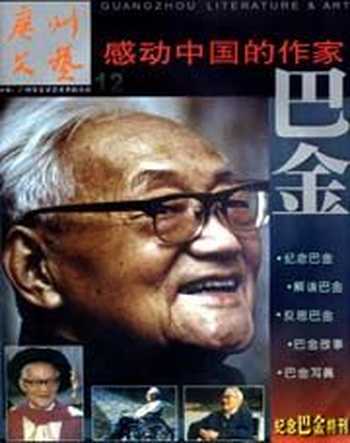巴金与鲁迅
春 华
巴金,和他生平最崇敬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之间,可以说有着一种深远的不解之缘。
1926年8月,巴金第一次到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他在北京患了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住了半个月就走了。
在这半个月内,始终陪伴着巴金度过那段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以后的几年里,巴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他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巴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至今他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他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
后来,巴金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感触颇深地说:“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1935年8月,巴金从日本回到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开始出书,先后出版了10集、160本单行本。与此同时,巴金还与靳以再次合作,创办了《文季月刊》,与靳以一起担任主编。
巴金在编辑《文学丛刊》时,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中一直钦敬的鲁迅先生,便向鲁迅先生约稿,先生一口答应了。过了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巴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收进去。
《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
谁料,鲁迅先生很快就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巴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鲁迅先生对任何工作都是很认真负责的。
在繁忙的编辑事务中,巴金和他早就心向往之的鲁迅先生有了直接的交往,尽管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相距也并不远,巴金却从未主动拜访过鲁迅先生。这或许是由于不习惯、不善于在先生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或许是怕打扰了先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巴金对鲁迅是怀着敬重和信任的,他也期望自己能让鲁迅了解。
他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和鲁迅先生熟悉的友人黄源、黎烈文,向鲁迅转赠自己的作品,也从他们那里听取鲁迅先生对于编辑工作的意见。
对于巴金这位并不参加左联,然而才华出众、在读者中间有广泛影响的青年作家,鲁迅与某些左翼评论家不同的是,他更多地采取了理解和爱护的态度。他更看重的不是人们说巴金信仰什么,而是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和怎样做的。
当时,在左翼阵营内部发生“两个口号”论争,内部矛盾呈现在表面。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在鲁迅与冯雪峰的支持下,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纠正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意见”,于是,双方各不相让。
在这种背景下,以周扬一派为主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他们有意拉巴金和黄源加入,由于巴金更亲近鲁迅,不赞同“国防文学”一派,所以拒绝加入。
而且,《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发表后,巴金和黎烈文还分头起草了一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明不同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态度。《宣言》写成后,交由鲁迅先生修改、签名。
6月15日,巴金和鲁迅、曹禺、靳以、黎烈文等77人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这激起了“国防文学”派对巴金的不满,《文学界》编者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说:“…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
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写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严厉斥责徐懋庸的不负责任的错误说法,文中写道: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鲁迅的复信还没有正式发表,巴金就在印刷所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看到自己素所景仰的鲁迅先生给自己这么高的评价,并且仗义执言,他深受感动。
有了鲁迅的理解,巴金对别人加在身上的莫须有罪名无所畏惧。他也写了一篇《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的文章:
“我是很赞成联合战线的;不过‘文艺家协会有着徐懋庸那样的人做理事,纵然加我以任何可怕的罪名,我也不会加入,因为破坏统一战线的并不是我,倒是他了。”
1936年10月1日,鲁迅与郭沫若、茅盾等21人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巴金是这次宣言的积极参加者。
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震动全国,也震动了巴金的心。虽然直接的交往有限,巴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感佩与亲近之感是极深的,何况先生给了他的事业以重要的支持,给他的精神以巨大的鼓舞,给了他理解。这些也使他对先生充满了感情。
对先生逝世,巴金不胜悲痛,他赶着为《文季月刊》第6期编一个纪念特辑,他在卷头语《悼鲁迅先生》中说: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虽远僻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很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在几乎所有的巴金所写的追忆鲁迅先生的文字中,他都强调了先生的伟大的人格风范,经常出现如“良心”、“人格”等字眼,我们知道,它们也是理解巴金一生写作品格的关键词。可见,巴金从鲁迅先生那里是自觉汲取了人格力量的。
同是在这一篇文章中,他还说:
“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领寻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明前进”。
而巴金,无疑正是这无数青年中的一位。
20日,巴金到鲁迅家参加治丧事务,参加了鲁迅先生治丧处的工作。21日,在万国殡仪馆,他守候先生灵前数日。
22日,为鲁迅先生举行葬礼,巴金亲自参加扶柩,和其他几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棺木,亲手把他生平最崇拜的伟大导师的遗体送入墓穴之中。
13年后,巴金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依然满怀深情地谈起他当时在殡仪馆中为先生守灵的情景——
“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帮助和鼓励,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对青年的热爱,我想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够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
我暗暗地说:他睡着了,他会活起来的。我曾经这样地安慰过自己:他要是能够推开棺盖坐起来,那是多么好啊。然而我望着望着,我走开,又走回来,我仍然望着,他始终不曾动过。我知道他不会活起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像立誓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
‘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辜负你。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
鲁迅——巴金心中永不殒落的辉煌太阳!
(责任编辑:朱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