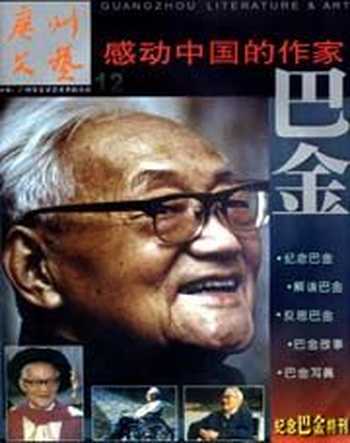信仰.磨难.智慧
路 哲
也许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名声不佳,好心人总想为巴金洗刷“罪名”,其实,无政府作为一种学说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可饶恕,巴金早年也不讳言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1921年他公开宣示:“安那其才是真自由,共产才是真平等。要建设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就只有社会革命。”他信仰无政府主义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也非因为“和国内外,一些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有过交往。”他认真钻研过许多无政府主义经典,积极从事过大量重大活动,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队伍中坚持时间最长,参与活动最多的人。有人说在中国“对无政府主义理论有研究的是黄凌霜和巴金。”“五四”前后巴金阅读过很多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对他影响尤大,他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1940年巴金在《面包与自由·前记》中写道:“在19世纪的末叶和20世纪初期没有一本书有过这样巨大的影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著作对他也有很大影响,他说:“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个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早在1929年毛一波就称赞巴金有“畅所欲言的魄力”。但是1949年以后,巴金在谈到他早年的信仰时,却变得谨慎小心、吞吞吐吐了。这是为什么?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曾是颇有影响的激进社会思潮,它传入中国的时间比马克思主义早,也比它影响大。“五四”以后有些中共党员就是由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巴金也是在这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众所周知,马、列等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过严厉批判,中共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曾进行过论战,1949年后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1980年巴金在回忆他50年代的心情时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这样,一个敢于畅所欲言的巴金,一个曾立志要“以‘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为敌人,决心与封建落后的制度作战”的“笔的斗士”,却被吓破了胆,忍气吞声了。他在《关于〈激流〉——创作回忆十》中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此时的巴金正满怀激情,很想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
巴金因为信仰受到旁敲侧击或蒙受屈辱时,他很少申辩,他只是说:“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他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个正式的、严密的组织。”这的确也是他的真心话,但是也正如他1980年所说:“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从巴金参加无政府主义活动和他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来看,他相信:“安那其才是真自由,共产才是真平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必定要来的、社会进化的趋势是如此”。巴金就是从他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中得到了鼓舞和力量,他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味盲从,对他所不同意的观点敢于据理力争。一辈子都在追求真理、讲真话并坚持信仰的巴金竟因为信仰遭受磨难该是多么痛苦呀!
中国的读书人因文字言论而招致灾祸者不胜枚举,但勇者仍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因为他们干预国家政治,并非为个人名利而是出于民族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是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一根支柱。中国不缺少唯唯诺诺的奴才,需要自信、自立、自尊的创造者。梁漱溟在泰山压顶之际仍然敢问:“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听意见的雅量?”孙冶方在大祸临头的1962年凛然宣称:“我不需要有三不主义,……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丁玲在悼念关露时深情地说:“这么多年来,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人人都需要温暖宜人的阳光,尤其是被打入冷宫的人们。人人都希望法治,非常害怕有人以言为法并朝令夕改。但是谁能保证不再出现滥用职权的“长官”?我们应当从巴金的著作中吸取智慧,应当学会“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责任编辑:王绍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