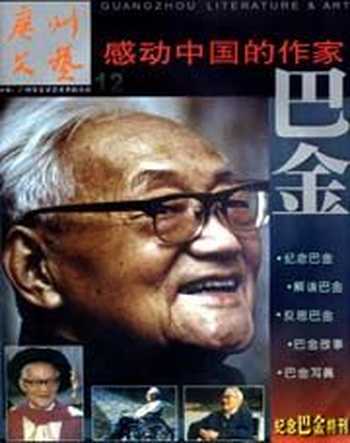论巴金
夏一粟
在读了前几期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发表巴金先生一封《给eg》底信后,我底眼泪顿时便不觉潸然地流下来了。
于是又使我回想起两年前一位朋友曾向我这样问着过说:
“在目前中国底许许多多的作家中,还有谁比巴金先生更伟大呢?”
当时我却躇踌了,沉默了,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一个有比巴金先生这样更伟大,更真挚,更激烈,更为正义而苦痛着的作家来。而且这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一直到了如今,如今我依然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解答来。
巴金,在他自己的那一条路上的确是伟大的。他因为看到眼前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事态,耳朵里听不惯民众底苦痛的呼声,所以,他也要求着革命。而革命必会使一个伟大人物死亡的,所以他的杜大心死亡了(《灭亡》),他的革命的人物毁灭了(《死去的太阳》),以后他又为着正义而需要着《复仇》,为着一个民族的被践踏而作着《海底梦》,为着大众的不平而有着他的《沙丁》和《雾》。总之,他的一切的著作都是感着人间的罪恶而苦恼,为着全世界的人类的不幸的命运而痛哭。而且他的每一篇著作都可以给每一个青年人带来一种伟大的心情,一种向光明走去的心情。自然,他的思想如何,当属另一个问题。但可以保证的是:他绝没有一般所谓普罗作家的臭味,尤其很少“口号”和“标语”,和等等色色的所谓“正义意识”。如象听见别人谈到民族,谈到国家,便斥为是思想落伍,这一类的下流习气,更可以说是绝对没有。
巴金,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作家,恐怕是谁也不敢加以否认而敬虔的吧?
但,惟其因为是伟大,一般地,所以总是苦痛着的。但丁是这样,杜斯杜夫斯基是这样,而我们的巴金先生也是这样。
可是,我所说的关于他的苦痛,并不是物质的;在作为物质生活与发展中的巴金,他起先在东南大学附中出去,因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到了法国后,便在一个平民的拉丁区内,嚼着冷硬的面包,忍耐着苦痛,一直过了两三年这样下贱人的生活;就是回国后到了上海,也仍然在开明书店作过极不相干的外国文的校对职务。在这种境地里的巴金,当然为一般大人物们所不屑道及的。但,这样看来在物质方面的巴金似乎也很苦痛的,可是实际上他的最苦痛的还是精神上的,譬如在《复仇》的序里面他说:
“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记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戴了假面具。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
又说:
“……我的灵魂为着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这就是他的灵魂的自白,也就是他的苦痛的自白。而且由这些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作家在精神上是怎样的苦痛。
在上海环龙路的一家花园的别墅的小屋里,他整天价地,日也写,夜也写,忘记了饮食,忘记了苦痛,忘记了自由。在青岛的一个朋友家里,他的灵魂也是悲痛着,颤动着;在北平与沈从文同住一个屋子里时,也还是一样。他显然地,没有过着安定的生活,而把他的一切的生活,完全建筑在信仰与理想上面。他说:
“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我是可以来牺牲我的一切的。”
但他并不是没有享受的机会的,也并不是无享受的可能;然而,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在过着他的素朴的平简的生活,而且还不见他有过恋爱的事情。虽然他也赞美女人的爱。而有着他的“初恋”,但人家总不相信他是会爱女人的。所以在《光明》的序里面他说:
“......不仅是一个阶级,差不多全人类都要借我的笔来伸诉他们的苦痛了。他们是有这权利的。在这时候我还能够絮絮地像说教者那样说什么爱人,祝福人的话么?”
啊!你伟大的作家哟!
这伟大的作家永未抛弃过他的指斥罪恶咒诅横暴的笔,他永远用他的苦痛的灵魂来使青年感动,教每个青年去怎样爱人,救人;而且每个青年为了读他的作品真不知流过多少的眼泪,痛哭过多少次,但这是同情的激感的。比方你谈他的《灭亡》,看到《杀头之盛典》,看到张为群的被杀的时候,那种凄凉的惨况,你能不流泪么?
巴金,这个大脑大眼,长脸短脚的作家,现在还在中国生存着,健长着,工作着的。自然,一样地也还是苦痛的。
虽然在《给eg》信的最后他说:“现在天下太平,文章无用,以后决计搁笔。”然而这却是他的绝望的哭泣。本来一个人不能发展他的信仰,散布他的思想时,这是多么一场最苦痛,最悲哀的事情啊!何况我们的这个伟大的作家——巴金!
巴金,总之在觉悟一民族的灵魂,而使之“向上”“奋斗”这一意义上说,巴金是有着他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自然,倘若对巴金先生有着兴趣与敬爱的青年人,在读了他的《写给eg》的信后,至少是会象我一样地关切的悲痛地,毕竟要流下几点酸痛的泪来。
但我们除掉希望我们的巴金先生能够重复继续来执笔写他的伟大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一点更多的光明,此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啊啊!你伟大的作家哟!奋兴吧!最后的胜利还是会属于你的。我们是如何地在被你感动着啊!
完了,完了,我们就此祝福吧!
(选自1935年7月16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第1736号)
(责任编辑:王绍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