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宵别梦寒
蒋 芸

到青山寺去求一根签,想问问自从父亲去后,为什么总也梦不到他。签上说他正在远游。年轻时的他,爱游山玩水,现在尘缘已了,正可以还他心愿。只是他一个人太寂寞了。路过道教的青松观,还是放心不下,还是要求一根签,想问问父亲的近况:钱够不够花,冬衣暖不暖,那些他游历的地方好不好玩。真是寂寞啊!没有人陪他,为什么连梦也不捎一个来?大概他还在生我的气。他生气时,总是这样不言不语,透着些疏淡,叫我看了伤心,比骂我还难过。
就是在他七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月,悄然离开,等不及我回去见他一面。灵堂前,照片中的父亲俯视着我,眼中有太多要说的话,也好像在等我跟他说话。
在他病重的那些年里,我本来应该守候在他榻前,跟他说些令他宽慰的话,说些我从未告诉过他的秘密往事:在成长的过程中,曾小心隐瞒着他的事儿,但是,我仍然抛不开那些俗事俗务。当他仍在人世的岁月中,心中带着牵挂与病魔搏斗,而我却为了并不充分的理由,疏远地往返着,真是对不起他。而他去后,曾经写过那么些文字的我,竟无一言一语来纪念他,只是一味支撑着心里面的凄凉、伤心、绝望与无可弥补的歉疚。虽然那样明白,日子过得愈久,那些感觉愈浓,那样的想念他,那样的爱他,却是太迟了。
父亲的影子,漂浮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一年一岁的成长历程,在一些记爱与记恨的思绪中,逐渐壮大。我总是要让他知道啊,父亲是那样疼我,我想临去的那一霎,他仍是惦着我的,亲爱的父亲。
我在记忆中翻寻,可曾有过依偎在他膝前的岁月?可曾向他发过小女儿式的娇嗔?他可曾对我说过一些足以宠坏我的话?不,自我懂事以来,他和我们总是聚少离多。父亲的慈爱躲在他高大的身影里,躲在他紧抿的唇角中。但是,每一个我长大的重要时刻,他总会赶来。那一年,在风城,面临紧张的升高中考试,从台北回来的父亲得了腹膜炎,躺在医院中。我带着复杂的心情,惦着他的病,惦着自己的考试结果,从新竹女中到新竹医院的路程变得那样长,慌乱的自行车,几次差一点把行人撞倒。我不敢去看榜,只想早一点看到父亲。那个夏天的风城,竟没有风,街道两旁,仿佛连路灯也没有。一排排的病床前,父亲虚弱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以棉花替他濡湿着,他只是说:“考不取也没关系,不要担心。”三年后,上台北考联考,同现在已当了十多年修女的伟利住在光盐宿舍。晚上,父亲成了修女宿舍中惟一的男访客,沙嬷嬷引他进来,父亲的影子在黯淡的灯影中显得那么慈爱。只是我那时实在不知道前途,真想扑在他怀中大哭一场,告诉他,我实在不想考这劳什子的大学,这样辛苦的准备,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但我只是像一个中学生站在老师面前一般,一句话也没说。父亲仍然说:“考不取也没关系,不要担心。”与三年前同样的一句话,竟成了我的定心丸;它是吉利的象征,对我。
他实在不是一个多话的男人,他的严肃与威仪使我从来没有机会对他说:爸爸我爱你,我想念你。我大概也遗传了他的这份倔强,不会说一些甜蜜的话,即使是真的感觉也难以启口。在木栅的第一年,父亲请了假来看我,宿舍里每个同学都说他神气,我很骄傲,却也没对他说过。我们一同走到车站,我送他回台北,一路上,没有什么话说。而假日,我去看他,他不在,工友替我打开爸爸的房门,一屋子的阳光。我就在他的宿舍中暖暖地睡了一觉,到现在还能感觉到那股直透心底的温暖。天黑了,父亲回来,看到我,笑了。那笑容也像下午的阳光,隔了二十年还记得分明,我却从来没有对他说过那时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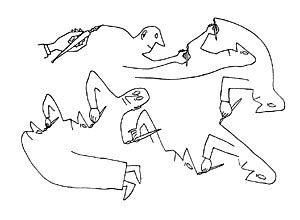
离开家以后的那些年,我习惯拿那些年纪与父亲差不多的人与他比,客观地比,总觉得没有人能比得上父亲。亲爱的父亲,有人拿玉树临风这四个字来形容男人,而年轻时的父亲,最配得上这四个字。十七岁那年,他独自从苏州到上海讨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自学自修,从不间断。我们常翻他读过的书,眉批上的字,详细而独到;他苦练的柳体,挺拔秀气得像他的人;他自己发明的读诗读词的声调,韵味十足,冬夜里,听来特别苍凉。好几回,耳际响着父亲读诗词的声音,催眠着我思乡的梦。啊,我亲爱的父亲,今宵别梦寒。
每一回过年,我们总搬个炭炉子进客厅,让父亲大显身手做蛋饺。他的蛋饺做得真细致,一般儿形状、一般儿大小。他原是一个整洁的人,等他病倒了,再也没有做蛋饺的心情,年也不像年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虽然,记忆里仍然留存着橘子皮在炭火中爆发的香,混合着蛋饺的香,弥漫在我们小小的厅中。这些也无可追寻,在外头,更怕过年了。
父亲做事的机关,是负责外销商品检验的。有时,家中也来些送饼干的人,饼干盒中自有乾坤,而我们每回早已懂得以跑一百码的姿态,将饼干盒送回馈赠者的手中。因为,总也忘不了,第一回打开盒子时,见到钞票,父亲愤怒的脸胀得通红,他一生最恨人不诚实。还记得初来香港第一年,看台湾的报纸,爸爸局里的金牛贪污案,大大小小官员牵连好几十人。编剧部的董千里先生开玩笑说:“有没有你父亲的大名?”
以父亲的职位,不可能不受牵连,但我脸不红,心不跳,连报纸也不看,名单也不查,坦然地说:“绝对不可能,我父亲是一个清廉的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我可以毫无惭愧,自自然然打心里说出这话来。
感谢父亲,他一向使我对他信心十足,他使我们在家境困难的岁月中,仍然保存着自尊、自爱。他也使我们懂得,穷困家境中长大的孩子,惟一的财富便是自尊心。
他有过许多机会,但他认为尊严比金钱物质更重要而不屑一顾,非常地能安贫乐道。
父亲的一生都是不阿谀逢迎的,对人好,却不媚俗。家搬到台北来以后,假日,厅中常会坐着一两个高谈阔论不请自来的年轻人,父亲最多只冷淡地点一下头;来的次数多了,坐得久了,下班回来的父亲有时会板着脸不招呼,常令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回,父亲对我说:
“好的男孩子,不说太多话。”
他自己就常是轻描淡写的一两句。后来,我发现背后骂我的人,便是曾在我家厅中坐的次数最多、话也说得最多的人。父亲看人有他自己的一套,只是当时我不觉得,一心想着,这样板着脸,不太伤人吗?想起来,惭愧自己的天真:怕伤人,却伤了自己。
来香港之后,几回,父亲也曾托人替我带来寒衣,尺寸不差,正好合适,那是他为我设计的。穿在身上,人家总问:在哪儿买的时装呀?真别致。而我总骄傲地说:爸爸为我设计的。人家再问:你爸爸是做时装的吗?不,不是,当然不是,爸爸只是一个学什么,像什么,做什么都要求好的人。他穿衣服别有品味,教我们身上不能多于三个颜色,永远保持自然与清爽。当我穿上他为我做的衣服,感觉上,不像一个已走出社会的大人,而只是一个小女孩子。但是,已离他太远了,在离家那段岁月,真正是想念他的,只是,在他的教育下,早已学会了不婆婆妈妈,也一样地倔强,不肯诉苦。我真正是爱他的,只是,那些年来,早已学会了不去吐露。走在尖沙咀的店铺中,拿着第一个月的薪水,替他买一只表,但是,金光闪闪的,他舍不得戴;替他买一个打火机,但是他早已戒了烟。一面逛街,一面思量,其实我真是爱他的,而且希望更像他,有他那一身的傲骨与做事的能力,也有他那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的洒脱。我在异乡中回忆,小时候,他带我去看电影,一部接一部地看,看到华灯初上,文艺片、西部片,喜剧、悲剧。但他从来没看过我编过的电影。现在,我也学会一口气看好几部电影,几番悲欢离合都经历了,却不能与父亲面对面坐下来,说一些我的得意与失意,说一些离家以后在江湖上的事,说一些以前不敢开口问他、不敢告诉他的事。让他看我像看一个成年的女人。
人来人往的街头,看到朋友的父亲,带着他成年的女儿亲密地走着,每回看得发痴,看得心疼。而香港,曾是父亲南来的一个驿站,他也曾在这里奔波过。十多年来,我摸熟了这里的街道,这里的名胜,这里好吃好玩的东西,却没有机会陪他旧地重游,也没有机会带着他,站在嘈杂的英皇道上,叫他看,对面高楼,突起的一块天台,有九盏红红的灯,有细细密密下垂的竹帘、灰色的砖墙,那便是我自己搭建起来的王国。我还拥有其他的东西,我的梦在现实中成形了一大半,但我并不快乐,因为他再也看不到了。
父亲大殓前,替他清理一些衣物、书籍,想找出一些心爱的东西,让他带去,竟找到一封他中风后,用左手写给我的信,歪歪斜斜的几行,还没有写完。在那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仍爱我至深,而我竟不知道!而我写给他的这一封信,却未及发出,他再也看不到。其实,我要对他说的话有更多的字数,而且我是从来没有对他说过的。我实实在在以我父亲为荣,我也要他以我为荣。他在不言不语中,教我做一个真正的人,教我凭自己的本事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成与败、好与坏都对自己负责任。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像一些平凡的男人一样,有过错误,有过一些小小的光荣。以我们成长的眼光,重新看他,更了解他,也更爱他。他的一生,虽然已终结,但是,我们子女对他的爱,以及他对我们的爱,将使他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选自香港《散文精读·亲情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