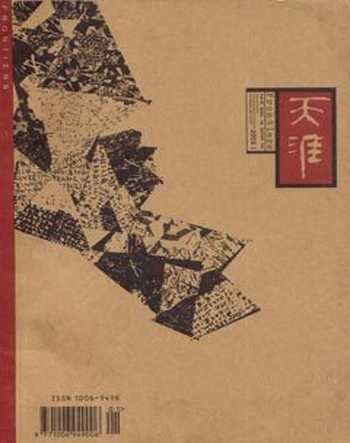阿巴斯自述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单万里
[伊朗]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著
单万里译
身世
我于1940年出生在德黑兰,小时候喜欢画画,上七、八年级的时候拿起彩笔就在纸上画。在学校里,我不是好学生,也不是好画家。我性情孤僻,沉默寡言:从开始上小学一直到六年级,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是的,跟谁都没说过话。
爱好
我十八岁就离开了家,被迫独立谋生。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成为电影工作者。一切都是出于偶然,是我朋友阿巴斯·柯汉达里的一双皮鞋使我成了一名电影导演!我参加高考时报的是美术专业,高考失败后就到交通警察部门谋了份差使。一天,我去柯汉达里的缝纫用品店,当时我穿的是凉鞋,柯汉达里让我陪他去一趟塔吉里什桥。我说不想去,因为我穿的是凉鞋。他就把自己的一双新鞋借给我,尺码跟我的一样。我们去了塔赫里什桥,来到法尔哈德·阿什塔里。阿巴斯·柯汉达里认识那里的一位叫穆哈盖克的先生,他是一个美术工作室的负责人。我就在他那里报名参加了补习,后来再次参加高考被录取了。我总共花了十三年时间才完成学业,获得学位。上学期间,我还一直在交通警察部门从事道路管理工作,或者负责监督道路拓展方面的工作。我晚上工作白天上学。
广告
后来,我开始从事广告工作,起初是搞平面广告设计,同时为好几家公司干活,比如设计书籍封面、画广告画等等。一天,我来到塔布里电影公司,那时这家公司也有一个广告片制作部。他们建议我到这里当导演,要求我为一种等温热水器写一个广告片拍摄脚本。当天夜里,我就为这种热水器写了一首诗。三天后,让我惊喜的是电影上播放了这则广告,里面用了我的诗歌。这是我从事广告片创作的开端,后来我又为其它广告片写创意,并逐渐过渡到亲自导演广告片。从1960年到1969年,我拍过一百五十多部广告。我的一位朋友发现我在广告中从不用女演员。事实上,在我拍的五十多部影片中都没有女性角色。那时,即便是做汽车轮胎的广告,人们都让女人出现在片子里。我很喜欢广告片。拍广告片受到很多限制,但这种限制是有益的。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里能说些什么呢?必须简化介绍性场面,浓缩信息,紧扣主题,让所有人都能一看就懂。拍摄别人定做的只有一分钟的影片,必须传达出有效信息,影响公众,促使他们购买产品。拍广告片的经历和美术设计的实践教会了我拍电影:一个美术设计方案,不论是出现在书上,在栏目里,还是在画框里,都得能让读者或观众一看就产生兴趣。在我看来,绘画是所有艺术之母。拍广告片受到很多限制,拍摄别人定做的影片迫使我们思考……不过,我记得那时人们说我拍的广告片确实很好,但不是为了促销商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没有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了去。
第一部影片
1969年,伊朗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领导人菲鲁兹·西尔凡路看了我拍的一部有关煎锅的广告片(这个协会也有一个广告公司),他对我的片子很感兴趣。拍摄这部广告片的灵感来自一本摄影杂志,人家都说我的片子很像西方电影:也就是说“挺棒”,技巧也不错。西尔凡路打算在协会创立电影部,就邀我一起做。我们说干就干,筹备工作持续了八九个月,包括建造一个摄影棚。那时,协会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搞电影的,我的第一部影片《面包与小巷》也是协会电影部的第一部影片,其他搞电影的人是在这之后陆续来这里拍片的。
绘画
小时候,我用画画打发孤独。午饭后别人都在午睡,可是我不困,就出去散步,为了不发出声响,就在阳台上画画。进美术学院之前,我在盘子和其它物品上画过骆驼、奶牛、豹子以及风景之类的东西。我的一些亲戚将这些画保存了起来,为了以后能卖个好价钱,他们现在见到我时还偶尔问我这些画的价钱有没有涨。
内心影像
存在于我内心的影像有别于我在画布上再现的影像。我在画布上再现的东西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倒是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影像、记忆、画家的精神对我帮助很大。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画家才有画家的精神。一天,我奶奶坐在行驶的汽车里说:“瞧,那树,那山……”在我看来,这时她指给我看的是一幅意想不到的影像,是数不清的影像中的一幅,是从成千上万个角度看到的影像中的一幅,她选择了其中的一幅尽情地欣赏,她正在自己内心里作画,她有画家的记忆,正在画一幅内心的影像。
捕风
我从未想到《橄榄树下》会在一个劲风掠过的麦田里拍摄,因为这个影像正是我十年前作的一幅画中表现的东西,最初的构思又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那时,我很少作画,而是更喜欢摄影。这个主题和构思更多地出现在我的摄影作品而不是绘画……但是,我认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因素会彼此融为一体。在我的摄影、绘画和影片里出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一种简单的颜色和光线,一种特别的意义和时刻。我搞上电影后也作过不少画,我认为电影比绘画更丰富。我在画布或画纸前经常不知所措,我无法表现麦田里的风在往哪个方向吹,可是在电影中就容易多了。我绝对不是画家,我绘画的目的主要是“用绘画疗法”治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绘画。
看电影
我小时比伙伴们更喜欢看电影,儿时的伙伴现在大都成了商人、医生或画家。我喜欢把电影当作娱乐,从来没有因为某部影片是某个导演的才去看。当然,我喜欢后新现实主义时期的德·西卡的批判喜剧,但是对我来说索菲娅·罗兰比德·西卡更重要!我家里人是不看电影的,他们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占据了他们所有的时间。除了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影片(为了医治孤独症我曾到布拉格去看捷克语电影),我一生中看过的影片不超过五十部。我从来没有把一部影片看过两遍,这样我也就不受任何电影家的影响。另外,我从来没看过任何一部“真实电影”。我无法忍受布莱松或德莱叶的影片,它们使我疲劳,我没能进入这些影片中。我读过好几遍由巴巴克·艾哈迈迪写的关于布莱松的书《自由的风》,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但是书中的理论比它的主题似乎更有意思。与德莱叶和布莱松的影片相比,伊朗影片对我产生的影响更大,比如苏赫拉比·沙希德·萨尔斯的《简单的事件》,比如基米亚维的影片,或者达里尤什·麦赫伊的《邮差》中的某些片断。我永远不会忘记《简单的事件》中那个孩子喝百事可乐的场面,不会忘记他为了跟上父亲而离开服装店的情景。总之,我看过的影片中让我觉得重要的场面不超过二十个。
希望与失望
我记得小时候把自己写的故事给大人们看,通常他们都非常谨慎地说挺好,而且往往补充一句:“可是太悲观了,实际情况没这么糟。”我立马就断定他们缺乏独立性,他们屈从于权力,拒绝承认苦难的社会现实。但是如今,当年轻人让我读他们的剧本时,我谨慎地说:“年轻人,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一线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你也应该试着……”从他们的目光里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认为生活和经验带给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几年来,尽管处境艰难,但是我的精神状态很好,这种状态以某种方式反映在了我的工作中。
剪辑
在我的第一部影片《面包与小巷》中,有一个特写镜头表现的是一个老人走向摄影机,然后继续走他的路,后面跟着一个小孩。那时人们说这不叫电影。我没有勇气让摄影机运动起来,推拉镜头,或者寻找正确的轴线,而是喜欢等待人物进入画框……我相信所有评论家的话,因为我害怕。让摄影机运动起来对我来说总是非常困难,那时我的理由是:当我们长久等待的某个人从远处走来时,我们就会一直看着他。我们等待着他的到来,因为他不是普通的过路人,他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致我们的目光不停地看着他,我们不想让这个镜头中断。那些莫名其妙的镜头分切,我搞不懂它们的意义何在,从来都不是我的趣味,那些被分切成八个乃至十个镜头表现的场面使得人看不到完整的场面。有时,现实本身也告诉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地分切场面,为了接近人物不必非得将摄影机靠近他们。必须等待,肯花时间才能更好地观察和发现事物。有时,特写并不意味着距离拍摄对象太近,大远景镜头也是一种特写。我发现,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在书上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行不通的。在拍摄影片《经验》时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少年让别人给他的皮鞋上蜡,那个擦鞋人坐在少年的脚旁边,试图修理他的皮鞋,但遭到少年的拒绝,因为他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接下来有一个主观镜头,摄影机表现弯下腰的擦鞋人。在这个镜头里,擦鞋人以自信的目光看着少年,似乎在告诉少年他不会把皮鞋弄坏,以致少年无法拒绝,最后终于抬起皮鞋。书上的规则告诉我们,如果摄影机俯拍某人,就意味着这个人处在劣势,其实一切都取决于谁看谁,以及他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规则你都必须学习,但是学习的目的是避免使用!
拍摄演员
当然,我也不同意一味地以连续拍摄的方式把所有东西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观众。起初我看到摄影师在拍摄一个场面时突然停下了,他说:“演员把脑袋转过去了,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就对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演员,即使他偶尔背对摄影机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观众老是看演员的近景,该怎么想呢?”每当演员在一个不太明显的地方走动,摄影师就将镜头切断。但是,我们是可以将昏暗的场面用来为影片服务的。有时,看某人的膝盖反倒可以更好地表现出他的精神状态。遗憾的是人们有这样的想法,即如果只向观众表现演员的项背,就是不尊重观众,或者认为观众会感到不舒服,就好像在剧院里看戏一样,演员总是面对观众而从来不转身背对观众。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痛苦,感到无法理解。当然,我也意识到戏剧有它自己的规则,但是作为观众我认为这是造作。有时,摄影师就像拍证件照的照相师一样拍电影,他们认为绝对需要“框住人们的两只耳朵”后才能拍摄,原因是他们没有把影片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一位摄影师合作之前,必须知道他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只有具备足够的耐心,才能很好地拍电影。
同期声
声音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比画面更重要。我们通过摄影获得的东西充其量是一个平面影像。声音产生了画面的纵深向度,也就是画面的第三维。声音填充了画面的空隙。这就如同绘画与建筑之间的区别,在绘画中我们面对的是平面影像,而在建筑中重要的是维度。没有现场的特定声音的镜头是不完整的。以《橄榄树下》中侯赛因在阳台上跟塔赫莉说话的场面为例,为了跟塔赫莉说话,侯赛因需要跟她单独在一起,不应该让其他人听到他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只听到侯赛因的声音是不可行的,必须还有其它声音,只有在其它声音的掩护下侯赛因才能跟塔赫莉说话……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把摄制组工作人员的说话声跟演员的说话声混合在一起了。没有这种混合,镜头就缺少了某种东西,我在拍摄许多场面时都使用了这种方法。大多数录音师都只顾看录音机的指针,试图尽可能地录下质量最好的声音,他们不关心声音产生的景深问题或特别的印象。比如在《特写》中马克马尔巴夫和塞巴齐安讨论问题的那个场面里,声音突然被切断,过了一会才恢复。所有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抱怨录音师,说他没把这段声音录上,也就不再信任他的工作。大家都觉得这是他的错误,而实际的情况是,这段声音空缺是我在后期制作时有意为之。如果不是出于自愿,这段对话是可以补录的。当我想用剪刀切掉这段声音带时,《特写》的录音师有意地看了我一眼,他认为我不会真的这样干。他拒绝亲自剪掉这段声带,最后是我下的剪刀,那时他正在剪辑室的另一头来回走动,看了我一眼后自言自语地说:“他正在用自己的手搞乱他的影片。”
表演
我觉得,在跟非职业演员合作过程中,如果没有情感上的联系就无法与他们沟通。我跟我的演员在拍片以前很久就建立起了联系,而且有别于一般导演与演员的关系,否则我的演员就无法表演。从前,我的同事们曾经问我:“跟非职业演员一起工作是否很难?”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直到起用职业演员穆罕默德·阿里·凯沙瓦尔兹出演《橄榄树下》之后,我才找到问题的答案。尽管他的表演让我满意,但是现在该轮到我问我的同事们:“跟职业演员一起工作是否很难?”跟职业演员必须用职业语言交流,而跟平常人交流需要触动心灵,以心对心的方式说话。他们无法接受命令,无法按照你的命令精确地行事。为了使他们按照你的愿望行事,你不必教训他们,只需与他们相依为命。这样会使演员与你如此接近,以致你都不知道是你在写对话还是他们在写对话,是你在指导他们还是相反。我被迫经常去找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我”,而我也变成了“他们”。如果您觉得我影片中的表演非常敏感和细腻,那是因为我跟这些非职业演员之间存在着这种感情上的联系。
演员至上
我在拍过几部影片后就彻底意识到:必须取消导演!事实上我已走上这样一条路:为演员提供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摄影师与我之间的纠纷不断,他们说我太宠爱演员,这样做将导致“演员至上”。
重复
对所有那些想跟非职业的演员合作拍片的人来说,必须明白这样一点:不能让演员在摄影机前背台词。他们连普通的表演程序也不懂,必须让他们相信对话,以便能在一段时间后感觉到这就是他自己的话。为了与他们真正进行交流,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时间,而且不能随便找一个什么人就在摄影机前指导他们演戏。到《橄榄树下》开拍时,我跟侯赛因·莱扎伊已经认识一年多时间了,我跟他一两个星期见一次面,我们一起讨论剧本和对话。这就像人的头发一样,必须一点一点地长。每一次见面我都跟他谈到“富人与穷人”问题。当我们见到该片的摄影师侯赛因·贾法利安时,我对侯赛因·莱扎伊说:“请重复我对你说的有关富人和穷人的事情。”这时,他已经搞不清这些话是对他说过的还是他自己说的。总之,后来他重复了这些话。当他说错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这不是他从前说过的话,也不是我加上去的,而是他说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当我见到一个新的非职业演员时,我就对侯赛因说重复有关“富人和穷人”以及“有房子的人和没有房子的人”的事情。逐渐地,侯赛因认为这些话就是他自己的话,这些话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在拍摄期间,他在摄影机前自然而然地重复这些话。甚至在接受采访时,他都认为这些话就是他说的。他之所以相信这些话是他自己的,是因为他知道这些话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了,这些对话是属于他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程序。
现实
我总是寻找简单的现实,这种现实往往隐藏在表面现实背后。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有时会碰到摄影机之后发生了某些事件,它们跟影片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比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的主题更吸引人更有意思,于是我就将摄影机转向这些事件。
幻像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正在观看的是一部电影。即使是在看来非常真实的时刻,我都希望画面旁边的光芒闪烁不停,为的是提醒观众不要忘记他们正在观看的并非现实而是电影,也就是我们以现实为基础拍摄的影片。我在新拍的几部影片里加强了这种做法,以后还会进一步加强。我认为我需要更加内行的观众。我反对玩弄感情,反对将感情当作人质。当观众不再忍受这种感情勒索的时候,他们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就能以更加自觉的眼光看事物。当我们不再屈从于温情主义,我们就能把握自己,把握我们周围的世界。
拍摄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影像是所有艺术之母。我之所以被电影吸引,应该说是因为影像总是让我着迷。不管是摄影还是绘画,我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像的控制,以致最终走上了从影之路。然而,我之所以当上电影导演,并不是因为电影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艺术,或者如人们常说的是一种综合艺术。我始终认为摄影、绘画、平面设计等艺术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很重要,不过我仍然认为摄影具有特殊的地位。我还记得,我们在拉什特城完成《合唱》的拍摄任务以后,像往常一样,摄制组人员都离开了高原,有人甚至已经回德黑兰了,只有我留在了拉什特,与一架照相机形影不离。第二天,我带着相机信步穿行在狭窄的街道中,街道两边到处是潮湿的水泥墙,长满青苔的石灰墙以及油漆斑驳的木门等等。我在那里呆了好几天,拍照片打发时间,我感到非常安静,不用再为拍摄电影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烦恼。现在,我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画面了。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影像是万物之源。我经常是从一幅内心影像开始写作剧本的,也就是说,我是从存在于脑子里的一幅影像开始建构和完善剧本的。比如,在构思《结婚礼服》时,我脑子里起初出现了这样一幅影像:清晨,一个神情困惑的小伙子在阳台上给天竺葵浇水。这幅影像本可以构成一部长故事片的情节线索,但是拍摄到第四天,当我们正在拍摄这个浇花场面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场面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强烈的冲击力,换句话说,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故事被废除了,直到最后化作乌有。而拍摄《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过程则与此相反,重要的场面是最先出现的:一个孩子朝着小路尽头的一棵树跑去,最后消失在山里。拍摄这部影片之前,这个影像在我脑子里已存在了好几年,这样的影像可以在我那个时期的绘画和摄影作品里找到。我的无意识被深山和孤树吸引,我们在影片中忠实重构的正是这样一幅影像,山、路、树是构成这部影片的主要因素。
对于所有电影艺术家来说,摄影也许是一种基本需要。首先,摄影教给他们如何观察世界,使他们在自己的内心积累影像。摄影能够获取某些图像,也能舍弃某些不合适的图像,识别和选择美的事物是一项复杂和艰难的工作。只有摄影才能使我们获得这种识别的能力。在有关平衡与和谐的意义方面,摄影启发着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视觉。事实上,如果说美是构成艺术的本质,美的表现形式是平衡与和谐,摄影就是理解美的基本意义的途径。在我看来,摄影师可以通过不同的构图记录下自己的感觉和审美趣味。他可以将过去的照片放进抽屉,需要参考的时候就拿出来,以比较或研究自己的美学趣味与敏感性的演进。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求助于影像纪录事物意味着“占有”人类的精神财富。我在观看《哪里是我朋友的家》时重新发现了二十年前的画面:一条街道,一条狗,一个孩子,一位老人,一根面包棍,这一切重新出现在我拍摄的影片里,这种连续性的重复在我的无意识中发生了作用……
摄影能够满足人们的创造欲,使人可能接近安宁,具有某种神奇的净化心灵的功能。当我看到卡斯莱安在达玛旺德山上拍摄的照片时,我想起了神圣和虔诚,长年累月地拍摄这些高山,我认为是一桩神圣的事情,它使我想起了电影摄影艺术的至高无上。摄影的神奇净化作用表现在人处在孤独中,面对自己的时候……按动快门的“喀嚓”声没有扰乱大自然的寂静,这寂静被瞬间凝固了。神奇广袤的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摄影表现的内容,被简化到摄影机里,以便人们能够放在内心深处安然地保存下来。我们以某种理想主义的方式观察事物,认为它们接近于我们想象的样子。不幸的是,通常情况下事情并非如此……比如,在阳光明媚的蓝天下拍摄的山峦当然很美,但是在有白云掠过的情况下拍出的效果可能更美,因为光与影的变化使景物丰富多彩……
摄影能够使我们以某种神圣的方式欣赏大自然和生命的存在。不应忘记,达到欣赏自然和生命的阶段是很难的。人们应该懂得观看,懂得观察,一切都归结于观察事物的方式。秘密就存在于有关视觉的知识和观看事物的方式中,我们拥有两个无法估量的、值得我们爱惜的珍宝。一天,我跟儿子在街上散步,那时他还是孩子,他对我说:“爸爸,眼睛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不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两个小小的圆球能看到那么大的东西。”我知道,那时他正在看街对面的迈拉银行的高楼建筑。有时,孩子们提醒大人的东西让大人感到惊讶,大人们不应以表面的方式看待生活,而是应该好好地睁开眼睛,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
我佩服观察,默默地观察,特别是观察大自然。当我们喜欢某人时,人们就跟他一起照相,想他时您只需翻开家庭相册。我的家庭相册里珍藏的满是大自然风光。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伊朗著名的电影导演,具有国际影响。主要电影作品有《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生活的继续》、《橄榄树下》等。
单万里,学者,现居北京,有译著多种。